第七章 大禹之墓
我不能接受若燃身体有问题这个说法!
可这到底是真是假,连我都不知道,我可是他身边最亲最近的人啊!
想来想去,我给肖亚伟打了个电话,含蓄委婉地说找他有事儿,但是又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之下谈,我提出找个地方吃饭,边吃边谈。
他略略犹豫一下,就答应了。
谁会拒绝我这个未亡人的请求!
见面的地点就在我们家门口的饭店,还不到饭点儿,这里很安静,非常适合谈事情。
我假装不经意地透露,若燃有段时间对我很冷淡,我怀疑他在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
肖亚伟会心的一笑,之后摇摇头,表示不可能。
我又半开玩笑地问学校里有没有漂亮女孩儿、若然对漂亮女孩儿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并且强调一句:异性相吸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肖亚伟老老实实回答,学校里面漂亮的女孩子很多,漂亮的女老师也多;若燃因为长得帅,在女生当中还特别受宠;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有女朋友,而且对他的女朋友特别好。
“那你们在背地里,会对漂亮的女生、或者身材好的女生,做更深的讨论吗?”
“哪方面的讨论?”其实他肯定猜出来我要问什么了,只是确认一下。
“比如,更深一点的,生理方面——?”
话题一旦打开,接下来的交流就容易了。
果然,他们在背地也会谈论“男人间”的话题,比如那些日本A&V,若燃完全表现得像个正常的男人,他不仅对那些个名字耳熟能详,还会深入讨论一些类似“姿势”之类的问题,而且他还提过,他女朋友的胸部尺寸是非常“傲人”的。
我旁敲侧击地问起若燃的“尺寸”,性取向等等。
肖亚伟虽然即脸红又惊讶,但还是很认真地告诉我,他的“尺寸”绝对能让大多数女性满意。性欲旺盛是雄性动物最基本的竞争优势,这也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猜他能听出我的揶揄口气。
“这好说,一起洗澡,或者一起上厕所就能看见。只要是男人就不可能对同性这样特殊部位的尺寸毫不在意。”
若燃的笔记本电脑上确实有成人片,而且肖亚伟还知道他的电脑密码,这连我都不知道。
我顺理成章地从他的硬盘找出了不少“藏品”,一想到若燃看上去白白净净地,人长得绝对斯文,平时羞涩得很,却有如此强烈的这方面的爱好,实在是大出我意料之外,隐约又觉得自己对他确实太惨忍了。
对着电脑看了一会儿,眼睛疼,于是起身走走,走着走着,就到了若燃睡觉的房间里!
没错,不多的几次若燃回来睡觉,就是睡到这个房间里!
他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这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
我无法相信那个事实,无法相信这个家这是我一个人了!
这是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房间,现在它正中间放着一个很大的箱子。
房子很小,箱子很大,显得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都是肖亚伟从若燃的办公室里收拾回来的!
我胡乱翻着,都是课本和教参,还有一些画稿和绘画工具,还有乒乓球拍儿,羽毛球拍!
最后,看到一个软皮的会议记录本!
扉页上写着,“私人日记,请勿打开!”
多么幼稚的一句话!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离开云梦山那年,我只有七岁。
那一天的云霞开得格外灿烂,周围连绵起伏的群山被一层朝气所笼罩,爷爷用羊皮袋灌满了山泉水,我们便出发了。
我们要步行十几里的山路,才能走到大公路上去坐车。
山里枝繁叶茂,树木高耸入云,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枯枝败叶,里面夹杂着松果和碎石,非常难走。
我是自小在山里长大,脚力极好,但是依然跟不上身轻体健的爷爷。
我问爷爷我们还回来吗,爷爷说那是一定的。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离开?
爷爷慈祥地微笑,一如往日,“小儿长大了,你会有你应该守护的东西。”
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爷爷那么大,爷爷守护,为什么要小儿守护?”
爷爷说,乱世则出,太平则隐。
我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伤感和无奈,小孩子的想法总是那么简单。
若干年后我问自己,如果有权利选择,我会怎么办?
上了车,我一路晕车,爷爷只好抱着我,他的身上总有一股清新的味道,让人迷恋、沉醉。
可我在强打精神,默默地记忆路旁的每一个标志、路上的每一个拐弯儿、每一个上坡下坡、转过的每一个山头、经过的每一个村庄,生怕会迷路,生怕爷爷把我丢下。
可我最终还是沉沉地睡去。
睡了不知道有多久,爷爷抱着我下车了,司机说不走了,怕被困住回不来,前面已经淹死人了。
我醒来,发现公路旁边到处都是水,一片汪洋淹没了远处的村庄和农田,本来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却给人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
爷爷望着远方,水天一线处,飞过鸟群,给这个死气沉沉的大地带来一线生机,爷爷说,“小儿谨记,你是大禹的后人,应当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
我非常害怕,但是依然点了点头。
1996年,河北发生了特大洪水,我和爷爷一路踩着水,艰难地回到了故乡Z城。
我第二天醒来时,爷爷就不见了。
只有奶奶陪着我。
后来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爷爷还是会回来,寒暑假的时候也会带我一起回到云梦山,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但是,我只能在山里待很短的时间,因为,我要读书,我要上学。
爷爷说,天地无情,只有好好念书才能好好牠保护家人,保护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上了村里仅有的一所小学,直接跳班读的二年级,我学得很容易,在班里总是考第一,老师说我是个聪明的好孩子。
有一天,班里有一个同学带着蛋糕到学校来过生日。
同学们给他唱歌,她妈妈微笑着跟大家说谢谢,还给我们每一个人发了一块蛋糕吃。
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蛋糕发到我这里,已经发完了,她给我一块糖吃!
我心里委屈又不敢说,她妈妈非常抱歉地说,“对不起,要不等你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你买一个更大的蛋糕!”
我哭了,我以为蛋糕只有妈妈才能买,而我没有妈妈!
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妈妈从他儿子的蛋糕上又分下来大大的一块发给我,可是我却没有吃!
回到家里,我鼓起勇气问奶奶,为什么我没有妈妈!
奶奶的反应和平时一样冷漠,起身回到她自己的房间里,一扇薄薄的门帘,把我隔绝在另外一个世界。
是的,她没有义务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而且我跟她也不亲。
我们只是住在一个屋檐下,她照顾我的吃穿住行,仅此而已。
我知道我只是被爷爷丢给她的,甚至可能从没有问过她个人的意愿。
我故意地不吃饭!
她从地里回来之后,看到桌子上的饭已经是冰冷的,筷子也没动,愣了一下。
我故意地不看她!
最终,她将饭菜端走,没有说话。
离开的时候,又回头最后看了我一眼,满脸的冰霜,那枯瘦的身体像秋日被寒风刮断的一截树枝。
等她最终消失在门外,我泪如雨下。
她依然每天忙碌着,到了吃饭的时候就给我盛好饭,摆好筷子,也不说话。
可是我还是不吃。
等到凉了她便端走。
下一顿饭还做,凉了还端走。
我终于被她的这种态度激怒了,我把碗狠狠地摔在地上,拿板凳砸她,躺在地上哭闹!
她不说话,不卑不亢,面不改色。
等我闹够了,她便起身收拾,收拾完了还去地里干活!
三天后,我终于因为饥饿在课堂上晕倒了,被老师送回家。
我醒来时看见奶奶坐在床边。
奶奶看着我已经醒过来了,便闪身离开。
桌子上依然摆着两碗饭,她一个人默默地小口小口静静地吃着,也不抬头。
我终于屈服了,端起碗来,大口大口地吞咽,偷偷地打量她,她没有任何表情,一如往常!
奶奶只管我的一日三餐和最基本的衣物,甚至连袜子和内裤都不给我买。
她所有的时间都在摆弄村头那一片金银花,剪枝,打杈,除草,采摘;再剪枝,打杈,除草,采摘!一茬又一茬,一年又一年!
她把采来的金银花很小心的放在一个个长方形的木匾上,很小心地把它们摊开,轻轻地抚摸,如同在抚摸自己的孩子。
那是她的孩子,而我不是。
我终于鼓起勇气再次开口,“我的妈妈在哪里?”
“你的妈妈死了!”她头也不抬,冷冰冰地说。
“死在哪里?”我追问。
“埋在地里了!”她不耐烦地冲我摆摆手。
爷爷说,每个人都是会死的,人死了之后会埋葬在土里,但他们的记忆会像一颗颗种子在土壤里生根发芽,长出地面,飘散在空气中,最终附在金银花的花瓣儿上,等待着下一世的轮回。
所以金银花的花香,会唤醒你前世的记忆。
从那以后,我对金银花总有着敬畏之情,我相信妈妈总会追随着前世的记忆找到我。
我轻轻地抚摸着它的每一个花骨朵,仔细观察它的纹理,对着它们小声说话,诉说着对母亲的思念,常常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我将花骨朵放在掌心里,让它的孤度与掌纹重叠,仿佛命运纠缠的曲线。那清冷的颜色总令我着迷,就像云梦山的迷雾,幻化出无数的形状,熟悉而久远。
我每天闻着它的味道睡去,带着对母亲的思念醒来。
我对于自己的身世有很多种猜测,每一种猜测刚开始都信以为真,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怀疑,怀疑之后又开始新一种的猜测,周而复始。
我常常梦见我的母亲会过来接我,带我离开这个冷漠的奶奶,带我离开这个丝毫没有温度的家,去一个有电视有暖气的新家,还给我买蛋糕吃。她一定有着和三标妈妈一样亲切的微笑,或者,她和爷爷一样有本事,是个武林高手。
我长得叛逆而暴躁,对奶奶冷漠而挑剔,稍有不顺心,我便冲他大喊大叫。
我常常在外面一呆待一天,宁可饿肚子也不回家吃饭;明明知道大人担心,却依然在外面的水坑里面游泳。
可是她从来不管我。
有一年暑假,七月的天气火热异常,等到了半夜,我再一次跑到家门口的水坑里去游泳。
我意外地发现我已经长成了半大小子,不仅长高了,身体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水是流动的,格外的轻柔,如同母亲的手。
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手指碰触到一个软软的东西,我一惊,猛地从水里窜起来。
就好像在暗夜沼泽地里匍匐前行的旅人,突然看到了七月萤火虫微曦的点点光亮,那些光亮最终汇聚,勾勒出母亲的样子——
月光下,一个女人的面庞清晰地从水里钻出来,出现在眼前,一双大眼睛闪亮如星,黑白分明,黑得如寂静的夜空,白得如洁净的晨雪,黑白交汇间,清澈见底,透彻通灵。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这扇窗户一定连接着她最深处的爱与善良。
我禁不住要在心底赞叹命运的慷慨恩赐,有幸遇见她,千年等一次又何妨?
她专注的看着我。
空气里弥漫着金银花的香味,那个女人就在我的眼前,望着我,一动不动,恍若隔世,神仙一般!
她五官普通,却非常清秀,头发湿漉漉地垂下,肩膀和大半个胸部露在水面之上,圣洁的如同一朵待放的白莲花!
我刚才触碰到的莫不是她的胸部?
想到这里,我的脸火辣辣地烫!
等我反应过来,才意识到我们俩都没穿衣服,我赶紧游回岸边去找衣服。
那个女人也跟着我过来,我穿衣服的时候她一直盯着我,本来是夏天,我有一条裤衩,一个背心。
看到女人纯净专注的眼神,于心不忍,我把背心脱下来递给她。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身体,却又不敢有半分邪念。
我害怕,又渴望,是母亲来接我了吗?
她却没有半分羞涩,只是呼吸格外沉重急促,好在那个女人个子不高,我的背心也大,勉强遮到她的大腿根部。
我拉她上岸,触到她的手,凉而温和,是人的体温。
那种温度,让我冒出了一缕属于男人的胡思乱想。
她也不说话,用手撩了一下额前的头发,不动了。
我本来也不爱说话,两个人就这样尴尬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夜已经很凉了,我站起来,她也站了起来,跟我一起回了家。
此时已是半夜,奶奶早已经睡下了。
那个女人一进门就倒在床上,沉沉地睡去。我只能在旁边对自己打了个地铺。
一夜无话。
地上又潮又冷,好几次,我一厢情愿地想:那个女人会不会不忍心、主动提出让我上床去,或者我忍不住爬上她的床、贴进她的温暖?要知道,我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虽然比大多数人自律,但是最基本的需求还是有的——
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耻!
第二天早上是奶奶把我喊醒的,我问奶奶,有没有看到那个女人?
奶奶叹了口气,“该见得总是会见,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我听不懂,她也不可能跟我解释。
高考结束之后,我又一次跟着爷爷回了云梦山。
在祖师爷鬼谷子的神像前,我叩了三个响头,爷爷问我,“你更愿意在山里待着,还是回到老马庄村?”
我说我都不想,我想去大城市, 考上大学,好好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爷爷叹了口气,“你不可能离开大陆泽!你一旦离开,整个大陆泽将会被洪水淹没!”
“为什么?”
“你是大禹的后人!爷爷年轻的时候,不想留在这里做守墓人,至到1963年洪水肆虐。后来,小儿出生了,爷爷带小儿去修行,直到1996年洪水泛滥,爷爷意识到,血脉里流淌的使命,不可辜负!如若不然,必遭天谴!”
我只知道长辈人说这里是祖上先辈马允中的坟墓,只因为是马家长辈在此看守,所以叫看坟庄,没想到,这里竟然是大禹的坟墓。
而我生来,就是为了给人看守坟墓的!
这让我无比心痛,相比奶奶的冷漠和无视,做一个守墓人更让我难以接受!
“大禹的坟墓在哪里?”
“等你有一天娶妻生子,我会告诉你!”
“家里穷得叮当响,你还指望我娶妻生子?”
“该见得总是会见,该来的总会来的!”
“那如果我一定要离开呢?”
爷爷长长地叹息!
我终于在大学里见到了那个女人,不,是个女孩儿,似乎她的年龄比我还要小两岁,那个酷似母亲的女孩儿。
我想我们注定要遇见,即使不是在这所大学,也会在别的地方遇见。
我总是想方设法找借口接近她,又害怕离她太近而亵渎了她;她会专注而深情地看着我,却对过去的事情一无所知。
这个女孩儿是个学霸,每天都在操场上锻炼身体,每天都去图书馆学习,虽然长得不出众,却完美得像一个女神。
我真心喜欢她,她善良执着,真诚自然,流淌着春风般的暖意。她有小轩窗、正梳妆的温婉,也喜欢左牵黄、右擎苍的豪迈;更有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忧伤。
对于一个女生最高评价莫过于赞美她有才学,就好像赞美一朵花的品质。与其说是知识的重量感,不如说是长期的专注与投入给她一种尊严感,这种尊严感让人敬畏。因为才学带来的气质是无与伦比的。
我感觉我苦苦的追寻和夜以继日的思念有了结果!
后来她变成了我的女朋友,我却不敢在她面前表现出欲望,不敢碰到她身上不该碰的地方,不敢亵渎她神圣的身体。
强大的人性都是雌雄同体,他们早已从男欢女爱的桎梏中走向了灵魂深处对自由的探寻与渴望。
有时候我在心里常常泛出一丝伤感,如果她和我在一起,那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永远呆在老马庄村里,总也走不出来。
可我又舍不得与她分离,毕业之后她和我一起回到了故乡,我给她买了房子,却又不敢和她在一起过夜。
家里的摆设相当简单,除了一些绿植和简单的家具家电,没有丝毫的赘物。
如果不是厕所里面放着卫生巾,你绝对想象不到这是女孩子的房间。
她的日子过得十分简单,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来往。
她从不穿裙子,从来不买化妆品。
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我,我说我辛苦一点没关系,我希望她过得好一点。
但是她从不以为然,依然清苦,却说自己很幸福。
她没有权力欲,也没有物质欲,像一朵白莲花!
是啊,她看起来总是简单而幸福的样子。那她是真的幸福呢、还是仅仅看起来幸福而已?我不知道。
不过,我却因此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深深的寂寞。
大概是和她在一起待的久了,我对她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我也曾经幻想过生一个和她一样的孩子,最好是个女孩儿,我用一生一世去呵护她们,给她们幸福,除非死别,绝无生离!
可是,守墓人的使命,让我对未来望而却步。压抑,无奈,我堂堂985大学环境设计专业高才生,只能在县城呆着,甚至给不了她稍微好一点儿的生活!
看着她每天忙碌,我万分愧疚!
为什么不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个世界如果虚华,我却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和自由,我所有的爱和梦想都无处安放,在这个家族古老的使命面前,我注定无处可逃!
真应了央仓嘉措那句话:假如真的有来世,我愿生生世世为人,只做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哪怕一生贫困清苦,浪迹天涯,只要能爱恨歌哭,只要能心随所愿。
字迹写到后面越来越乱,甚至还用钢笔扎了几个洞,可见他当时已经烦躁无比!
而他对我,从来都是那样的温柔。
我一直觉得他生性懦弱,却没有想到,这懦弱的背后有那么多的悲伤和无奈!
温柔的人通常都是这样诞生的,他们亲身经历许许多多的难过后,决定让其他人不再像自己这般难过,这份血淋淋的体贴,人们称她为温柔。
那秀丽的字体,那让人肝肠寸断的柔情,句句扎入我的心底!
那个出现在他日记当中的女人是谁?真的是我吗?
神经兮兮的!
奶奶说,如果想找粑小儿,必须到水里面去,原来那里是大禹的坟墓。
是不是他们的子孙后代死了之后都葬在哪里,或者,若燃也要魂归故里?
清明节已过,我母亲来了。
关于所谓的“守墓人”,我有万千个疑问,也只能暂时放下,因为我腹中的婴儿,正在一天天地长大。
母亲要求我把孩子打掉, 此时距离飞机出事已经一个月了,照理说,飞机上那些人已经没有了生还的可能,包括若燃!
我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我真的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关系。
母亲说:最早的族志记载,涂山氏族,居青丘国。而涂山是个氏族名,那个时候国家尚未形成,青丘,实际上是个城池的名字。
九尾狐是涂山氏的图腾,只有这一条血脉,你也知道我们家族人丁衰弱。
这里的人丁,自然指的是男丁的意思。
万恶的男尊女卑的思想!
相传当年,大禹为了治水,抛弃涂山氏,一别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来功成名就之后,另娶他人,生下了开创夏朝的启。
而涂山氏一生孤苦伶仃,为延续九尾灵狐之血脉,钻研未婚生育之法,看来,最终应该是成功了。
但是,纵观涂山氏整个家族,从来没有过超过22岁未婚的女性,所以也不知道未婚生育这项特殊功能有没有传承下来。
你若想知道这个孩子是否是若燃的,只怕只能等生下来之后做亲子鉴定。
如果不做,他假使活着,按照一般男人的想法,他能否接受这个孩子,也是未知数!
不过现在反正已经没有必要,若燃已死,死人就是死人,他的意愿已经不再重要。
如果孩子生下来,别人也以为他是若燃的孩子,你要让他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纵然你万般骄傲,一个月才挣多少钱,能否养得起它?养孩子不是小猫小狗,更何况生完孩子之后人是万般虚弱的,至少需要两个人在身边形影不离的照顾,除了我,你指望谁?
我想起若燃那个奇怪的奶奶,还有他那个我从来未曾见过的爷爷!
母亲领着我在医院产科转了一圈,确实,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母婴身边都是前呼后拥的,如果换了未婚的我,——
未婚生育我好意思跟别人说吗?所以,那个时候肯定只有母亲在我身边!
再想想,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家里谁不是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孩子一堆,只有若燃,孤苦伶仃地长大,我的孩子,要和他一样吗?
这个孩子生与不生,都融进了太多的悲剧意味。
母亲说:“把孩子生下来肯定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你肯定是要结婚的,不要轻易做出当一个单亲妈妈的决定。”
现代社会,不管一个女性如何再优秀,只要她没有结婚生子,我们心里总会有一声叹息和一丝暗暗的得意,觉得她总归没有那么幸福,就连原本的嫉妒也好像淡化了许多。
只在这一条上,她的人生似乎就黯然了不少。纵使她在事业上再辉煌璀璨,纵使她过着质量很高的单身生活,纵使她一直孜孜不倦的在追求着自我,纵使她对这世界还保留孩子般的纯真和热情,但在旁人眼里,她就是不如意,不痛快,我们认为她一定会渴求着婚姻生活的降临和一个男人的陪伴。
人们的眼光还是那么的狭隘,就仿佛远古世纪,女人应该三从四德,应该相夫教子。
而观念的东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我心中万般悲痛,想起若燃对我的千般好,我却无以为报。
一个生命要葬在我的手中,这种感觉是很复杂的!
从小到大,母亲没有反对过我做的任何决定,就连当初我和若燃在一起,纵然她心中也有一万个不愿意,最后也是默许了。
而现在,我也只能遵从她的意愿!
我没有给钟华打电话,有些事情,你越跟别人商量越拿不定主意。
做了这个决定,才知道打胎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去小医院,担心医疗条件不行;去大医院,跟你要身份证等一系列的证明,还要有家属签字。而且,大医院里人来人往,这种事情,肯定要偷偷摸摸地做,万不得已不能让别人知道。
想来想去,不能在Z城做;也不能回老家做,万一碰见个熟人,只怕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于是跟单位请了假,决定去W市!
一来对那个城市比较熟;二来,同学都已经毕业了,也不容易碰见熟人。
火车在急速地奔驰,母亲晕车,一直昏昏欲睡,我在一旁无声地啜泣!
我无数次幻想过自己孩子的样子,我甚至幻想过自己第一次做L的样子,唯一没有想过的是,我竟然会堕胎?
可怜的孩子,我曾经期待过你的到来,可却无法迎接你的到来,因为妈妈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勇气来保护和照顾你,如果可以,我愿一生一世守护你。
怀孕不容易,胎儿不知道修炼了多少个世纪、经历了多少次磨难终于长成了人形,才有了一点儿意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种痛苦。
都说母爱最伟大,母亲是最善良的人,为什么会舍得让自己的骨肉承受这种痛苦。
它会不会跟我说,“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它愿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
生离死别,竟是如此地痛彻心扉!
我问:“医生流产怎么做?”
医生说:“一般情况下,先吃药,孩子会自动流出来,但这仅限于怀孕49天以内的胎儿。50天以上的胎儿,药流一般流不干净,需要再刮gua宫!”
“那宝宝疼不疼?”
“宝宝?”医生奇怪的看着我,“哪个宝宝?”
“当然是肚子里的那个!”
医生笑了笑,“基本上每个人都会问流产疼不疼,很少有人会问孩子疼不疼,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所以不清楚!”
旁边另外一个医生说:“如果你决定不要的话,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手术;如果想要的话,还希望你三思!因为这个药一旦吃下去,就没有办法挽救了。”
“那么流掉的孩子,你们怎么处理——”
“放到焚烧炉里边焚毁,你要知道我们也不愿意碰那些东西!”
我仿佛看见一个还未成型的孩子被扔进火化炉时的情景,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要遭受这种待遇,真是冤孽!
医生继续说:“我看你还是舍不得,有很多人在吃了药之后跟我们说:‘医生啊,我后悔了啊,你看孩子还能要不?’我们也不好处理,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
可是最终做决定的却不是我。
做完一系列复杂的检查之后,医生单独把妈妈叫去,说了一大堆,妈妈出来的时候,万分为难的样子!
医生解释的比较专业,孩子已经两个多月,医生初步决定的方案先药流、再刮gua宫,但是我的身体条件——
我的处女膜长得非常完整,这也出乎医生的意料之外。
他们医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给未婚少女做妇科手术,必须以保护处女膜为前提,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更何况,孩子非常健康,手术又不是非做不可,所以,医生这样告诉我母亲,“建议你到别的医院去问问。”
没办法,我只能给钟华打电话。
他当时正好在W市。
他本来就是本地人,总不能为了若燃的事情一直留在Z城,甚至,我都不一定会留在Z城!
医生之间的对话更为专业,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术语,而后,又告诉钟华:他们医院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病例。
“是不是一个叫——”钟华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从手机上找到一张照片给那个医生看。
那个医生看了一眼,又给另外几个医生传看,他们小声窃窃私语了几句,最后跟钟华说:“是的!”
那一瞬间,钟华看上去十分失望,他微微叹了口气,又问:“她当时的病例我能看一下吗?”
“没有病例,因为她只是做了个检查,我们没有给她做流产,所以,——”医生看了看我和我妈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看我们,我母亲却懂了,拉着我出来!
“你看你一点儿眼力价儿也没有,还想一个人养孩子,人家摆明了是不想在我面前谈这个事情!”她又恢复了往日训斥我的语气,全然不顾我是个孕妇。
我只能讪讪地笑笑。
我只能讪讪地笑笑。
“那个男人是谁?”当母亲的总是对女儿身边的异性非常敏感。
“他是若燃的朋友!”我说。
母亲叹了口气,奇怪,她为什么叹气呢?
若燃出来了,他把我母亲叫过去说了很多话。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被他劝服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地转变,竟然坐火车回老家了,临走前嘱咐我好好照顾自己。
“你跟我妈妈说了什么?”母亲走了之后我问他。
“你为什么不问你妈妈呢?”
“问你不是一样?”
“……”
“你有事瞒着我:那个女孩儿是谁?”
“千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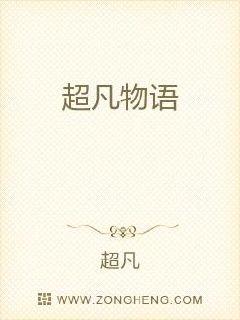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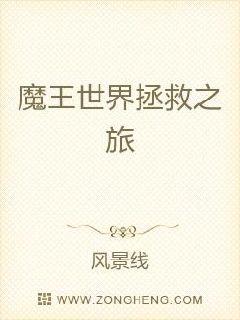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