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尖啸
发现自已故人士吴宇的遗物。吴宇于2015年12月25日于家中自焚身亡。
————————————
我的祖父在2002年9月因肝癌逝世,追悼会举办得很隆重。由于当时尚且年少,所以对祖父的记忆早已模糊,只记得当年他是一位勤务兵,最高时位至少尉。
祖父在我印象中总是严肃且一言不发的,或许是因为病痛的折磨。自从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他才会偶尔露出笑容。也许是经历了战争年代的金戈铁马,见识了人间地狱吧。这种场面自然会将心智健全的祖父拖入永无止境的噩梦中。单是看作家们对战场血肉模糊、蛆虫遍布的惨烈场景的描绘就会心悸的我也不必多说。直到我了解了这背后的背后所暗含的险恶真相——如果那份资料落入某些狂妄自大的官员手中,一定会掀起恐惧的浪潮,造成难以估量的惨重损失。
我快要抑制不住冲动了。在此之前,我将写完这篇手稿并妥善安置它。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请你毁掉它吧,无论你看完与否,请将它撕碎,丢入火堆。我没有再继续隐藏这个秘密的勇气了。我恳求你。
如同好奇的潘多拉打开魔盒一般,我在三年前拜访寡居的祖母时发现了藏在床底的古老木箱。箱子用的木材不甚优质,枯朽得很厉害。祖母所说,祖父在世时从未提到过这个箱子。箱子的发现纯属意外,我在帮助祖母打扫房间时,拖布卡进了床底的一条缝隙里。这条缝隙让我这之后的三年都处于不得安宁的无定状态。我原本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只有用命运才能解释我的遭遇。恶毒的命运三女神在纺纱时就早已构思完成了以我为主角的悲剧故事。
我探进床底,下面似乎有擅自改装的痕迹。这是我的祖父生前少数的几个爱好之一。很快我就确定拖布陷入了地板上的一条狭窄缝隙中。我挪开床,清理干净不知多久没动过的积尘的床底,发现了一块明显是后来压上去的石砖。从灰尘的厚度来看,这块石砖在被放下去之后就再也没有被抬起来过。我本该记得祖父过去对后人最后的警醒——石砖上没有安装把手,说明他想将这个秘密永远埋葬,而我在可怖的悲哀命运的驱使下发现了这个地方,并打开了它。
祖母早是皈依佛门之人,对我发现祖父隐藏的遗物并没有太大情绪上的波澜。她未向我质询,相信了“军旅日记”这种蹩脚的谎言,任由我将石板底下的箱子转移走。不知名的读者,我有一个请求,如果你读完了这份记录,请不要打搅我的祖母。她或许知道一些,但肯定没有可悲的我在这里记录的多。请不要打搅她的生活。
箱子是用一个古老的扣栓结构锁住的,大概是我祖父年轻时的作品。扣栓用的金属块早就已经锈在了一起,锁孔也早已被铁锈堵得严严实实,更别提我根本没有找到的钥匙了。我于是用榔头敲开了早就枯朽的箱身,保留了扣栓做纪念。
箱子里方方正正地放着一个包裹,用似乎是降落伞布的防水布料细心地缠裹。内部是一个铜盒,盒子上印着“工农阶级必胜”的红色标语和版画。盒子里是一些信件、资料和几个更小的盒子。现在我一想起那个画面就毛骨悚然,而那时却不自知。
我的祖父属于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出身,并不识字,这铜盒中的信件他并不能看懂。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放进盒子,然后在最隐蔽的地方将资料隐藏?如果是国家机密,那早就应该烧掉了。好奇心驱使我翻阅其中的信件。
按照顺序,第一封信的落款时间是1964年6月,寄信人署名“王瀚索”,收信人“首长”。原件早已在我的打火机前化为烟尘,现在只能凭记忆还原那封言辞恳切的劝谏信。
————————
尊敬的首长:
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并通过您的警卫员将信递交给您,完全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小小地向您的警卫员撒了个谎,让他将这封十万火急的信移交给您。我谨代表我个人,恳请您拖延行军部队进入西藏的时间。
倘若这只关乎我个人的利益安危,我大可不必写这封信给您,徒添日理万机的您的烦恼。而如果在没有处理掉“那个东西”的情况下就入驻布达拉宫,这将会是一场灾难。会有无数的战士为此牺牲,同时造成人心惶惶的舆论局势。这对一路高歌的革命事业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这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
鄙人名为王瀚索,是一个对西藏、印度、尼泊尔地区的语言和历史小有研究的学者。我出生于1896年,后来成为了少数赴美留学的学生。我曾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读书,后来又在阿卡姆的米斯卡托尼克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毕业以后我回到祖国,希望为强国事业添一份力。几十年动荡之后新中国成立,我有幸成为了西藏学术问题的研究组长,负责记录西藏的各项事宜以便入驻。
首长曾在莫斯科居住了很长时间,想必也有很多学习,不知是否对那本疯狂的《死灵之书》有过了解。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当初阅读此书时一笑了之。直到我们团队在整理西藏寺庙中的典籍时,我们才发现了其中令人无比惊异的巧合。
《死灵之书》的作者是八世纪阿拉伯人阿卜杜拉·阿尔哈萨德。他是一个疯子,但他的疯言疯语却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在书中写到的“米-戈”与似乎不愿多提的可憎生灵“煞地极”都和大昭寺中最秘密的典籍(我队通过一些特殊手段得到了其中最古老的文书)有着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
西藏地区的平民和农奴似乎对这两个名字有着异乎寻常的恐惧。关于“米-戈”的描述类似于欧洲探险队在十八世纪时所说的喜马拉雅山雪人的故事,以及1928年前后以艾尔伯特·N.威尔玛斯为首的关于美国佛蒙特州奇异怪物的论战。而对于“煞地极”的恐惧更是如同根植于他们的血脉之中,提起这个名字连少不更事的藏族少年也会骨寒毛竖。
据典籍上记载,“煞地极”幽居于一个黑暗的石窟里,上古时期以人为奴,食其血肉与恐惧。伟大的格萨尔王将其击败,囚之于洞中。但煞地极拥有无穷的生命,会挣脱囚禁,向人世散播疯狂与恐惧。此时需活佛高僧现身,用秘法将它定住,并举行危险而血腥的仪式:高僧静坐于囚有煞地极的房间,煞地极会试图侵染高僧,高僧则要在它“涌入口鼻”之时死死咬住它,并用鲜血作法将其收入坛瓮,七七四十九位铁棒喇嘛念秘咒三天三夜加固封印,之后将瓮放入深邃无人的洞窟深处。
我在美国时参观过一些博物馆,曾经看过掳掠而来的古印度和古尼泊尔文献。这些几千年前的古代文献也提到有叫“tha-dva-jña”(古尼泊尔则是“jā-ke:dʒɚ”)的邪恶生灵带来的灾难。上古魔书《伊波恩之书》中写到魔物“Sareadge”,其中对它的描述十分瘆人:在万古以前,Sareadge就已经存在,它以人的血肉与恐惧为食。恐惧的极致不是恐惧,而是镜子。相传西藏的番僧可以制住这等扭曲的生灵,但它是不死的——或者说,在本源的恐惧面前,连死亡都会退却。
之后的情况实在过于惊悚,十七人的考察团里有十二人神秘失踪或死于非命。我有着充分的证据表明那只贯穿历史的无名邪物已经醒来。我们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编队来协助圣僧封印上古魔物煞地极。
王瀚索
西藏拉萨书/十万火急
1964年6月■日
————
接下来是信封。信封的外围用特质的胶水粘着一张“十万火急”的红色牌子。在上个世纪,这种贴有“十万火急”的信封将会在七天内送达国内任意指定地点,十分稀有。但当时的我认为王瀚索教授患有精神方面的隐性疾病,高海拔地区引起的高原反应作为诱因将其爆发出来,浪费了一张十万火急令。但现在的我只能想,在窥视了阴影之下荒诞的真相后,发疯才是最美好的归宿。
那个“首长”的回信耐人寻味,他确实派了一支小队去解决事端。我想当时他也许是想将发了疯的王教授抓起来,换一个人来完成这项工作。下一份资料是名单,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了。我曾就着名单一个一个找到那些人——如果他们还在世且神智正常——去询问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名单上记着科考人员和护卫队成员,我的祖父就在护卫队里。
护卫队成员有三分之二死于这场劫难,这促使首长紧急变更了任务。在协助下,高僧成功用秘咒束缚住了那个恐惧的化身,将它装入了净体金瓶中。任务圆满完成。
唯一不圆满的是,第二年伪流亡政府建立,后来还引起过数次骚乱,而那个封入金瓶的洞窟被列为了军事禁地。
也许你不会相信我所叙述的一切。那你又如何能解释那些死去的人在再次见到家人时只剩下骨灰了呢?为什么幸存者除了贼王阿铭和我的祖父,都被绑了束缚带,关进了精神病院呢?是什么让我的祖父在腹部有一个无法愈合的贯穿伤口,又是什么让贼王的整条右臂消失呢?
是的,我查到了。疯狂的《死灵之书》中提到,那狡猾的不定形黑暗,倘若吞噬了施术者,便会变成施术者。谁说那个活佛高僧仍活于世?在荧幕前微笑的和蔼光头怎么可能是救世主?煞地极侵染了他,将他痛苦哀嚎的灵魂塞进金瓶,让他的凄厉惨叫回荡在永世黑暗的无人地穴。
你以为我什么都没做吗?不,我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做,放任那匍匐蠕行之混沌的最险恶的眷者滔乱世界,享受盛宴?怎么可能?我化名前往美国,前往活佛下榻的旅店。我从通风管道进入,枪杀了他那不知能不能称为人类的随从,来到微笑着看着我的活佛面前。我开枪把他的脑袋打成血窟窿,用刀剜出他漆黑的心脏,把他的肢体搅得七零八碎。
无人发现。那位不可称呼的神祇喜爱混乱,我用混乱取悦祂,祂用祂的权柄帮我用混乱终结混乱。但是——
但是第二天,那个活佛依然完好无损地站在摄像机前,两个随从的脑袋光洁如新。不死的!它是不死的!恐惧未消,它怎么可能遭到死亡缠绕!混乱之神与它忠诚的眷者握手,相视而笑,它正谋划着让整个世界堕入混乱。活佛对着摄像机,笑着双手合十。
他是朝我合十的!我的身上沾了煞地极那恶臭的血液!我会被转化,成为它无比忠诚的信徒来传播混乱!
我在我的身上浇满汽油。写完这些,我将用火焰消除掉身上所有的恐惧和疯狂。
你会认为这是疯子的绝笔。噫!我有可能是疯了,自从那场未遂的谋杀……或许你会觉得那场谋杀并不存在吗?
躺在箱底的信是写给我的祖父的。
————————
亲爱的宗甫:
你们可真会错怪人!我只吃了十三个,你们却硬要说我吃了你们十九个人。你们当然没困住我。时代早变了,我将用新的方法猎取恐惧、混沌与血肉。没有人能阻挡我。你很厉害,但你无能为力。
煞地极
————
随信的盒子里装的是一双眼睛和一块舌头的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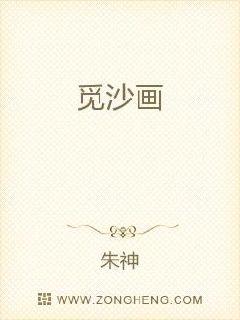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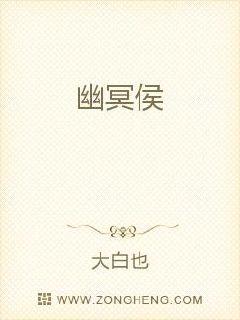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