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闪现
马车行驶的极快,风在我们耳边呼啸而过,天上突然闷了一道亮眼的闪电,身后响过几声惊雷,地上震了几下——地下的兰城消失了。
李大龙闭上双眼,两行清泪,无声的从他脸颊上滑落。
我摸不清他对时宸的情愫,是知己还是曾经并肩的同伴,夜半无言,直到天将亮我们才回到了珞城。
刚进城门,李大龙用一件斗篷将夏青遮了个严实,趁着天还未亮透去了城中一户郎中家中,这位郎中姓钟名癸,自成年之时患有眼疾,终日以黑布掩目。但钟癸的医术是闻名于附近数城中的,能医治许多旁人医不了的疑难杂症。
我继续驱着马车往翠姨的住处赶去,我对赵蜀人讲了翠姨的近况,他把腿搭在马车边上猛吸了一口旱烟,道:“冤冤相报何时了。”
将赵蜀人送回家中,我又只身来到铺子中,明日就是初七,会有寄存人来店中,我得提前打点好每一块尸皂。
刚近店门,一盒油皮纸包裹得点心系在门闩之上,我将点心拿进门,打开一瞧,是城南芝丰园中的蛤蟆方酥,四角方方正如点心的名字,表上一层满口香的大颗芝麻粒,配上内里绵白糖的甜劲,一口下去尽是香甜酥脆。
我正疑惑着是谁拿来的这盒点心,又看到随着点心盒绳子上附了一封信,我打开一瞧,原是冯闻跃和柳甜甜来信,信上写着自从上次一事,俩人生活已然平静恩爱,近日登门致歉却发现店门紧闭,现特送一盒哈蟆酥聊表歉意。
我心中一喜,近日疲乏的身子也顿时轻快不少,我放下屋内的帷幕,打开店门,阳光刚好照到门槛,让空气流通进来,给生人逝者都留有一些新鲜之气。
逆着光影从巷子中走出来俩人,我眯着眼瞧着,待他们走近,发现是冯家夫妇,手里正提了一盒印着丰芝园三个红方底黑字的点心,我转头瞧向屋内,帷幕正挡着,但桌几上正摆着一样的蛤蟆方酥。
我愣了神,此时冯闻跃已经走向前来,说:“林先生,连接登门了几日,都未见到你,还以为今日又见不到你了。这才致信一封,现下也用不到了。”
说完,冯闻跃将随着点心盒的信抽出,我忙拦道:“冯公子且容我一瞧?”
冯闻跃将信递于我,我打开一看,跟刚才我看到的那封信上的内容一模一样。
柳甜甜见我有些呆状,将手在我眼前一挥,“林先生?”
我回过神来笑道:“屋里请。”
我关上门,将帷幕卷起,拿椅子背上的褂子一遮,挡住了桌子上的蛤蟆方酥,“近日出了趟远门,桌子上有未收拾尽的杂物,有碍眼观。”
“林先生客气了。”冯闻跃坐定,告诉我他和柳甜甜打算远离珞城,决心重新来过。
“那孙小姐的尸皂……”我问道。
柳甜甜开口道:“我们此次离开珞城,想将我父亲的绸缎生意做远一些,每月的初七、十七两日来回太为频繁,此次正来,想问林先生可有解决之法?”
我站起身,来到隔间,从存放鞋子的柜子中取出冯闻跃送来的鞋子,说:“冯先生,三月时间未到,孙小姐的尸身还未缩至到这鞋子中。若你不做这单生意,我可将孙小姐的皮骨复原。”
冯闻跃和柳甜甜商量了一番,带走了孙钰儿的尸首。我送走她们,揭开罩在桌子上的褂子,捡起一块蛤蟆酥,陷入了沉思。
李大龙和夏青来到了钟癸医馆中,钟癸问明了夏青嘴部病因,当即调了一副方子,让李大龙照着方子抓药,药材铺在蓝瓦上煎,烧成干状碾成粉,再调入钟癸给他们的药膏,敷在夏青嘴上,不出十日,便有成效。
李大龙千恩万谢于钟癸,正想寻问酬金时,钟癸先开了口:“钟某不要金银,也不要珠宝。”
“先生这是……”李大龙试探道。
钟癸摸索着桌角,借力站起身来道:“我要你最后的这身皮。”
李大龙惊道:“先生怎知?”
“一点小伎俩罢了。”钟癸笑道,“眼睛无用的人,耳朵倒是灵巧的很,不瞒你说,这张皮,是我们这些医治怪病之人求不来的好药材,我对你也是早有打听。今日你一来,脚步声比普通人轻上很多,想必是个习武的高人,又听到夏姑娘叫了你的名字,就对上了号。”
李大龙又惊又恼,他没承想竟然有这么多人惦念着一个死人皮,这张死人皮还要入药,更是没想到他们早已打听到自己的底细,就等着自己死呢,这算什么医者。
但他也不好发作,看了看一旁的夏青,咬了咬牙应承了下来。
他将夏青安顿好,来到铺子中找我,商量赵蜀人杀人案一事。我看着他说:“杀人偿命,理所应当,但是赵叔杀的是俩个刁难过重黎的人,你说杀得不杀得。”
“这事就这么算了?”李大龙咂咂舌,他的内心跟我一样矛盾,既希望赵家夫妇能脱身,又过不去心里的坎。
想来想去,我们决定还是先找赵蜀人商量一下,但是刚推开赵家的门,两根小孩腕粗的草绳上吊着人,我和李大龙忙将人救下,但赵家夫妇气脉皆断……
俩个月后。
夏青头戴一顶小花蕾编成的花冠,一袭白纱,手上套着一双白绸手套。迎面站着的是穿着新式西服的李大龙,眼窝里攥着泪儿,俩人正式结为夫妇。
这场新式婚礼引来不少的人围观,还占了《珞城时报》的半壁篇幅。
来采访的记者中有一个时姓的民生部的副主编,身材高大魁梧,一张脸却白俏细致,一对丹凤眼吊到眉梢,但眼窝还有些深,整个人看起来带着几分天真几分认真,又带着几分心机几分肃杀,具体要呈现什么性格,倒要全依赖他自己表现出的神态。
新娘的捧花一抛,此人跟我撞了个满怀,他护着他的宝贝相机,我伸手够着捧花,两人相叠,墩坐在了地上。
众人嘻笑着将我们搀开,我向李大龙扬了扬手里的捧花,与之会心一笑。
参加婚礼的宾客散去,我与几个熟人送走亲朋,互道了告别的话。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扯开脖子上系着的领结,这新潮的衣服我也是头一次穿,有些不习惯。
正在此时,有人拍了拍我的右肩,我转过头去,是一个鼻子修长的男人,我眼睛里尽是他那尖又长的鼻子,好似离我再稍近一些,便要触到我。
我后退两步,“先生何事?”
来人“嘿嘿”一笑,“你身上的味道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我的目光扫到他衣领里窝着的红掌花碎瓣,又看向他的眼睛,我心里疑惑,这不是刚才的时记者吗?这世间万物,虽有能人善变化易容之术,但每个人身上至少留有一处,还是会显露自己原本的面貌癖性。
未等我问出口,时记者又是“嘿嘿”一笑,那尖细的鼻子立即缩了回去,变成了一挺与他面貌相趁的驼峰鼻了。
看他的样子,并无恶意,我也报之一笑,“这鼻子伸缩如常之术,林某人佩服。”
“你姓林?我看你年纪也就二十出头,我肯定年长于你,我直呼你名字罢。”时记者倒是“自来熟”,还未等我应允,又问道,“林兄弟家中几人?姓名为何?现又哪里高就?”
我慢条斯理道:“时记者虽自顾说年长于我,但瞧模样也仅有二十有余。”
“我们做妖怪的,脸上的皮囊之色怎能与常人一致。”时记者倒也不遮掩,直接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我知道你不是人,但也不像鬼,你到底是什么?”
说罢他又凑近我嗅了嗅,摇了摇头,“我怎么闻不出来呢?”
我也来了兴趣,直说道:“鄙人姓林名慕青,家中仅我一人,现经营着一家寄放尸体的铺子。至于自己,是人是鬼还是其他妖怪的,你若问我,我也扯不清楚,反正是与一般人不大一样。”
时记者也自报了家门,“我姓时,叫时陋,家住南坛大街358号,是个穿山甲妖,现在《珞城时报》担任民生部的副主编。”
此时,跑来一个脖子上挂着双镜反光相机的人,气喘吁吁的说:“时编,城东船楼二户的王奶奶家的猫跟城南汪大爷家的狗在一起了。”
“这关我们民生部什么事?”时陋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与刚才判若两人。
来人继续喘道:“王奶奶跟汪大爷因爱宠生情,家里儿女反对,现在正闹殉情,安眠药都吞了好几片,现在都送到民安医院了。”
时陋拔腿便跑,“林先生后会有期。”
我看着时陋远去的背影,感觉这人还不错,嘴上不觉得露出微笑。
我继续向前走着,发觉刚才随手解下的领结已不在衣兜中,想必是刚才落在了路上,我便返身找去,在石子路上,看见了领结。
一个人拍了拍我的右肩,我转头看去,是鼻子又变得细长的时陋,我问道:“怎么又回来了?”
时陋喈喈一笑,“你身上的味道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的脑子里顿时像炸开了一场盛大的烟火,眼前的人和事物放大了数倍又渐渐缩小,反复几次,我已然乱了阵脚,我顾不上搭话,转身跑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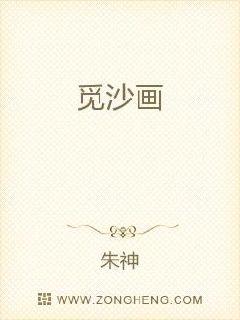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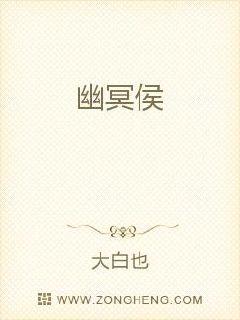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