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生的梦魇
孩子和父母分离应该是依依不舍,但无雨却感到分外地轻松。假期终于结束,新学期在无雨的期盼中来临。
无雨和季洁、宾书每天还是忙着学习、谈理想、看电影。
每周学校大扫除都很凑巧,无雨总是被分配到擦窗户的任务。个子矮小的她每次都要在课桌上放一个凳子。即使踮着脚踩在凳子上,还是够不着最上面的窗户玻璃。
幸运地是,季洁和宾书每次都会帮忙,这次也不例外。
无雨头上仍然戴着那个青苹果发卡。季洁头上戴了几个亮晶晶的发卡和彩色发箍。
无雨擦着窗户,回头看了看忙碌的宾书和季洁,眼睛湿润了。
季洁问无雨:“眼睛怎么红了?眼病又犯了?”
“不是。一粒沙子进了眼睛。”无雨垂下眼帘,擦了擦眼睛,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
“无雨的眼病应该已经好了吧?”宾书把抹布递给季洁。
无雨笑了笑没说话。
“寒假妈妈带我出国了,可好玩了。”季洁在水桶里搓了搓抹布递给宾书。
宾书说:“我和弟弟去了海边。爸妈买了好多礼物给我们。也有你们俩的礼物哦。”
“我爸妈也让我给你们带礼物了。”季洁看了看无雨头上的青苹果发卡说,“我妈给你带了好多漂亮发卡。”
“我妈和姐姐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无雨咬了下嘴唇,“我妈说叫花子才要别人的东西。”
季洁一脸的愕然。
“无雨,寒假过得怎么样?”宾书问。
无雨轻声叹气:“唉,一般般。”
“我是卫生委员。”季洁看了看窗户,说,“嗯,窗户擦得很干净了。无雨,你可以回家了。”
“今天是大扫除日,王老师会来检查!一定要再擦干净点!”宾书提醒了一句。
每次擦完窗户,宾书和季洁都会躲在楼梯口。王翠英会用白布在窗户上抹两下,再把白布伸到无雨面前让她看看窗户有多脏。不知道为什么,不论窗户擦得多干净,王老师手里白布上总有黑色灰尘的痕迹。
“还是没擦干净,你看看,你看看...”王翠英用手指指窗户说,“这、这、还有这,再擦擦。擦干净就可以回家了。”
王翠英老师离开了教室。无雨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6点多了。天边的晚霞如火烧般通红。
擦完窗户,无雨背着书包,拿着下午摘的大把映山红和宾书、季洁开心地骑车回家。
宾乐坐在单车上,停在岔路口,向季洁和无雨招手告别。在橙红的夕霞衬映下他像油画中的人一样。
季洁和无雨抱着大把的映山红进了季家院子。
季外婆剃了光头,戴着帽子,坐在院子里打毛衣。她的病情开始恶化,这一阵都在医院化疗。
季外婆看到俩孩子,脸上露出笑容。“回来了!”
“外婆,我最爱你。”季洁抱着季外婆亲了一口。
无雨把单车靠在树下。单车后座上的书包打了几个补丁,“忍者神龟”的图案已经模糊不清。
“小雨,我今天买了几个新书包。你进屋随便挑一个。”
“不用了,外婆。我妈和姐姐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无雨抱着映山红坐上秋千,脸上笑开了花。
季外婆问:“外婆我是别人吗?”
“谢谢,外婆。你的心意,我心领了。”无雨慢慢荡起了秋千,“我喜欢这个书包...让我有回到童年的感觉。”
“这孩子…”季外婆笑着向屋子走去,“马上开饭了。”
季洁问:“外婆今天吃什么菜?”
“你们最爱吃的剁椒鱼头。”
“外婆万岁!”
“还有板栗烧鸡!”
“耶!”两个孩子欢呼着。
季外婆哈哈大笑走进屋子。
季家房子非常大,光是客厅就比无雨家大两倍。家里所有家具、电器都是进口货。客厅里摆着两张超级大的白色真皮沙发和花梨木大桌。一个桌子上摆着麻将,一个桌子上放着几个新书包。屋角摆着一架白色大钢琴。
季外婆走进厨房。两个保姆正在做饭。
季洁和无雨边荡秋千边开心地笑着。
无雨嘴里哼着小曲:“山顶有花山脚香,桥底有水桥面凉;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
“你老哼这曲子。到底是什么歌?”季洁好奇地问。
“不记得了。小时候听过的一首歌,”无雨低头闻了闻映山红,“歌词就在嘴边,可怎么也想不起来。”
“吃饭了!”保姆跑出来喊道。
俩人争先恐后地跑进屋子,坐在饭桌前,端起碗就开吃了。
“洗手!先洗手!我的祖宗耶!”季外婆唠叨着。
俩人大笑着跑进洗漱间。
无雨几乎每天都在季家吃了晚饭才回去,享受着季家的亲情。但美好的生活从这天之后嘎然而止,没有一点预兆。没有狂风暴雨,没有闪电雷鸣。13岁的无雨万万没有想到,噩运悄然来临。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无雨的眼病又发作了,双目通红。无风和往常一样陪着无雨去医院看病。看似平凡的一天竟然成为无雨人生悲剧的起点。从这天开始,所有的努力、奋斗、梦想、希望、友情甚至亲情都化为乌有。
五官科诊室门紧闭。走道上除了姐妹俩,空无一人。头上的青苹果发卡有些掉色,夹子也有点松了,时不时往下滑,无雨把发卡取下重新戴在头上。
平日这个时候医生已经来了,但今天迟迟未出现。无雨担心迟到太久会被老师骂,等得有些着急,于是问姐姐:“唐医生怎么还不来?”
“还早呢。再等等。”无风看了看手表。
窗外鸟儿清脆的叫声此起彼伏。
无雨走到窗口。窗外绿树郁郁葱葱,显得生机勃勃。一只白色小鸟站在枝头上“咕咕”鸣叫着。
太阳从窗户照进来,仿佛将窗外的生机带入了走道。
无雨闭上眼睛,仰头深吸了口气,享受着阳光的沐浴。
楼梯口传来“咚咚”脚步声。
无雨回头一看。唐红其提着黑色公文包,从楼梯走上来。
俩姐妹忙和唐红其打招呼。
“眼病又犯了?”唐红其笑着从口袋里掏出钥匙。
无风答应着:“是!”
唐红其边开门边问:“你们父母还在外地打工?
“是!”无风答应着。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无风回答:“过年的时候。”
唐红其打开诊室的门。无风、无雨跟着他走了进去。阳光从窗户照进诊室。整个屋子显得通透明亮。
无雨抬头看了眼诊室墙上的挂钟,7点31分。
唐红其把门关上,把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从门后取下白大褂穿上,坐在椅子上,戴上头镜,打开墙壁上的灯,翻动无雨的眼皮。
“你今天请假了没有?”唐红其问无雨。
无风说:“我帮她写了请假条。她到学校拿着假条和病历给老师看。”
“今天第一节是什么课?”唐红其又问。
无雨看了眼无风,轻声答道:“英语课。”
唐红其的脸凑了过来,鼻子里的热气喷在无雨脸上。
“眼睛朝右看。”
无雨眼珠转向右边。
唐红其说:“左。”
无雨眼珠转向左边。
唐红其说:“上。”
无雨眼珠转向上边。
唐红其说:“下。”
无雨眼珠转向下边。
唐红其看着无雨的眼睛,问:“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英语老师叫王翠英?”
“是。”无雨轻声回答。
唐红其又翻了翻无雨的鼻子、耳朵。
“王老师的课上得怎么样?”唐红其问。
“很好。”无雨轻声说。
无风问唐红其:“唐医生,她这眼病反反复复发作。有什么办法根治吗?”
“她这眼睛的毛病叫'春卡',”唐红其把头镜取下来放在桌上说,“青春期卡他性结膜炎,属于内分泌失调。过了青春期就好了。又不传染,问题不大。”
“不传染就好。”无风笑着说。
唐红其戴上听筒,说:“把棉袄脱了。我听听你的心肺功能。”
无雨看了眼无风。无风点点头。
无雨嘟着嘴低头把棉袄脱了。
唐红其拿着听筒在无雨胸部来回移动。
无雨害羞地低着头。
“嗯,心肺倒是没问题。但你这眼睛发病的频率有点高,我担心是糖尿病。我检查一下你淋巴有没有问题。”
唐红其用手摸了摸无雨下巴。
无雨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
唐红其问:“痛不痛?”
无雨摇摇头。
唐红其又问:“有什么感觉吗?”
无雨摇摇头。
“说话呀,哑巴啦?”无风说。
无雨低下头轻声说:“没有。”
唐红其的手顺着无雨的脖子往下摸。无雨涨红着脸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唐红其说:“抬起头来。”
无雨不情愿地抬起头,看了眼无风,垂下眼帘。
唐红其摸了摸无雨锁骨沟,问:“痛不痛?”
无雨摇摇头。
唐红其说:“把毛衣和裤子脱了。”
无雨愣了下,抬头看着无风。
无风笑着说:“没关系。”
无雨嘟着嘴慢慢地把毛衣脱了。
无风催促着:“快点,你还要赶去上学。”
无雨低头把裤子脱了。
唐红其紧紧盯住无雨的脸,观察着她的表情。
当唐红其的手伸向她的时候,无雨顿时全身僵硬,脸成了猪肝色,低头看着地板,产生了幻觉。
周围突然变得漆黑一片,无雨发现自己站在万丈悬崖上,有头狼在后面追赶她。悬崖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海水是黑色的。
狼向无雨狂奔过来,她吓得直往后退,失足跌下悬崖,掉进大海,挣扎了几下便悄无声息地坠向海底。
狼站在悬崖上发出低沉的嚎叫声。
唐红其说:“好了。“
无雨陡然回到了现实。方才阳光满屋的诊室变得阴森森。
“你现在可以穿上裤子了。”唐红其轻描淡写地说。
无雨涨红着脸低头背对唐红其,穿好衣服、裤子,一脸要哭的样子。
“快点!”无风催促无雨,“已经7点50了。”
“你身上的淋巴是没问题。但还不知道是不是糖尿病。”唐红其边写病历边说,“这付中药的吃法、外用药膏、眼药水的用法和以前一样。药吃完了眼睛还没好的话,你们再来找我。庆大霉素注射一天一次。”
“谢谢,”无风转头看无雨,“无雨…”
无雨低头没说话。
“怎么这么没礼貌?”无风有点上火。
无雨低头说:“谢谢。”
唐红其打开诊室的门。“如果下次眼病还发作,我给你好好检查检查。到时我再给你们开个新方子。”
无雨红着脸跟无风走出诊室。
“无雨,等等!”唐红其叫喊了声。
无雨身子抖了一下,站住没动,也没回头。
无风转身看着唐红其,满脸笑容。
唐红其指了指他脚下的青苹果发卡。
“你的发卡掉了!”无风对无雨说。
无雨仍然一动不动。
无风走到唐红其跟前,蹲下捡发卡。
唐红其低头看着蹲在自己跟前的无风,脸上露出笑容。
无风捡起发卡站起来向唐红其道谢,把发卡递给无雨。
无雨没伸手去接。
无风把发卡塞进她上衣口袋里。“傻里傻气的!”
无风拉着无雨的手离开诊室。走道的阳光不见了,一片昏暗,似乎没有尽头。
无风说:“没关系。这很正常。医生不都是这样检查身体吗?”
无雨嘟着嘴,低头不语。
门诊大楼里黑暗压抑,到处都是穿着白大褂的人。无雨环视四周,松开无风的手,低头垂下眼帘。
买了药之后,俩人骑单车分头离开医院。
无雨感觉像是刚从刑场出来,心情极其沉重。羞耻感像千斤石头一样压在她的心头。都说时间可以治愈伤口。但无雨今天受到的身心伤害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点一点消耗着她生命的能量,吞噬着她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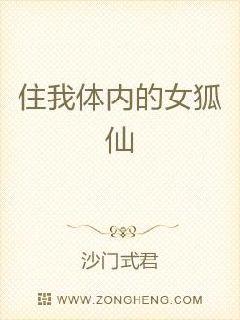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