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不靠谱
记不清,防震棚里到底住了多久。
后来,大家见没再地震,就都慢慢搬回家住了。
而那段日子,终生难忘……
村里拆了防震棚没多久,早晨的田野竟有一层白霜,恍如浅浅的白雪。
还是出事了。
真让我们村的半吊子阴阳——海子爹说中了,天人有感应呢。
天崩地裂,巨星陨落,寰球震惊,举国哀思,人民群众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这一年,注定不平凡。之后年末,在一片欢呼声中,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关于太岁的事儿,好像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大家都淡忘了。
改革春风吹进门,全国人民抖精神。
又一年,我们村包产到户,日子马上变了样,穷人家里开始有了余粮。
在高楼万丈平地起的歌声中,我走进了石房村小学一年级的课堂。我也有了大名。
书本皮上,都写着呢:石房村小学,一年级,石小山。
我妈说,要按算命先生的说法,我命里喜土。
我爸望着门前的山头,略一沉思,就叫小山吧,于是我从二蛋变成石小山了!
深秋初冬的蓝天下,田间屋旁,一颗颗柿子树,脱光叶子的枝丫,显得格外沧桑而古朴。每颗树顶都挂着几个红彤彤的柿子,分外耀眼和诱人。
我问过爷爷,每颗柿子树上都要留几个柿子,为什么不全摘了。
爷爷说:“好事不能占尽,坏事不可做绝。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规矩!”
“树上的柿子,总要留几个给老天爷,麻雀乌鸦啊的一些鸟儿,就靠它过冬呢。要是摘光了,明年树就不结果子了。”
我不大信,但也记住了这是规矩。以后摘果子,也总会特意留几个在树上,规矩就是规矩。
深秋的暖阳,染红了满山红叶。种上冬小麦,晾晒好黄豆,收了红薯入窖后。乡亲们像长了膘的羊群,生活的节奏也慢了许多。
农闲人不闲,今年农历年闰四月,在闰年为家中老人打棺材增寿。
我爷爷奶奶都早已过了六十大寿,爸爸和叔伯姑姑们商量,在今年为老人准备好寿木。早早就让海子爹选了日子,当时农忙,在四月初就先了破木,到有空再开始做。
做寿木也是有很多讲究的,首先就是要找活做得漂亮的木匠。一般的木匠还干不了这活路,这一带棺材做得好的木匠,屈指可数,我本家大伯就是其中拔尖的一个。
大伯不光木匠活好,他也是这一辈中的老大,性格开朗,为人热心,很受乡邻们的尊敬。
我爸年初就向大伯提起准备做寿木的事,大伯很高兴地满口答应:“给我叔做寿木哩,再忙都要先给咱自己人做了。他八叔,准备用啥板木做?”
我爸在本家兄弟中排行老八,年龄要比大伯小好多,但哥俩敢情很好。爸爸笑着说:“我平日离家远,不常在家。老人也没享过几天福,这两年日子宽松一点了,想用柏木的,前些年也准备了一些,估计还差不少。我也不太懂,你给看着张罗就行。”
“好,好,用柏木好”。大伯一脸兴奋。看过木料后,大伯用铅笔列了张要准备的木料油漆等料单,约好在闰四月先破木,秋后动工。
秋后忙完农活,我爸特地从县城回家一趟,安排给爷爷奶奶做寿木。别看就做两口棺材,但农村极讲究,请阴阳先生,择吉日,要纯木工卯榫结构,不用一颗钉子,雕刻福寿图,刷漆上油等,工序相当复杂。为老人尽孝增寿,也为子孙添福......
紧赶慢赶,也要两个月左右才能完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在石房村也只是口号。
放了学,我也不在路上玩耍。匆匆赶回家,帮大伯递工具,拉墨斗。在石房村用纯柏木做寿材,就是顶好的了,且不说柏木材质紧密耐腐,光是那独特的香味闻着也是一种享受。
大伯很享受这好木材做活的过程,不紧不慢,有条不紊。
木工是门手艺活,我也爱看这些木料在锛刨斧凿,火烤漆粘中一步步成型,但更爱听大伯在干活中唱戏说书讲故事。
大伯讲的故事和海子爹讲的故事不一样,大伯的故事不像海子他爹讲的古灵精怪,大多是戏文和说书类的,讲到高兴处,还时不时唱几嗓子。
什么“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头带亮银盔,身披黄金甲,胯下千里追风马,手拿虎头夺命枪”......
大伯有说有唱地讲故事,听起来过瘾,记起来也容易。我觉得大伯是个能人,有手艺,有文化。无论男女老少和谁都能聊得来。我有什么听不懂,大伯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长子长孙,顶门立户。
大伯在我们石家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承担更多。关于家族的事儿,大伯很尽心,他们这一辈本家堂兄弟十人,在兰河一带不算大家族,但也不小。大伯做寿木的空档,在联系春节操办“家会”的事。
在帮工之余,我片段地听到,他们商量操办家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修家谱。
“国有史书,家有宗谱,认祖归宗,人之常情。”说起家谱,大伯总是这样开始的。我才知道,原来我也是有家谱的人。
在大伯家主屋的墙上,一直挂着石家的家谱。据说是明朝洪武年间,石家先祖由山西大槐树迁至洛阳涧西,其中一支在清嘉庆年间又迁至这里。挂在大伯墙上的家谱,就是涧西石家的支谱,支谱的开谱始祖就是清嘉庆的一世始祖公,到大伯他们这一辈是第七代。
首先是名字,大家紧跟时代潮流,取名多有这个时代的特征,已经把家谱的规矩丢到一边去了。
“举家世贤,维振方兴”,大伯强调这是家谱规定的起名用字,并解释说我爷爷的爷爷辈,也就是高祖是“家”字辈,曾祖用“世”字;六个爷爷是“贤”字辈,名字一个不差。伯父们名字还很一致,是“维”字辈的,名字中间都有一个“维”字,但我小叔石援朝是个例外。到我们这一辈就更乱套了,只有大伯三伯家的孩子全是按族谱的“振”字取名,其余的全是乱弹琴。
像我的名字,石小山,这就不靠谱,都上不了家谱,入不了祠堂!
“不靠谱,那咋办啊?”
“你石小山,这个名字,只能叫小名。”
“我小名不是叫二蛋么?”
“二蛋那是乳名,名字可讲究着呢。你听古人都有名号的:关羽关云长,人称关二爷;赵云赵子龙,人称常山常胜将军赵子龙。”
“那我这名字不靠谱,咋办?”
“那就要正正经经拜祖先,按规矩,起大名后,才能上家谱。人常说你尊姓大名,小名大名就是这么来的。大名才是正式认可,有据可查的。起名这事,不用你操心,是你爸爸的事。”
“哦…那咱石家祖上是做啥的?”
我记起在学校,屈万才就拿过两枚袁大头,用两个指甲盖掐着袁大头的中间,对着银元用力一吹,迅速地放到我耳边,说听见嗡嗡声了吧,是纯银的!他爷爷以前是地主,这是他家的传家宝。
“咱石家我知道曾爷爷,哦,也就是“家”字辈的,从清朝的时候开始就是贫农,成分好啊!”大伯不知道我这个问题的心思。
“成分是好,就是穷啊。三年大灾害闹饥荒的时候啊,你爸饿得面黄肌瘦,榆树皮吃光了,就吃观音土,差点都要过继给你四爷了。
你爸没办法,听说县城煤窑招工,就瞒着你爷爷报名下了矿井,你爸也争气,干得好,现在也是正式工了,每月工资都几十块呢”。
一问一答中,我多少有点失望,虽然自己有家谱,在石房村也算是仅有的有谱家族,但祖上几代都是贫农,连富农都没有过,更别提什么官宦名门之后了,当然也不会有传家宝之类的,除非哪天祖坟冒了青烟。
在棺材盖中间打上红线,放了鞭炮,谢了匠人后,寿木终于做好了。
四邻五舍看过纷纷称赞,爷爷奶奶也非常满意。十来个人喊着号子,好不容易才把两具寿木抬起放到堂屋木梁上。
我觉得有点别扭,想着头上就放着两口沉甸甸的棺材,心里就有点莫名的发慌。晚上不敢一个人在家,脑子里不断回想起那些听过的鬼故事。
姑姑们商量着给置办寿衣香表,爸爸叔伯们开始商量坟地的事了。上次因为太岁的事搁下来,现在还得商量咋办?
祖坟选好了,子孙辈才能飞黄腾达。“千人挣钱不如一人睡觉”这类故事,我听了不少。仅石房村这百十户人家,就因为坟地纠纷,吵吵闹闹,甚至打得头破血流的事也常有发生。
谢家祖坟占的好,你看人家兄弟几个都混得牛,老大在省城做官,老二老三在合作社吃官粮。只要有人聚在一堆拉闲话,就常能听到类似的说法。
一命二运三风水。信则有,不信则无。谁不希望自己过得更好一些呢?谁不希望自己的运气更好一些,谁不盼着自己的祖坟也冒青烟呢?
从大伯那里知道祖上并非富贵人家,先辈也毫无任何奇异之处,在内心深处,我隐隐地希望自家也能占个好风水。
但我家起坟,闹出个太岁头上动土,挖出个太岁来,心里就隔应的慌……
这几年虽然没再闹啥事,但心里这个疙瘩还在,问题还没解决。
爸爸说这些是封建迷信,但给爷爷看坟地,这事还真马虎不得。谁家要是敢不请阴阳先生给瞧瞧,还不给乡亲们的吐沫星子淹死!这不是迷信不迷信的事,光是孝道上尽不尽心的说辞,就够受的了。
何况,还有太岁那档子事在呢。
这事不处理好,不光我大娘,我妈不愿意,村子里其他人,估计也不答应,都在看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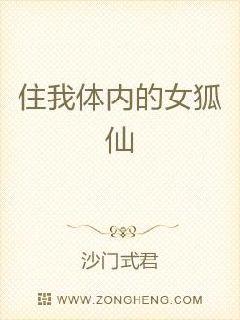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