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阻且长
我不知道一个疯子写作是否被允许,但是作为疯子,我愿意拿笔,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写作?
我热爱写诗歌,却被嘲笑。
我写:我压断了天使的羽毛,
天使说,别在我身边玩闹。
我于是掉下凡间。
天使再不带着我飞,
而是下来陪着我跑。
我幻想拿给同学看,同学嬉笑着拿出去宣扬,然后在我面前撕掉。我才不要。
于是我又写起了小说。
我写:疯狂的骑士举起长剑,可笑的魔术师抽出卡牌。
我的后颈感到疼痛,我的小腹血肉模糊。
我幻想拿给同学看,同学嬉笑着拿出去宣扬,然后说:被割了脖子要挂的。
他们想我死。我才不要。
可我还是想写。于是我又写戏剧。
可是我不会啊,于是我就摘抄: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那么尽管让狂风肆意地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
我幻想拿给同学看,同学嬉笑着拿出去宣扬,然后笑:这疯子是在自喻莎士比亚哪!
我痛苦地用头撞击墙壁、桌子。
这时候哥哥进来,他问我怎么了。
我不想说。
不过我哥哥从不认为我疯了,那我可以告诉他。
哥哥笑,我说你笑什么?
哥哥说你写出来我给你当粉丝啊。
我说,我要写出来了还差你一个吗?
我哥哥鼓励我写。那我就写吧。
我敲下如下内容:
城南花已开——记一个孤独者的独白
舞者飞快地往前跑,衣服在风中鼓成一张帆。
他必须知道时间,但是这里不太对,家里的设施都没有变过,唯独钟表都消失了。但他确定在半小时前听见了教堂的钟声。
家附近没有教堂的,他确定,如果他掉进了轮回怪圈,那么这个怪圈肯定和时间有关。
舞者一路带起的风吹散了潜匿的柳絮,也带起若有若无的花香。
很浅。
是很熟悉的味道啊。舞者突然停下来,猛吸了一口气,耳朵都痒了起来。真是好笑啊,兔子,你走了这么久,我却没变呢。兔子,你看这花香,像不像你啊,怪阴魂不散的呢。兔子,真是过分啊,要是这个怪圈里有你,我怎么可能走得出去啊……
……也许能再见兔子一次啊……
舞者听见有人在抽噎,下意识一摸脸,干的。
哦,不是我啊,还好不是我啊。
舞者又站起来,朝着钟声传来的地方狂奔去。哪怕再看一眼……
教堂塔顶很高很尖,却通体黑色,不确定这是什么宗教的教堂。
他抬头看教堂上巨大的钟面。十二点差十五分钟三十秒。细长的指针是骑士长剑的模样,上面缠满黑色的荆棘,开出诡异而妖艳的花。想了想,还是推开沉重的大门,走了进去。
教堂里不是很亮,窗子里透进来的光都泛出金属的灰色,空气暖暖腥腥的。
兔子,这不是你血的味道吧?在这样的地方见面,看着你死去的话,就有点残忍了啊。
兔子,你不在这里吧?你还在城南那片花田里玩吧?还在收集那些让我耳朵痒痒的花吧?这样的地方,我知道你不可能来的。
兔子,我宁可困在怪圈里也不想遇见你了。
兔子……你凭什么那么早就走啊……
舞者继续往前走,前方恍若有灯火,看得人心头一暖。
走近些,看清是一个个子很高大的人提着灯。
再近,哦,阿努比斯。
“葬神都出现了,是我死了还是有人需要我收尸了?”
“生者,救下那个少年吧。”阿努比斯轻轻颔首,“我已经带回去太多太多人了。”
“多久?我还有多久?”舞者问。阿努比斯很高,舞者尽力昂起脖子,方能看见那颗狐狼头。
“三十秒。”阿努比斯回答。
舞者向前冲去。
又突然停下。
面前有两个人,两个一样的人。
兔子?
左侧的兔子眼睛血红,手中锋利的长剑泛着冷光,另一边的肩膀血肉模糊,滴滴答答地往地上滴着血液。右侧的兔子还是和原来一样,看着弱不禁风,低着脑袋,脸被长剑抹到,破了层皮,渗出了血珠,整个人不住地打抖。
舞者看着兔子,转身泪如雨下。
二十、十九、十八……
“住手!”舞者喊出声,一步冲向前去抱住右侧瘦弱的兔子,“没事了,我们回去吧。”
这拥抱,恍如隔世。
下一刻,痛感从腹部和后颈袭来。怀中的兔子是善于伪装的魔术师,背后的兔子是疯狂的骑士,而舞者就这样相信地把后背和胸怀交给了他们。
“兔子……”
阿努比斯缓缓地走进来,扶起了瘫倒在地的舞者。
“死者的记忆同生者不一样,但是总有楔子。我能帮你的不多。”
舞者站在巨大的教堂前,没有丝毫犹豫地冲了进去。
热热的,腥腥的风扑面而来。
这是兔子最讨厌的味道啊,兔子怎么会忍受的了这么浓重的血液气息呢。要是我有能力,一定要让这里充满花香,哪怕我的耳朵痒都没关系。兔子,我该怎么救你?
舞者经过阿努比斯,微微鞠一躬,径直向前冲去。
骑士举起长剑,魔术师抽出国王牌。
“兔子,你还记得那片花海吗?”
面前的两个少年轻轻看过来,眼波微动。
“那时你最喜欢那里,拉着我陪你去。我闻那花香,一闻耳朵就痒,但是我不告诉你,因为你那样爱那里,我怕你为了我舍弃你最喜欢的地方。我在花田里跳舞,熟悉了那里的一切,却没想过要把你……要把你葬在那里。后来我想,那里也好,你……生前一直很喜欢那里的,我……兔子,你能听见我吗?”舞者的眼泪砸在教堂的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像心中困兽的嗥鸣。
“花。”两个少年齐齐发声。
“是,花,那片花海,你不记得了?”舞者上前一步。
骑士缓缓放下长剑,魔术师收回可笑的牌。
“在哪里的,我想不起来了……”两个少年蹲了下来,痛苦地抱着头。
舞者连忙接口:“在城南,城南的花田。”
“城南……”
当——当——当——当……
教堂敲响钟声,骑士与魔术师在痛苦中化为灰烬。
“阿努比斯!”舞者痛苦地咆哮。
阿努比斯信步走来。
“你要我看着他死多少次……”像是孤独者的呓语,舞者早已泣不成声。
“你若救下他,我们会把他还给你。”
舞者抬起头,脸上满是可笑的泪痕。
“……请送我回去。再来!”
骑士举起长剑,魔术师抽出国王牌。
“兔子……”舞者突然哼起了歌,渐渐成了曲调。
“城南……花已开……”两个少年走到一起,在舞者模糊的视线中合二为一,走向舞者。
阿努比斯再次走进来:“生者,祝贺你成功了。你可以带着返生者回去了。”
舞者和兔子相拥而泣。
外面,名叫兔子的少年在花田中已经躺了三个春秋;舞者也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三个冬夏。兔子的墓碑上写着:一个带不走的少年;舞者的病历单上写着:一个孤独的芭蕾舞者。
舞者重新穿上舞鞋,在狭窄房间起舞。
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那么尽管让狂风肆意地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
城南花已开……
哥哥看完我的文章,说写的真好。
我说,假的,要不然怎么都没有点击量。
我哥哥说真的。
是真的,哥哥两滴好亮的泪珠就这么滚落下来。
砸在我心里酸酸的池塘上,溅起一朵很酸很酸的浪花。
我说,哥哥你别哭。
可是哥哥越来越伤心。
人总是这样,我想,明明没什么,却总也止不住泪。
还不如一个忧郁症患者。
我笑起来,那就假装普天之下都是正常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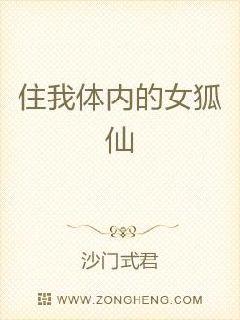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