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淑梅顺利地通过了托福考试,虽然分数和大多数中国学生比,没什么可炫耀的,但是达到园艺系研究生的入学标准还是绰绰有余。在此之前,东山已经给她联系了几个园艺系的教授,并且带着淑梅一一拜访,表达成为入门弟子的愿望。一个红鼻头,笑嘻嘻的爱尔兰裔老教授欣然接纳了淑梅。研究方向是利用除草剂对园艺作物进行杂草控制。淑梅对杂草不感兴趣,她更喜欢园艺系里几个花卉研究的项目,但是有的教授婉言谢绝了她,有的教授虽然有意收她,但目前没有多余的项目资金,只得作罢。
东山安慰她说,除草剂项目听着不那么唯美,但是很实用,美国绝大多数商业化的农业生产都要用除草剂,市场广阔,将来找工作比那些花花草草的专业容易。淑梅不置可否,找工作对她来说太过遥远,令她高兴的是开始上学就有收入,她和东山两个人加起来每月能有两千多元,手头就松多了。当然能混个美国学位,就是好上加好,锦上添花。她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家里通报了这个喜讯,当然是在东山不在家的时候。
“淑梅啊,你说什么?你被美国大学录取啦,要去读研究生,哎呀太好啦。”淑梅听见电话那头董翠馨的声调越来越高。
“淑梅呀,你进步好大呀,都被美国录取了,值得祝贺呀!爸爸很满意。”江胜春的语病听起来很滑稽,但淑梅并没有计较。
“淑梅,妈早就知道你很优秀,只是以前你的能力没被挖掘出来。咱们这个楼里,除了二单元老聂家的女婿,去美国读大学的你是第二个,你可真给妈妈长脸。”
“不过淑梅,你也不能骄傲自满,进了学校要努力学习,多和教授同学请教,继续进步。”江胜春说话总是带着领导干部的范儿。”
“好,我知道啦。”淑梅耐心地说。
“淑梅啊,你搞得那个什么除草剂就是农药吧,那个是不是对身体不好,你为什么不选个其他的项目呢?”董翠馨有些担心。
“哎呀妈,没关系的。 搞农业,生物这些怎么也离不开化学的东西呀。实验室里都有很好的防护措施,不会有事的。”
“那你一定要小心啊。如果有危险,宁可不做,身体要紧。”董翠馨叮嘱淑梅。
“哎呀,干什么都得有风险,哪能一点苦都不吃。趁年轻,锻炼锻炼没坏处。但是一定要做好保护啊,淑梅。”江胜春插话。
“这是和你女儿说话,不是你在单位搞动员,但什么风险啊,你老糊涂了!”电话那头董翠馨在呵斥江胜春。
能为父母脸上增光,淑梅心里很高兴。她当然没忘了把即将读学位的消息告诉王艳,王艳虽然立即对她表示祝贺,但淑梅能看得出她眼里的失落。
“你们都去上学了,就我自己在家里当家庭妇女。”王艳无可奈何地说。
“你是福命,你老公马上就要博士毕业了,等找了工作,你就在家当太太,哪用得着像我这样跑到外面打拼。我到乐得在家当太太,可东山有那本事吗?”淑梅安慰王艳。
“但是你上学就忙多了,咱们也没时间经常在一起了。”王艳有些不舍。
“看你说的,上学又不是去充军,咱们楼上楼下的,想聊天儿不就是两步路得事。”淑梅拍拍王艳的肩膀。
戴安听到淑梅即将入学的消息给了淑梅一个大大的拥抱,“淑妹,太好了,我真为你高兴。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了,你让咱们妇女更强。”戴安说着把拳头举过头顶。
淑梅被戴安的热情弄得有点难为情,她从心里觉得自己不过是读个学位,实在难当此殊荣。
“你将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在那个领域为咱们妇女挣得一席之地。谢谢你,淑妹。”戴安诚恳地说。
“呃,其实,实在是没什么。”淑梅尴尬地笑着。
“不,很重要,在这个男性统治的世界里,我们妇女每挣得一席之地都是一个胜利。能帮到你,我很自豪。”戴安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部。
“我其实要谢谢你,戴安,你真的帮了我好多。”淑梅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
戴安起身去拿了一本书来,淑梅看见就是那本《丛林》,她笑着问戴安:“怎么,还不放过我吗,还要我给你读书?”
“当然不能放过你,”戴安笑着说,她把书放到淑梅的面前,“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戴安的表情变得严肃,“我希望你能把这部书读完。剩下的部分是说主人公尤吉斯最终从堕落和颓废中觉醒,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的信仰者。”
“谢谢,戴安。你真好。”淑梅把书拿在自己手里。
她这次来戴安家里,只是告诉戴安她即将上学的消息。她觉得自己英语水平的提高,戴安功不可没,来告诉戴安她的劳动成果是应该有的礼貌。她没有期望从戴安那里得到什么礼物,戴安送书给她,当然很nice,但她对这个礼物一点都不敢兴趣,书里描述的一百多年前美国食品生产的令人作呕的情景,和工人们的悲惨经历让人感到压抑,每次读这本书都让她情绪低落。现在,她即将揭开人生新的一页,她将不再是一个陪读的家属,而是一名正经八百的留学生,还是研究生。它和东山将有更多的收入,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运转,她可不想让这本悲惨的书破坏她的心情!她故作珍惜地接受戴安的礼物,准备一回家把这本书扔进一个角落。
“淑妹,其实就算你不来,我也会打电话让你来的。”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淑梅不知道戴安找她有什么事,心里有点好奇。
“我要搬离此地了。”戴安平静地说,就好像告诉淑梅,她要去趟图书馆。
“为什么,搬去哪?”这的确是令人吃惊的消息。
“两个星期前我去做例行体检,大夫发现我的心脏有些问题,恐怕需要手术。”戴安依然很平静。
“哦,很严重是吗?”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淑梅有些措手不及。
“应该是的,不然医生不会建议手术。”
“那你什么时候做手术呢,我能为你做什么?”淑梅没有客套,她是真心想为戴安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谢谢你的好意,淑妹,”戴安握住淑梅的手,“不过恐怕用不着,我要搬到东部去。我和你说过我儿子在纽约,去那边方便他照顾我。”
淑梅听戴安提起过她的儿子,但好像她并不想和儿子同住,但她顺水推舟地说:“是啊,您现在岁数大了,应该和儿子住一起,方便照顾。”
“不,我不会和他住一起,我会找个离他近的地方,但不会和他同住。”
“为什么?在中国,老人都是和儿女一起住的。”淑梅实在不能理解戴安家里的这种安排。
“我和我的儿子,尽管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但我们不能眼对眼地看世界。你明白什么是眼对眼吗?”
淑梅摇了摇头。
“就是说我们在几乎所有事务上都有不同的观点,意见不一致。我和他的父亲都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可我们的儿子却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崇拜者,而且是一个成功的实践者,很讽刺是吗?”
淑梅没完全听懂,“您的儿子……”
“他是学金融会计的,毕业后去了东部一所很好的学校拿了MBA,然后就去华尔街工作,他现在是一名基金经理,一个月赚的钱,比我一年的退休金还多。”
淑梅吃惊地哦了一声,原来戴安有这么一个有钱的儿子,她以前从来没有漏过口风。
“可我总觉得他把钱看的太重,把钱当成成功的唯一标志,缺乏社会责任感。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争执甚至争吵。但是我也明白,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有拥有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权力,所以我们选择互相尊重,但是拉开距离。我找一个离他近的地方,如果我病了,他可以很方便地来照顾我,其他时候,我们可以每周见两三次,每次只谈天气,美食,还有亲朋好友。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很爱对方,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信仰和观点,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和平相处的方式,你明白吗?”
淑梅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戴安说的让她有点云里雾里。不过美国人总是这样稀奇古怪,清官但断家务事,人家母子之间的事,她一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如何参与?于是她假装很理解的说:“是的,我明白。那就好,那就好。”
几天后淑梅去戴安家里和她道别,屋前的草坪上已经插上了出售的牌子,屋里是成堆的纸箱。戴安指着散落在各处和堆在地上的东西说,所有没有装箱的东西你随便拿,剩下的我打包卖给别人。戴安的东西都不错,淑梅真想全部拿走,可是那样就显得自己穷困且贪婪,她不想留给戴安那样的印象。她只挑了一些餐具、厨具、家具和日用品,叫东山开车拉回了家。
那天她还见到了戴安的儿子,一个高高大大的美国佬,声音浑厚,标准的男低音,人却很和善。他笑着轻轻握了淑梅的手,对她说:“你是淑梅,母亲老对我讲起你,谢谢你在我不在的时候陪伴母亲。”
淑梅第一次和一个年薪几十万美元的人握手,她既紧张,又兴奋,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不断地重复:“没什么,没什么。”
戴安和她的儿子似乎很亲密,说说笑笑的,如果不是戴安亲口告诉她,他俩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她完全会以为他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母子。多年后,当淑梅对美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才明白,戴安和她的儿子,实实在在地就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母子。
晚上她和东山说起此事,东山说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美国这样的家庭很多。有一对夫妇,男的是民主党的军师,女的是共和党的军师,两个人分别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工作,但他们却结婚十几年,还有两个女儿。他们的原则是,在家不谈工作不谈政治。
啊!淑梅做了个鬼脸,好像吃了什么难吃的东西。她搞不懂,她不理解,这些奇怪的美国人,这些令人费解的美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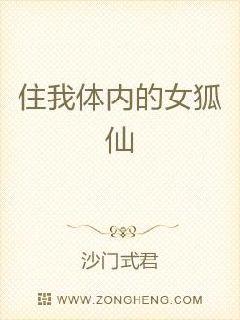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