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之十 妙缘和尚的隐情
10、妙缘和尚的隐情
第二天一大早,二担就下地走了。白春燕也起来做饭,顾亦言昨晚没睡好觉,早上醒不来,再加上这些日子在公社,不用起早,也就懒散得早起了。白春燕也没喊他,只是把他掉地下的枕头捡起来,塞到他头底下。
快吃饭的时候,顾亦言才醒了,连忙从炕上起来。来到外屋,他问白春燕:“二嫂,玉秀有消息吗?”
“哎,没有消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为这个,二担和我吵了好几回了,他怨我当初就不该管这事,惹了一身麻烦。哥俩差点没打起来。”她跟顾亦言讲了事情经过。三担看二担一点办法想不出来,就知道埋怨她,就生气了,说二嫂想帮我留住这个家有什么不对,你当哥的不管,还不让二嫂管,你还是我哥吗?二但说,你惹下这糊糊事,让别人替你吃瓜捞!三担说,看你一天老实巴交的,平时一扁担打不出一个屁来,这时候说话倒挺噎人!你当哥的一点也不替我想想,这事都怨我吗? 二担说,啥事不替你想,你结婚不都是我给出的钱,你不领情道谢就算了,还事事儿的,还说我没替你想!三担说好,俺家的事以后不用你管,我花你的钱早晚还你!就这样,哥俩现在连话也不说。
顾亦言问:“二嫂,去公社人保组报案了吗?”
“报了,人保组说这要找起来,只能是大海捞针,根本办不到。就得看哪有消息传来,或发现尸首了,或发现线索了,才能去找。他们说一有消息就告诉俺们。”白春燕说。
白春燕想起来什么,说:“对了,老陈头的大儿媳说,那天她起来上茅房,看见玉秀慌慌张张地往北走。北面是兴业堡大队,我去找了,也没有。”
顾亦言问:“那北边有没有岔路,不到兴业堡,通到别的地方了呢?”
“有一条小茅草道,往山里去,俺们顺着道往山里走了十几里,都找了什么也没发现。”
“那山里没有人家吧?”
“没有人家,就是有一个山坳叫落雁坡,那里有一个庙,叫多善寺,庙里有个和尚叫妙缘。”说倒这儿,白春燕像想起来什么:“对啊,应该问问那个妙缘和尚,怎么忘了这个碴!”
“什么和尚,现在还有和尚?”顾亦言记得,**刚开始,一群红卫兵,到他家附近山上的观音阁破四旧,把里面的佛像,法器,供具全都捣毁砸碎,扔到后面的山坡上。又把和尚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据说后来这些和尚都被撵回了老家。
白春燕说:“我听说,以前庙里有两个和尚,除了妙缘,还有一个老和尚叫慧空,是庙里的驻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和尚被红卫兵批斗死了,当时要让这个妙缘还俗,但是妙缘就是不干,打算以死相拼。已经死了慧空,红卫兵头头怕再出人命,再说,谁也不知道这个和尚是打哪来的,往哪儿撵也不知道。就说,这个和尚疯了,再也能用宗教放毒了,不管他,咱们撤吧!就这样,妙缘留在了庙里。自己开了块荒地,种粮,种菜,摘野果,采野菜,也没有人来管他。”
顾亦言听白春燕说完,感到很新奇。
白春燕说:“今天咱俩去多善寺,跟妙缘和尚唠唠,看他能不能知道,或帮咱算一算,我听说和尚都能掐会算。”
顾亦言说:“二嫂,能掐会算都是封建迷信,骗人的!”
“小顾,你不知道,妙缘和尚真的会算,不是骗人的,你去听他算了就知道了!”白春燕坚持说。
听白春燕这么说,顾亦言也想见见这个和尚,想看看他用什么方法骗人,必要时会揭穿他,免得白春燕上当。他说:“好,我和你去!”
吃完早饭,二担又下地去了。白春燕用布口袋装了少半袋棒子面,让顾亦言拿上。她抱着孩子,和顾亦言往北面山沟里走,去多善寺见妙缘。
在白春燕的带领下,两人沿一条茅草路走,进了一个山坳,白春燕告诉顾亦言这里叫落雁坡。走了一会儿,就没路了,只是蹚着草往山上爬。爬了一阵,前面是一个松树林,松树林里面,有一大块平地,在平地上坐落着一座寺庙。走近看,庙墙斑驳陆离,庙门破败不堪,周围长满了野草,看上去根本不可能有人居住。白春燕走到门前,推了一下庙门,喊了一声“师父!”,听见里面有人应声,她俩人就走进庙门。进去一看,院里干干净净,杂草不生。大殿看上去虽然破旧,但仍掩不住的**肃穆。一个人从旁边的寮房里出来,他四十多岁,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中山装,头上有浓黑的头发。
白春燕双手合十,叫了一声“妙缘师父”。
那人也双手合十:“阿弥陀佛!”
顾亦言好奇,和尚不穿僧衣,还留头发,这和他以前见过的和尚不一样。更让他惊奇的是,妙缘和尚一见到白春燕,脸上立刻洋溢起笑容,而且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这是不是就是书里说的花和尚?”他心里想。
白春燕让顾亦言把棒子面递给妙缘,妙缘连声说:“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妙缘将二人让进寮房的外间,在炕沿坐下。白春燕说:“妙缘师父,我来就想问您一件事。”
妙缘说:“施主请讲!”
“我的妯娌玉秀,二十几天前离家出走,到现在音信皆无,请师父指点一下,怎么才能找到她?”
妙缘摇摇头:“不瞒施主,贫僧没有这个本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白春燕说:“师父,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听说,多善寺门中,有求必应,你就给说说吧!”
妙缘还是摇头:“施主有所不知,以前是姑妄说之,姑妄听之,而今看来都是装神弄鬼,封建迷信而已,罪过,罪过!”
白春燕说:“师父,有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师父之言能让俺们找到亲人,那就是功德无量,俺们感激不尽!”
妙缘沉思片刻,对白春燕说:“施主所言极是,这样吧,你别把我当师父,就当你我是萍水相逢的路人,闲聊几句吧。若对你还有些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好,好,请师父说吧。”
“请你先把玉秀的情况和我说说吧”妙缘说。
白春燕就把玉秀嫁到镰刀湾前前后后的情况都如实地说了,包括知道玉秀失身的事后,玉秀不辞而别,下落不明。
听完,妙缘还是不说话。顾亦心里想,这个和尚啥也不知道,不知说啥才好。
其实,妙缘不是不想说,也不是不会说,而是不能说。二十多天前的一件事,使他陷入了一个相当纠结的境地。那天一大早,他和往常一样早起,面朝西方,在心里咏颂《楞严咒》和《心经》,然后去泉眼提水。他忽然看到松树林里吊着一个女人,他赶紧跑过去,抱住那人的大腿往上举,用脚勾过被上吊人踢开的石头,放在那人的脚下。腾出一只手,解开绳套,把那人顺山坡平放躺倒。他用手试了试,她还有鼻息,才放心坐在一边等。
一会儿,女人睁开了眼睛,看到妙缘,想大叫,可发不出声音,想起身又没有力气。妙缘赶紧说:“阿弥陀佛,我是多善寺的妙缘,你别害怕!”
那女人闭着眼睛,眼泪大滴大滴地涌出来。妙缘问:“请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自寻短见?”
“你为什么要救我,让我去死,让我去死!”女人用嘶哑地声音叫道。
妙缘说:“姑娘,自杀是罪过,你不能就这么死,这么死会受到上天惩罚的!”
“你骗人!我都死了,还有什么惩罚?还有比死还厉害的惩罚吗?”那女人说。
“上天的惩罚,就是让你下地狱,做饿鬼,再托生成畜生!”
“老天爷,你讲不讲道理?我是被害死的,害死我的人怎么不下地狱,却让我下地狱!”
“姑娘,无论善恶都终将有报。作恶之人终将得到报应,不是不报,时辰不到!可尽管你是含冤自尽,也会变成孤魂野鬼而无处托生,再难为人身!”
“世上这么苦,做不做人又有什么关系!没有意思,不做就不做吧!”女人说。
“人生苦乐,全是因前世修行所来。虽然人活着诸苦兼备,但既得人身,却应珍贵。只有立志修行,崇善为人,积德行善,才一定能获得现世的安乐和幸福!”妙缘大声说。
“我的心已经死了,除了一具空壳,什么快乐也没有,活着干啥!”女人痛苦地说。
妙缘说:“今天相见,说明你和佛祖有缘。走吧,到庙里咱们再仔细谈谈。”
那女人跟妙缘来到庙里,妙缘给她倒水洗了脸。妙缘开导她半天,她不知不觉竟听得入了神。
妙缘说:“痛苦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师父,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一切痛苦的产生在于不能放下。不能放下自己曾经受到的伤害,于是你总是生活在怨恨和恐惧之中,不能享受人生的快乐,所以说痛苦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女人说:“师父,按照你的说法,什么都能放下吗?那我给你说说我的痛苦,你看我能不能放下,如果不能,我就去死!”
这个女人就是田玉秀,把自己的曾经被强奸的经历告诉了妙缘。她被强奸后,对男人产生了反感,对男女之间的媾和感到非常恐惧。结婚后,她以为能把自己的感觉改变过来,没想到,新婚之夜,三担连续和她**三次,次次都像被强奸时的那种下体被撕裂的感觉。她央求三担不要了,三担根本不听,继续粗暴地和她**,彻底摧毁了重新做女人的欲望。以后,她再也不让三担碰她,几次三担想硬来,她以死相拼,三担只能作罢。她不敢说出理由,她不是怕离婚,而是怕人们知道自己被强奸过,自己再没脸活在世上。因此,当这次三担指责她时,她知道她失身的事情已经败露,决心自杀。
妙缘听玉秀说完,慢慢说道:“就佛家来说,你的不幸遭遇不是你现在痛苦的原因。你现在所以痛苦,是你对这件不幸之事久久不愿忘记,用佛教的话就是你对那件事太执着,这才是你痛苦的真正原因。”
田玉秀摇摇头说:“我听不明白。”
“这么说吧,那件事给你的痛苦就像一把盐。你把这把盐放到一碗水里,会咸得发苦。可是你把这把盐撒到井里,会觉得一点咸味也没有。同样的痛苦,放到了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同地感觉。这说明,苦是不是苦,全在于自己的感觉,物随心转,苦自己生。如果你放下对痛苦的执念,放宽心胸,就像把盐放到了井里,痛苦就会烟消云散。”
“师父,你说的我好像听懂了。你是说我的心不够大,总盛着那件事放不下,所以才痛苦,对吧?”
“是的,就是这样!心宽一切宽,心迷一切迷,宽则快乐,迷则痛苦。”
田玉秀问:“师父,可是怎么才能让我心胸宽大起来呢?”
妙缘回答说:“自我修行,做到心无执着,到那时你心胸自宽,定能离苦得乐!
这时的玉秀,冥冥中感到佛祖在向他招手,她的心已脱离凡尘,向着佛界飞升……
她对妙缘说:“我想出家。”
妙缘说:“不行啊,现在所有寺庙都已废弃,僧人都已还俗,你没有出家的地方。再说,我给你讲这些,不是要你去出家,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这些要求修行,慢慢改变自己,消除心里的业障,多做善事,广结善缘,成就菩提之道,忘掉人间的烦恼,永隔苦海。”
“不,我就是要出家修行!做不到,那我还要去死!”田玉秀斩钉截铁地说:“妙缘师父,你给我指了一条活路,让我看到了光明,但那却是一条没法走的路。那我还要去死,我活得太累了!”她所以这么坚持,是因为她再也不想和凡人生活在一起。
妙缘知道,田玉秀被心魔彻底控制,已经无药可治了。出家也可能是她唯一的生路,可现在想出家比登天还难。
田玉秀等待妙缘的回答。她心如死灰,如果妙缘不能让她如愿出家,她决定去跳山崖。她知道,再往山上走,有一个立陡立陡的山崖,下面是几十米的深沟,跳下去一定会粉身碎骨。
一筹莫展的妙缘忽然想到了望海寺的弥彻,他早已是庙里的驻持了。后来,他还担任了当地的佛教协会会长,市政协委员的职务,**前期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中寺庙受到保护,望海寺没有像其他寺庙那样遭到打砸。望海寺的和尚,专门成立了一个生产队,表面上还俗,其实暗中还保持着一些佛教的活动。弥彻作为市政协委员,前不久,还出面以望海寺驻持的身份接待了一个外国佛教访问团。没别的办法,只好让田玉秀到弥彻那里去了,看能不能把田玉秀编到僧侣生产队里,让她和僧人们生活在一起,待将来看她的思想转变情况,再决定她的去留。
妙缘给弥彻写了一封信,把玉秀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说了,让他给想想办法。他把信装到一个信封里,交给玉秀收好。他给了玉秀十元钱,和十斤全国粮票。玉秀千恩万谢,给妙缘磕了几个头,就走了。妙缘双手合十,口中念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田玉秀的离去,让红尘少了一个怨妇,空门多了一个信众。
这些,妙缘不能告诉白春燕。他认为,如果让田玉秀的家人知道了她的下落,很可能就会被追回来,那样玉秀必死无疑。望着白春燕急切地目光,妙缘开口说道:“你说的玉秀,是被可怕的梦魇缠住,无法解脱。”
白春燕说:“就是,就是,她就拐不过这个弯来!”
“被**后,玉秀已经对男女之事十分恐惧,结婚后再逼迫她行周公之礼,就是再揭她流血的伤疤,那种痛苦超出了她的忍耐,结果一定会和你们的愿望相反。”
白春燕问:“什么叫周公之礼?”
妙缘说:“就是男女之间的那种事。”
白春燕害羞地笑了。
“这是其一。其二,因被**而失去贞操,对一些传统思想严重的人来说是奇耻大辱,生不如死,而玉秀就是这种人。三担的责问,撕去了她最后一块遮羞布,她的绝望可想而知。”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白春燕问。
“从她心里的障碍入手,诱导她放弃自卑,恢复应有的尊严,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最后让她融入这个曾经令她恐惧和失望的社会,融入家人、周围人的圈子里,成为正常人。”
白春燕着急地问:“师父,你说的都对。可是事已至此,还有挽救的办法吗?还有,玉秀现在会怎么样?”
“玉秀有两种选择,一是自杀,二是隐身于无形,让人再也找不到。”
“那玉秀是一,还是二呢?”
“从你们目前查找的情况看她,她应该没有自杀。”
“那她又能去哪儿啊,她在外地没亲戚!”
“像她这样的无辜蒙羞之人,理应得到佛祖的庇护,安然无恙,以待救赎。因此,你们不用着急,她不会有事的!”妙缘意味深长地对焦急的白春燕说。
顾亦言小声嘀咕道:“说了半天,没有一点实际的,都是封建迷信的那一套!”
妙缘并听到了顾亦言的嘀咕,没有反驳,仍然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万物因缘而和,也因缘而断,有因缘而断之时,一定也有因缘而和之处。”
白春燕摇摇头:“师父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我是说,玉秀和三担的因缘虽然断了,那她也许会接续一段新的因缘,这个因缘也许不是家庭和婚姻,而是精神和意念!”
顾亦言也听得似懂非懂,他对妙缘说:“你说的是不是,玉秀和三担的因缘结束了,但她会面对新的因缘,而这种因缘不是家庭也不是婚姻,而是精神上的,意识上的?”
妙缘说:“阿弥陀佛,施主说的正是贫僧的意思。”
“我不是什么施主!你一直神神叨叨地东扯葫芦西扯瓢,可就是不回答我二嫂的担忧!她想知道玉秀是不是还活着,在哪儿,她会不会回心转意?”顾亦言面对妙缘的闪烁其词,故弄玄虚非常不满。
“贫僧不是神仙,只知因果,未能知晓玉秀身在何处,望施主宽宥!”妙缘合十道。
顾亦言说:“原来你刚才说的是全凭你们佛教上因果理论推测的,这不就是瞎编吗?”他想起**初期,他看过一幅照片,上面是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庙前,红卫兵在批斗一群和尚,和尚手里拿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净放狗屁!”听了妙缘的一番话,他觉得挺好笑,但看到白春燕虔诚的样子,也不好说什么。
白春燕说:“你是说,从因果上看,玉秀结束了这段姻缘,又会去结交新的因缘,她会过的比现在好,对吗?”
妙缘说:“阿弥陀佛,这只是贫僧的推算,还要看玉秀的造化几何,正可谓命由天定,运由己生。善哉,善哉!”
顾亦言心里暗自嘀咕:“这不和没说一样吗?”
白春燕说:“谢谢师父,我明白了,谢谢你的点拨!我们回了。”
说完,白春燕向妙缘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和顾亦言走出庙门。妙缘双手合十,送他们到门外,连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等走出很远,顾亦言回头看去,妙缘还站在庙前,没有离去。
他对白春燕说:“我看这个和尚有点怪,总是拿眼睛看你,不知为啥!”
“你想到哪儿去了,妙缘师父是个好人,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你别看现在破四旧,还有人偷偷地给他送吃的,有时还给点钱和粮票。**前,有一个人家小孩高烧不止,家人抱着孩子到多善寺求佛祖保佑,去病消灾。妙缘摸摸孩子的额头,再看看奄奄一息的孩子,他对孩子的家人说,佛祖只拒心魇,不败病魔,快带孩子去医院,家人不听,执意念经救儿。妙缘急了,抢过孩子就跑,孩子家人只好跟随。就这么跑了十几里路,来到公社医院,打针吃药才治好了孩子的病。大夫说:‘再晚来一会儿,孩子就没命了!’。家人逢人就说妙缘是能救人命的活佛,一时间多善寺香火旺得不得了。”
顾亦言原以为,妙缘在宣传封建迷信,要不是陪白春燕来的,他一定会和他来一场辩论,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听白春燕这么一说,才感觉妙缘的确是一个有个性的和尚。他问:“妙缘和尚是本地人吗?”
“不是,听说是解放前从外地来的。”白春燕说。
“可我还是觉得他对你和对我不一样。他看你的眼神是那么专注,说话口气也不一样,这么说吧,我觉得他对你就像一个父亲对待自己的女儿。”
“那没错啊,要不怎么叫师父呢,既是师长,又是父辈。”白春燕不以为然地说。当然,她早就习惯了男人对她那种热烈而含蓄的眼神,但妙缘看她的眼神的确不一样。顾亦言说得没错,她也有这种感觉。
顾亦言不再说话,跟在白春燕后面踏着青草往山下走。走着,白春燕说:“可怜的玉秀,就这么失踪了,我真后悔死了!”
顾亦言安慰她说:“二嫂,你尽力了,这事儿哪能怨你。要不是老小子圈拢三担,要不是三担喝多,可能玉秀就不会走了。对了,二嫂,我还想问你,老小子为什么要对三担那么说,正常的人都是往好里劝,那有往坏里劝的?”
白春燕恨恨地说:“说实在的,自从那天我和老小子一接触,我对他就没有好印象。”
“为什么?”
“这个人挺滑,还有点奸诈,城府很深,说话能听出来,都是虚头巴脑的话。三担跟着他,他把三担卖了,三担还得帮找数钱。”
“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
“没人知道,反正是从很远的地方。老大不小了,也不成个家,真是个怪人!”白春燕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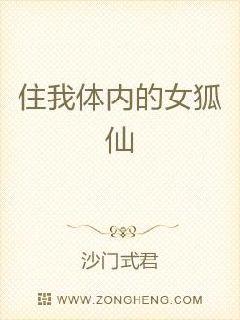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