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 各不相同的忧心事
世上的事变换如风云,转眼间夏去秋来,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到了被录取考生的手里。
冯清水始终没有接到这个喜讯。
随着时间的推后,那种失望和惆怅也越来越强烈。他多么希望和中考的录取通知书那样,再有一次补录的机会,但是,那种巧遇是不会常常发生的,事实越来越清晰越无情地证明,他高考落选了!
当他听说岩格和牛继红都考上了大学时,心中那种难受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体会得到。岩格考的是北京的一所有名的综合大学,牛继红也考取了北京一所师范学校,一纸通知书将他们分成了两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大学毕业国家是包分配的,将来就是吃公家饭,没有考上,就只能自食其力,象冯清水这种农村的孩子,也只有爬到庄稼地里干活了。
由于他的落选,全家的希望都化为了泡影,一个阶段,整个家轮罩在沉重的阴影下,父亲冯栓子的身体江河日下,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无奈之下,只好和全家人陪伴着极度虚弱的冯栓子,带着全村人东拼西凑来的不到一千块钱,无奈而又忧心忡忡地踏上了去往省城医院的漫长风雨路。
由于家中还养着三口猪,十几只鸡,眼看已进入秋收季节,又是土地承包的第一年,责任田间的庄稼长得粒粒饱满,异常出色和喜人,丰收季节怎能丢下一切不管呢?全家人思量再三,还是让冯清河留在家里最合适,下一年全家人还凭这些活呢。
这样一来,在外面就要靠初涉世情的冯清水了。
在省城这个地方既陌生又无依无靠,一家三口挤在租来的一个不足十平方米农户屋子里,为了图个便宜。就这,每天也要十块钱的房租,不过在医院周围,这是价格最低的。
好不容易才在医院里挂到号,又等了十几天才等到第一项检查,一个多月下来,病情检查单才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段的等待是最难熬的日子,全家人的心无时无刻不吊在嗓子眼,他们每接到一个检查单,心情都要经受一次难言的煎熬。不过,时间总要一天挨着一天过去,检查结果也终将无情地向他们裸示出来。
最后姗姗来迟的是那个切片检验报告,冯清水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拿到手里后,一直在发颤,因为他明白,这不是一张简单的病检报告,而是捧着父亲的命!是全家人忐忑等待的判决书!是生死相隔的一扇窗纸!
他不知下了多大的决心,不知费了多大的力,一点一点地往开展。
他胆战心惊地从上往下看,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身上不自觉地冒着了冷汗。
他看完了,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就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轻易放过。
他彻底摊到了那里,腿在不听使唤地哆嗦,软的无法自持。
他目光无神地靠在化验室外的一个墙角下,直到化验室进进出出的人逐渐消失,直到楼道里的灯光驱散了不知不觉到来的傍晚昏暗。
癌症,父亲得的是晚期肺癌!
他简直不愿再去重新看一眼那个可怕、可恶、可恨的字眼!那个让人见而生畏的恶毒字眼!
那一天,他也不知道是如何强撑着走回小租屋的,也不知道是如何开口向母亲透漏这个使人悲恸消息的,是如何装作镇静嘱咐母亲一起向父亲隐瞒的,总之,就像黑沉沉的天空渐渐在炸裂开来,似乎马上将要坍塌下来。整个大脑里被魔鬼的影子占据着,心脏那一块狭小的地方就象被生铁一样硬邦邦的东西撑得满满的,沉甸甸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那一段时间他和母亲在父亲面前还要强颜作笑,尽量掩盖掉凄哀无助的表情,尽量不使父亲知道真相,因为这是在谨遵医嘱。
那一段,他似乎没有再去想起高考失利的事,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想起那件事,因为,相形之下,那件事对于他来说,似乎已经显得不太重要。
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失意、最低落、最苍凉的岁月,他在这段岁月中趔趄着生存,支撑着前行,品尝了人世上最苦的滋味,也展示了人生舞台中最拙劣的演技,唯一的收获就是磨练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意志。他在无意间,又向成熟跨进了一步,大大的一步。
冯栓子不识字,没有看单子,但他却从来没有问起病情。
有时候,他们母子脸上在不经意间会流露出忧愁悲伤的表情,但冯栓子几乎没有在意过,更没有怀疑过和追问过,谁也不知道他的心里到底知道多少,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瞒住了他。也许,他早已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只是不愿捅破这层薄薄的窗纸,轻易地打破这种看上去很“平静”的湖面,或许他真的不知道。
手术很快确定了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给父亲补得好一点。大家都抱着接受最残酷现实的准备,但又都心照不宣。
术后,冯栓子的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建议回家静养,半年后再来复查化疗,就这样,一家人搀扶着摇摇欲坠的冯栓子,坐着表舅派来的公社小卧车回到了武家岩。
冯清水经过家庭变故,彻底放弃了继续复习的打算,无论家人怎么希望,无论躺在病床上的冯栓子多么着执地要求他再复习,他都没有答应,沉重的医疗负债,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他脆弱的灵魂,他要为家里增砖添瓦,减轻哥哥的负担。
这段时间对武学兵来说,就像眼前弥漫着遮天盖日的粉红色迷雾,整个灵魂就像一片轻飘飘的羽毛。一向无忧无虑的他身不由己地深陷在神池荡漾,魂不守舍的漩涡中,一种毫无共鸣的单相思驱之不散地纠缠着他。
徐艳芳的笑,徐艳芳的说话声,徐艳芳的举止,徐艳芳的背影,就连徐艳芳恼怒和忧容,在他的眼里都是铭心刻骨的雅,无与伦比的美。
徐艳芳的身影无时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无论走路、吃饭,哪怕是睡觉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梦境,没有一个清晰的梦境,没有一个踏实的梦境。偶尔中她也会出现在梦里,却又会在倏尔之间去之无踪。
醒来后,他似乎还能想起梦中和现实中衣着一样的她,一样的黄毛衫,一样的鲜红裤,一样流水瀑布般的秀发,但她的表情总是那样的模糊,想不起来哪一次她有过平常挂在眉梢的笑意,更想不起哪一次有过奢望的温情。她总是那样楚楚动人,又可望而不可及。
武学兵这时才对当时吴成德的痴迷有了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一种设身处地的煎熬、凄楚和伤情。
他借大队会记之机,想尽了所有办法去刻意接近朝思暮想的她,帮教室粉刷墙壁,帮学校劈柴生火,帮她贴床围墙纸,为她挑水……
所有这些,荷香妈看到眼里,明在心里,学校教室有什么小事小活都招呼他。但是,当武学兵每次做完后,赢得的只是徐艳芳平静的微笑和客套般的谢意,刚开始,他觉得心里暖洋洋的特别舒服,但久而久之,这种笑这种带着歉意的谢谢,就变成了一道使他无法逾越的鸿沟,一面拒他于门外的防火墙。
这道沟不浅不深,这面墙不薄不厚,有些时候还使他充满了遐思和臆想,但之间的距离却始终遥远如初,这段看不见却感觉得到的距离有时象一座大山压着他,使他顿觉消沉和绝望;也有时候却又像一片温柔的羽毛撩拔着他,使他心旌荡漾,不能自已。
就连她那和教室连着的宿舍,那两间房上已经长起茅草的破屋,在他眼里都魔幻般地变得那么亲切温馨。她与他擦肩而过时,那种矜持的步态和似隐似现的微笑,在他眼里都是天仙般的美奂。就连那高跟鞋扣击地面发出的声音节奏,在他看来也如一首跌荡铿锵的击打乐一样悦耳。
他鬼使神差地和其他村里的年轻人一样,有事没事都愿意到教室前边的那片场地上说笑玩耍。愿意到大队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闲坐,因为这里和她的宿舍中间只隔着三间房的教室,他坐在破旧的办公桌前就可以清晰地听到她那悦耳而清脆的教书声。
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他被这种毫无反应的单相思纠缠着,撕磨着,煎熬着,使他寝食难安,欲罢不能。
这种感觉是生平以来的第一次,来的这样猛烈,这样奇异,这样美妙,却又是这样的让人烦躁和莫名地痛苦。
长了这么大,从不懂事到懂事又到初中毕业,许多年来并不乏和女孩子的交往,在她们中有好看的,有不好看的,有俊俏的也有丑笨的,但彼此之间从未有过这样让人日思夜想,心往神驰而又略带苦涩的奇异感觉。
在这个让人眼亮神明的,时常带着笑容中仿佛夹杂着一丝忧伤的女孩面前,感到从未有过的局促和无力,就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生怕伸手弄碎似得。
多少天来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翻来覆去在思虑着如何把自己的心迹表白给她,但是,一次次又在自我否定中望而却步。
他担心,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自卑,他生怕被她一口回绝。他不敢想象被回绝后会是多么地痛苦,多么让人无法承受的打击,多么地无地自容。
在这种自我的焦虑、煎熬、挣扎中,他有时也恨自己无能。武学兵,你是胆小鬼,当年那种威风凛凛、无畏不惧的英雄气哪里去了,面对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怎么倒变得手足无措,胆小如鼠了。武学兵,你怕过什么?从小和人打架不止一次,也不止一次地挨揍,面对强敌都能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武学兵,你要把腰杆挺直了,大声把你对她要说的都说出来,喊出来,让她把压抑在你心里的所有心思都听到,让她做出她的决断吧,即使回应你的是一把匕首,那就让它插进心脏来好了,那也比这样的折磨好受的多——
但是,总不能直接面对着她,不管不顾地就说我喜欢你,我爱你吧,那不是难为情的事,是要命的事,是尴尬难受的事。要不然让荷香妈先捎过去个话打探一下?荷香妈曾是自己的老师不说,大人们掺和进来,不就满城风雨了吗?那样子,人家徐艳芳会怎么想,从心里能不能接受?还是觉得不行。要不让二妮传个信?二妮可是天天晚上要到学校和她做伴睡的,但是,二妮又和自己近邻家,从小一块长大,那么清纯而敦厚的小姑娘,她会帮这个忙?会不会越帮越乱?看起来这个主意还是用不上,要另辟蹊径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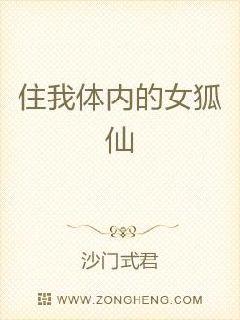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