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铁路工人
五十
月明青年点的男青年,除去接班、当兵、家住沿线的,剩下十八名全部分配在硼海火车站的装卸车间。女青年和木器加工厂,也就是“小点”的人员分配在硼海中心站的“铁路站前饭店”、“铁路站前旅店”、“铁路站前小卖店”、“铁路冷饮厂”和“硼海站职工食堂”等地方。
硼海中心站管辖十二个火车站,其中包括硼海站。硼海站分客运、货运、运转、装卸四个车间。装卸车间有三个班组,三个班组三班倒,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高天榜、丁龙、赫文亮等八个青年分在二班。这个班青年多不好管,原来的工长辞了职,说什么也不干了。装卸主任有招,他任命高天榜为二班的工长。高天榜充分利用小小的权力,遇有脏活、累活就把赫文亮支开。“亮子,你去把拉门绳拿来。”“亮子,你去通知货运,五道的硼砂装完了。”“亮子,你去拿个防护牌。”“亮子,货三的车对不上位,你联系联系推推车。”------有的老装卸工有意见了,可刚露出不满的情绪,“妈了个巴子”就骂上了。出了名的打架精,谁还敢说什么呐。
由于机械少,只有两台叉车和一台龙门吊,所以装装卸卸大都靠人力,这对没出过力的青年们确实是难以招架。才上一个班就有人开始活动了,别说,几日里还真有二个青年离开了装卸车间。
在货一卸完一车尿素,装卸工们在货堆上躺着、坐着喘粗气。赫文亮把帽子、外衣撇在一边,脸上淌着汗水,头顶冒着热气。
“文亮,你看谁来了。”丁龙在货堆上翻了个身,“妈的,怎么没人来看看我。”
货一的北头是个仓库,陶晓丽站在大库头往这边望。
赫文亮跳下货堆向大库走去。
陶晓丽和章娅莲是流动售货员,每天身穿白大褂,胸前挎个塑料筐,在站台上、候车室里卖食品。
“你来干什么?”
“看看你呗。”拂去赫文亮秋衣上的灰土,“累吗?”
“还行。”
“三姐准备托人把你调走。”
“不用,累是累点但挣的也多。”最主要的是干一天休两天,这样就有较多的时间复习高考了。“回去和三姐说,千万别把我调走,我在这挺好的。”
“瞅你这小体格能挺住吗?”
“放心吧,没问题。”
灰蒙的脸,汗水经过留下几道痕迹。
“喏,把脸擦擦。”陶晓丽手里拿着一个洁净,叠的整齐的花手绢。
“不用。”用肮脏的手,擦了一下肮脏的脸。
“哈哈哈,真好看。”
猜出了自己的形象,“你走吧,一会儿我们还有活。”
“给。”
“什么?”
“麻花。”
“不要,这么埋汰怎么吃。”
“怎么不能吃,把嘴擦擦就吃呗。”又把手绢掏出来。
“不用,不用。”用包裹麻花的纸擦擦嘴,咬了一大口麻花,“真香。”
陶晓丽满意地走了。
“别吃独食啊。”丁龙早瞄上了赫文亮手里的油炸麻花。
“接住!”将另一根麻花连同纸,扔向丁龙。
坐在丁龙身旁的高天榜一把抢了去,用满是灰土的手将麻花撅成两段。
丁龙嘴里嚼着食物,“你个黑鬼,什么时候才能死。”
高天榜一低头,一大口麻花咽了下去,“放心吧,我到哪都把你带着。”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装卸主任张显威拿着一沓人事令,“月明青年点的人注意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这是个绝好的好消息。从今天起,你们就是铁路职工了,人事令马上发给你们。”这是在早晨的点名会上。
“这回你们便宜透了,你们成了全民工,分配在别的地方的人,还有从我们这里调走的那两个,他们统统都是大集体,和你们相比差了一大截子,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张显威原是中心站科室人员,因工作中犯了错,被贬到了装卸车间。他发着人事令嘴里不闲着,“这人啊别太奸奸了,象吴红伟(离开装卸的其中一个),下乡的时候开假证明,说自己有病逃避下乡,可后来觉得不行了,怎么了,人家抽工都在青年点抽,这才又和你们一起下了乡,要不不早就回来了吗。”
高天榜觉得不顺耳,但没吱声,只是瞪了张显威一眼。
“这回吧,在装卸本来挺好的,可又挖门盗窗地走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走早赶上穷,走晚穷赶上,怎么折腾都是个穷。”
这话有意思,说是走早了“穷”在前面等着,走晚了“穷”又从后面追上来,早了晚了都摆脱不了穷。
五十一
硼海中心站成立了“硼海铁路劳动服务公司”,中心站管内没有工作的铁路子女,在“铁路站前饭店”,“硼海铁路托盘厂”(厂址在鸟头山)------工作的人员全都划规了铁路劳服,成了铁路大集体职工。公司暂时有一名经理,这个经理是中心站派去的一名干部,各科室及科室人员都在组建中。
章娅莲庆幸:多亏没把赫文亮从装卸弄出来,要不他也成了大集体职工。
成为正式铁路职工的第四天,赫文亮被站长叫了去。
运转主任简波,见装卸车间有那么多年轻职工便来到站长室。
“唐站长,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站长姓唐,叫唐永贵。
“什么事,说吧。”
“我们车间缺一个扳道员,总靠住勤也不是回事。装卸去了那么多年轻的,你看能不能给我弄一个。”
唐永贵一下子想到了赫文亮,“行,完全可以。”
唐永贵早年是硼海火车站,运转车间调车组的一名连结员。当时的站长赫冠义,破格提升他为线路值班员,后又提为坐台值班员,比唐永贵资格老的职工都很不服气。
“站长,你看把谁给我好?”
“你既然来找我,心里早有谱了吧。说吧,想要谁。”
“我看赫文亮这个小伙子不错。”
“好!就把小赫给你了,我这就给中心站人事打电话。”
从站长室出来,赫文亮心里高兴,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陶晓丽、章娅莲、高天榜、丁龙他们。
陶晓丽比赫文亮还高兴,“这回可好啦,不用再扛大包了。”
中午回家,刘畅见赫文亮脸上不是灰蒙蒙的,“盒子回来啦,今天没干活?”
“站长给我一天假,叫我明天去运转报到。”
里屋的赫文弘掀起布帘,核实性地问:“去运转?”
“是。”
“干什么?”赫文弘、刘畅异口同声。
“当扳道员。”
“太好了。”刘畅也知道扳道员比装卸工好。“快洗洗脸,一会儿吃饭。”瞅了一眼脸盆,“不用了,这回不用了。”
至从在装卸上班,赫文亮每次回来脸盆里都有清水。
有四个炒菜,赫文弘又拿出一瓶白酒,“下午不上班,咱哥俩喝两盅。”
难道四哥、四嫂知道我工作变动的事?
筷头在菜盘里搛来搛去不往嘴里放。“文亮,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赫文弘早已不叫“盒子”了
这才注意四哥、四嫂的表情,“什么事,四哥怎么了?”
“单位给我分了一套新房子------”
“好事啊,看你愁眉苦脸的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你嫂子不想要。”
“为什么?”
刘畅上了炕,“我们走了你咋办,这么大个房子一个人多冷清。再说,以后谁给你洗衣、做饭。要是成家就好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欸——这有什么,我这么大个人了什么不能做。厂子难得给房子,决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你们放心走吧,不用担心我。”
赫文弘筷头上的菜放进了嘴里,“你自己能行吗?”
“行,没问题。你们找人算算看哪天好,搬家时我找几个工友来帮忙。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一个人好凑合。”
刘畅还在犹豫,“把你一个人撂在这,四嫂这心里------要不你也一起跟我们走吧。”
“钢厂离车站那么远,我可不去。”
“那咋办——那四嫂以后常来看你,衣服不用洗,等嫂子回来给你洗。不愿做饭就到嫂子那吃。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千万别不好意思。”指着缝纫机旁边的大铝盆,“换洗的衣服就放在那里。”
赫文亮吃了一口菜,“四嫂今天做的菜真好吃。”
忸怩地,“不是我做的。”
赫文弘说:“她和我怄气呢,还说我不是你的亲哥哥,说我没长心。”
“四嫂你也喝点。”
“好,喝点就喝点。”
五十二
赫文亮的师傅叫解宝财,他没文化是个大老粗,干了大半辈子铁路还是个扳道员,自己的徒弟的徒弟有的都是干部了。别看是个大老粗,可脑瓜好使,十钩八钩活都不用写“调车作业通知单”。这是和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有关,每次调车作业前,他总要向线路值班员了解来车甩什么、挂什么,这样在调车作业计划下达前他就有了谱。他常给作业计划挑毛病,值班员都很尊重他,基本上都按他提出的方法干活。
扳道房不大,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部黑色电话机,一个备品箱,一个水壶,一个暖瓶,一个大肚滚炉子。桌子有三个抽屉,右下方有个小柜,这种桌子叫一头沉。年头久了,黄油漆变的有些发白,桌面上斑斑点点(桌面上布满了小坑,每个小坑就是一个小黑点),靠人坐的桌边没了棱角,弧形的桌边磨的又光又亮。扳道房的后面是个小仓库,里面放有煤、水梢、土蓝、除雪和擦道岔的工具。扳道房与仓库间没有门,间壁墙的右下角有个小洞,用煤时直接从洞里取。
解宝财拿出一个象新华字典一样大小的本本,说:“这是《技规》,我们干活主要就靠它。”
这是上班的第一天。
赫文亮接过《技规》,封面上写着《铁路技术管理规程》。学生时,经常见父亲捧着它看。
解宝财指点着《技规》,“我划圈的规章是咱们常用的,你要背下来。我们干行车的有三本‘天书’,一个是《技规》,再就是《行规》和《站细》,这《技规》是最主要的。”
赫文亮认真看着划了圈的一条规章。
解宝财凑近问:“这条规章多长时间能背下来?”
赫文亮合上书,“扳道员、信号员在值班时应做到:
1.严格按照车站值班员的接发列车命令,调车作业计划,正确及时地准备进路;
2.在扳动道岔,操纵信号时,认真执行‘一看、二扳、三确认、四显示’制度,对进路上不该扳动的道岔,也应该进行确认;
3.接发列车进路准备完了后,及时报告车站值班员。能从设备上确认者除外;”
解宝财惊疑地,“怎么,以前看过?”
“没有。”
解宝财又翻出一条规章,“你再背背这个。”
赫文亮看了两遍合上书,“道岔除使用、清扫检查或修理时外,均须保持定位。
道岔定位规定如下:
1.单线车站正线进站道岔,为车站两端向不同线路开通的位置;
2.双线车站正线进站道岔,为各该正线开通的位置;
------”
“哎呀,真是了不起,我教过这么多徒弟,脑瓜这么好使的还真没有。行,将来是把好手。小赫,还有四十一条。”
赫文亮找出第四十一条:道岔应经常保持良好状态,有下例缺陷之一时禁止使用。
“这条是道岔‘十坏’,你要先背下来,不然道岔有毛病你也发现不了。”
“叮铃铃------”电话响了。
“解师傅,给。”将电话推给解宝财
“你接。”
“我接?我也不会啊。”
“没关系,站里说什么你就跟着说什么。”“站里”指的是车站值班员。
“南头李兆麟”
赫文亮反应很快,“北头赫文亮”
“2585次二道通过,准备接、发车进路”值班员下达命令,他吐字清晰,说的较慢。
“2585次二道通过准备接车进路。”李兆麟省略一个“发”字。
“2585次二道通过准备发车进路。”赫文亮聪明地省略了一个“接”字。
宝财满意地点点头,有的徒弟跟了三、四个班也不能接电话,几句常用语好长时间也说不标准。
“师傅,什么叫进路。”
“问的好,一会我告诉你。”
赫文亮随着师傅,右手拿黄旗,左手拿红旗走出扳道房。
“我们上班时,就和这家伙打交道。看见没,这一段叫‘转辙部分’,那段叫‘连结部分’,再远一点的那段叫‘辙岔部分’,它们合起来叫‘道岔,’。这个道岔到那个道岔之间,就是2585次的发车进路。我们要从第一组道岔的尖轨尖端”,用脚点着“尖轨尖端”,“走到最后一组道岔的辙叉心,这就叫‘准备进路’。这段进路的四组道岔虽然定位都是二道,不用扳,但我们也要从头走到尾,看看道岔有没有什么毛病,看看道岔区域有没有障碍物。等列车过后,我们还要象这样走一趟,那叫‘跟踪检查’”
回到扳道房,解宝财把旗扔在桌子上,“小赫,你通知站里一声。”
“怎么说?”
“这样说:北头赫文亮,2585次二道通过,发车进路准备好。”
赫文亮说的一字不差。
“你爸这老头是个好人啊,可惜走的太早,和他轧伙计没轧够。还好,老天有眼,又把他的儿子弄来和我轧伙计。”
“解师傅你是长辈,我怎好和你轧伙计。”
“欸——咱们轧伙计可不分什么长辈不长辈的,关键是投缘。你今年多大啦?”
“二十二。”
“处对象了吗?”
“处了。”
“噢。”
2585次通过后,解宝财到小仓库拿出一个装柴油的小铁皮盒,擦道用的铁卡子,还有破布、砂布向自己分担的道岔走去。
“你过来干什么?不用你,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以后有空擦两次,知道怎么擦就行了。不过看别的书要小心,别让领导看见,咱这除了规章,别的书不让看。”赫文亮拿的一本数学书,解宝财看见了。
赫文亮点点头。
师傅干活,徒弟哪能闲着?赫文亮拿起了满是油渍的破布。
解宝财没阻拦,他一边擦道岔一边说:“这个叫滑床板,上面这个叫滑床台,很多人分不清,把滑床台叫成了滑床板。”
“师傅,你说这道岔擦的这么亮有用吗?”
“按说没什么用,只要涂点油,保证使用灵活就可以了。可道岔是扳道员的脸,道岔埋汰了就等于我们的脸不干净了。再说,领导来检查,主要就看道岔擦的亮不亮。中心站要求:尖轨象刀片,滑床板象镜面。你看看,就连中心站的领导也习惯地把滑床台叫成了滑床板。”
怪不得师傅负责的三组道岔,在运转会议室里的“道岔评比表”上,月月都有小红旗,他是把道岔看成自己脸了。
赫文亮穿上了蓝色铁路制服,戴上蓝色的大沿帽子,在车站走来走去很是耀眼。
有介绍对象的,赫文亮婉言谢绝,他的心里唯有陶晓丽。
五十三
夜深人静,人们进入了梦乡。
一声长鸣,一列货物列车轰轰隆隆地驶入了硼海火车站。
铁路严格的运输组织,使每个有关人员:值班干部、助理值班员、线路值班员、信号员、扳道员、调车组人员、货运外勤、装卸工相继钻出温暖的被窝,做着自己应尽的职责。
机车一声声懒洋洋的鸣叫,搅乱了宁静的夜晚。鸣叫声与这宁静的夜晚那么的不和谐。
机车带着九辆车体向六线推进,这是第十二钩活。突然一个怪异的声响,车列前端的硫酸罐车撞上了脱轨器,罐车的第一轮对从轨面脱落。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白天装卸作业,装卸工组干完活忘撤了防护牌(防护牌下是脱轨器);货运员消记防护牌时未到现场确认;作业前连结员未检查线路;作业中领车连结员未发现防护牌;值班干部监控不到位。多种原因造成了这起脱轨事故。
一时间,参加调车作业的所有人员,从不同位置奔向事故现场。惊魂驱走了困意和懒散,一个个瞪圆双眼看着落地的车轮。
简波来了,问值班干部:“通知唐站长了吗?”
值班干部颓丧地,“通知了。”
“那不是站长吗?”有人高声说。
一个黑影快速地靠近事故现场。
没有责怪任何人,唐永贵认真观察脱线的罐车。简波及在场的人有了依赖,有了主心骨。
“小赫快起来,出事故了。”
解宝财叫醒了赫文亮。
夜间干活时,觖宝财从不叫醒赫文亮。这是违反师徒不得分离之规定的,但解宝财是老资格,谁也不好说什么。
虽说入路不久,但对“事故”这个词还是很敏感的。赫文亮一下子坐了起来,“谁出事故了?”
“和咱没关系。走,去看看,多经历点事就多积累点经验,这样的事很少遇到。”
“简主任,你安排一下,把那八辆车转到三线,然后单机返回六线。要注意,不能再出什么岔子啦。”
“站长放心,保证不能出错。”
唐永贵又对那个值班干部说:“你去救援库把复轨器拿来。”
“是。跟我来两个人!”
一下子去了四个人。
这时候的人什么也不计较了,谁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事干还觉得不自然。在场的人不是在弯腰,就是在走动。
由于脱轨的是辆重车,救援工作非常不顺利。在救援过程中,第二轮对也被拖下了“炕”,整个台车脱离了轨道(一辆车有两个台车、四组轮对、八个轮子,现有四个轮子落了地),救援失败。
“简主任,你立即去运转室向分局行车调度通报事故,并告知中心站。”
在场人的身子都矮了一截。不用开会分析,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就是那个领车的连结员。领车连结员一屁股坐在路基上,头搭拉的都要到裤裆了。有的人盘算着自己在这起事故中所承担的责任,猜测着处理结果。
东方泛白,中心站、分局、路局的领导们接踵而来。随后,从安丹站开来了救援列车。
事故现场站满了人,有铁路的干部、职工,有看热闹的,更多的是看热闹的人。
一位分局领导看了一眼车弓子,“车里怎么还有货?为什么还不卸!”通过弹簧弓子可以判断车辆的空重。
唐永贵问货物主任:“谁家的硫酸?”
“是硼海硼矿的。”
“抓紧通知他们来拉货。”
“已经通知了,估计一会儿就能到。”
时间不长,果然有三辆拉酸的专用汽车驶向脱轨罐车。
简波急切地说:“快把盖子打开,抓紧卸!”
专职卸酸人员还没到,硼海硼矿发运员,从拉酸的汽车拿出一个活口扳子,爬上了罐车顶部。他经常和硼海站打交道,车站出事他显得很着急。
四个螺栓卸下了二个,第三个也松动了。
“嘭”的一声巨响,圆型的铁盖子被气流冲到了半空中,随之,车内的硫酸喷射而出,宛如一股庞大的人工喷泉在空中呈伞状飞扬。
卸酸的发运员,被无情的气浪从罐车顶部掀翻落地。
在场的人惊恐万状,四外逃窜。这个时候已看不出谁是干部,谁是工人了。
卸酸前,必须先打开排气阀,将罐体内的气体排出后才能打开盖子。可这个发运员不知其中的道理,才酿成了此祸。
硫酸是一级腐蚀性物品,一旦落到皮肉上,皮肉便会被灼伤,落在脸上,严重的那就是毁容。有人将一只青蛙用铁线拴住放进硫酸池里,只一会,青蛙就剩骨架了。在场的人大都不知它的厉害,只是被巨大的,类似爆炸的声音吓跑了。
发运员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从空中散落下来的硫酸只有星星点点落在身上,衣服、裤子有八、九个小洞,脸和手没被硫酸“咬”到。
发运员送到了医院,经诊断左小腿骨折,其它部位没有大碍,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脱轨车辆被救援列车吊回了钢轨上。
四十多名运转职工在车间的会议室里,唐永贵和一名副站长参加了事故分析会。
“大家静一静,”实际很静了。“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分析昨晚脱线事故的原因;二、几个事故责任人,包括我做深刻的检查;三、总结经验教训,制定防范措施,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四、搞一下‘四查’(四查的内容:1、查职工的两纪。也就是劳动纪律和作业纪律;2、查干部的工作作风;3、查工作中的事故隐患;4、查行车设备。);五、请车站领导为我们车间做重要指示。”简波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继续说道:“下面我把昨天的事故概况说一下。2582次的调车作业计划是------”
------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会议进行到了第四项——四查。一开始发言有序,发言的人有些拘谨,后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会场有些纷乱。
唐永贵对身边的简波耳语了几句后,简波站了起来,“别瞎呛呛了,下面让我们的新职工赫文亮说两句好不好。”
会场一下静了下来。
赫文亮先愣后紧张,他轻咳了一声,“我入路时间不长,对铁路还不够了解,再加上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免不了有不妥的地方,甚至有错误的地方------”
解宝财紧握的双拳松开了,他好象比赫文亮还紧张。
赫文亮的心情渐渐轻松了,“在运转上班的第一天,解师傅就叮嘱我说,干我们行车的要腿勤、嘴勤、眼勤,工作要认真、要仔细,不能少看一眼,少说一句话,少走一步路。象昨天的事故就是少看了一眼,少走了一步路,如果相关人员提醒一下,问问六线的防护牌撤了没有,也能避免这起事故的发生。有人说:车轱辘一转,事故不断。这话好象在为出事故的人开脱责任,但这话说的客观,也从另一个方面警示我们,只要有车辆在轨道上运行,就有出事故的可能。所以,我们要以这起事故为戒,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搞好自控、互控、干部做好监控,把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
对昨晚的事故我的理解就这些。我还想就几个问题说说自己的想法、看法。第一、警冲标。警冲标看起来只是个木桩子,但它也是行车设备,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想,如果加以改造,把它与钢轨联锁,一旦有压标车辆时,警冲标就显示红色或者其它明显的灯光,这样就可避免因越标车辆而发生的侧面冲突;第二、进站道岔的尖轨尖端至进站信号机的这段线路。这段线路没有名称,在调车作业中,有的线路值班员把它称为正线,有的把它称为牵出线,这都不准确。我认为它既不是正线,也不是牵出线,而是一段没有名称的线路。如果把它命名为外线或其它什么线的话,线路值班员就能准确地叫出这条线路来,在这条线路甩挂作业时,就不至于和其它线路相混淆;第三、跟踪检查。我觉得跟踪检查应该取消,只要我们能认真准备接发列车进路,就没必要跟踪检查;第四、擦道岔。现在要求我们扳道员:尖轨擦的象刀片,滑床板擦的象镜面。有用吗?我认为没用,没这个必要。道岔只要定期涂油,能保证使用灵活,再能保证道岔区域无杂草、杂物就可以了。从全铁道部来看,因擦道岔造成了多少行车事故和人身伤害事故?因擦道岔又消耗了多少抹布、砂布、柴油、机油?如果统计起来这可能不是个小数目。就说这些,不妥的地方希望领导,各位师傅们指正、谅解。”
片刻肃静后,会场骚乱起来。
“道岔是不应那样擦,能搬动就行呗”
“道岔要是不擦可省老劲了。”
“跟踪检查也用不着。”
唐永贵赶紧碰了一下简波,简波会意,“静一静,下面请唐站长做指示!”
“说的都挺好,关于赫文亮提出的问题我会向上面反映的。但领导没有答复前,我们必须严格执行以往的规定。时间不早了,还有下夜班的同志需要休息,我就不多说了。就一句话,你们车间要以昨晚的事故为教训,再也不要出事故了。”
身为站长的唐永贵,对赫文亮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特别是擦道岔,虽然赫文亮讲的有道理,可上上下下把擦道岔做为运转车间文明生产的主要内容来抓,车站这一级怎能取消呢。
“散会!”
简波话一落,乱哄哄一片。
唐永贵没起身,简波也还坐着。
“小赫,昨天的发言真不错,大伙在背地里都夸你呢。”扳道房里,解宝财对赫文亮说。
“我说的不知对不对。”
“对不对无所谓,你没看出唐站长的意思吗,他主要是想了解了解你的水平。看来他对你很满意,散会后有人听到了唐站长和简主任的对话。”
“怎么说的?”
“意思让你早点出徒,说过个一年半截的就要提你当助理值班员。”
“我哪行。”
“怎么不行,要我看别说当助理,将来就是当值班员,当主任什么的都行。”
电话响了,赫文亮接电话。
一列货物列车通过后,解宝财回到了站里。他知道,赫文亮在利用列车间隔时间复习高考。
室外下着雪,刮着北风。室内大肚滚炉子有一侧都红了。赫文亮脱去棉大衣,拿出一本“中国近代史”,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
扳道房的小窗前一个人头闪过,谁?书还没来的及藏门就开了。钻进屋内的气流,掀起几页“调车作业通知单”。门关上,来人的棉大衣带来一股清冷的气息。
“是你呀。”赫文亮起身,挪动一下解师傅坐的椅子,“你坐。”
来人谭吉森,是赫文亮二嫂的六弟,今年也刚好二十二岁。他大圆脑袋,短脖子,两个大肥脸上有许多小疙瘩。眼睛虽挺大却是单眼皮,总是闪着疲惫的光。乍往脸上看,没有眉毛、睫毛,这两样东西矮、细、疏、黄。他的外形呆滞,心却精细,写的一手好字。
手里的帽子拍打身上的雪,“我来一次了,不是你的班。”
瞅着地上的旅行袋,“你这是要去哪?”
两人虽是亲戚,但不走动,赫文亮只是在二哥家见过谭吉森两次。
“出去转转,没个固定地点。”
“找我有事?”
压低声音神秘地,“你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吗?”
“干什么?”
“我从安丹手表厂买的手表表把,拿到各地去卖,买时按斤,卖时按个,出去二十几天就能赚到一千来块。”
“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才二十四。
“我上次刚好二十天,就净剩一千多。”
“真的吗?”
“骗你干什么。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有的话咱俩一起干,我一个人出门太孤单。”
“有,当然有啦。”
“那好,二十天后我来找你。”谭吉森戴上狗皮帽子,提起黄色旅行袋,“车快到了,我走了。”
送出门外,“慢走,来得及。”
能是真的吗,真是那样的话,不出一年不就成了万元户吗。赫文亮放下“中国近代史”,心中的火比“大肚滚”还旺。
五十四
“三姐来啦,快进屋。”
赫文亮一个人在家复习高考,四哥、四嫂已搬到钢厂住了。
章娅莲把一本数学高考复习资料放在炕上,“看看能用不?”
翻了几页,“挺好,能用上。”
“听说唐站长在全站大会夸你呐,这下你可出了名,全车站没有不知道你赫文亮的。”
“那天突然叫我发言,吓得我这里怦怦直跳。”手在心口窝比划着说。
“煅炼煅炼就好了。”
“我看三姐也没煅炼,讲起话来却那么自然,一点都不怕。”
“咋不怕,我这里怦怦直跳。”也在心口窝比划着。
“三姐取笑我。”
章娅莲捋了一下金发,“告诉你一件好事。”
“什么好事?”
“中心站人事和劳服经理找我谈话了,叫我当劳服的副经理,星期三也就是明天去公司报到。文亮,这回我再也不用挎个蓝子各处叫卖了。”
“太好了!”
“还有件事,三姐必须跟你说。”章娅莲的脸色在变换。
“怎么了,什么事?”
“你和陶晓丽处的咋样?”
“挺好的,她常来帮我洗衣服,有时还给我做饭。怎么了?”
前几天,赫文亮还给陶晓丽买了一付皮手套。不见陶晓丽戴,昨天问她是不是不喜欢,陶晓丽说:“喜欢,你买的东西我都喜欢,我是舍不得戴。”
“你俩别处了。”
“什么!为什么?”
“别问了,反正我不同意你们再处下去了。文亮放心,三姐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
“不!我就要陶晓丽,别人谁也不要。三姐,你是不是觉得我能考上大学,怕将来陶晓丽配不上我?”
章娅莲不说话,心里好象在想事。
“三姐,就是上了大学,今后无论干什么我都不会离开她。”
看来不说出原因,我这个感情专一的弟弟是不会和陶晓丽分手的。“文亮,最近我和陶晓丽卖货时经常看见一个男人找她,两人嘀嘀咕咕的还背人,特别是背我。”
“是不是她哥哥或是什么亲戚。”
“看那个人的热乎劲绝对不是。”
“如果是呢?三姐,我相信陶晓丽,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唉,你这个人啊,什么事非得跟你说透,告诉你吧,那个人就是陶晓丽上两届的同学叫冷力。我都调查清楚了,他们在学校就好上了,听说还发生了那种关系。”
“哪种关系?”
赫文亮心里明白三姐说的“那种关系”指的是什么,可不愿相信。两只期盼,还有让人怜悯的眼神望着章娅莲。
“我的傻弟弟,还能有什么关系。”
“能是真的吗?”
“看陶晓丽倒不是那种人,可人家说的有鼻有眼的我也断不准。唉,这种事谁又能断准呢?我觉得还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结了婚再后悔那就晚了。”章娅莲知道,离开陶晓丽是赫文亮最痛苦的事情,但大事大非面前,当姐姐的必须有个明确态度。“文亮,我不同意你们再处下去了。”
赫文亮呆呆的,他已经没了思想。
“有没有要洗的衣服?”
“没有。”陶晓丽已经洗过了。
“饭做了吗?”
“没有。”也确实没有。
“我做饭,你好好学习。”
哪还能学习。
在学校,比陶晓丽高两届的冷力看中了她,每当下课时就来纠缠,要求和她处对象。处对象、谈恋爱,年龄还小的陶晓丽感到羞怯,对冷力的追求明确地回绝了。但冷力还是常常来找她,弄的陶晓丽心烦意乱。还好,冷力毕业了,陶晓丽得以解脱。章娅莲说的“那种关系”纯属谣传。
回城后,有一天陶晓丽和章娅莲在站台上卖货,冷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说是有事,硬是把陶晓丽拽到了避静处。打那以后,冷力隔三岔五来到车站,死皮赖脸地烦扰陶晓丽。每当这时,章娅莲都远远地看着,眉头紧蹙;每当这时,陶晓丽都心乱如麻,惶惶不安,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吃饭啦,收拾收拾吃饭啦。”
章娅莲把赫文亮魂魄招回了体内。
赫文亮未能接受“那种关系”,他疏远了陶晓丽。两次接触,陶晓丽觉查到了赫文亮的变化,虽不十分精明的她,也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情,陶晓丽痛苦地离开了赫文亮。就这样,两人没有明了的开始,也没有明了的结束,但两人的心里却留下了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美好情感。
五十五
赫文亮拿着一付信号旗走出运转室,准备接当天的第一趟列车。
“文亮,文亮!”章娅莲从南面走来。
“三姐,有事?”
“有人给你介------”
陶晓丽从北面的房头出现,愣了一下,想退回去。晚了,她只好拖着不自然的身子前行。
陶晓丽向赫文亮、章娅莲点点头,忧戚的脸上挤出一丝苦涩的笑。
紧攥胸前的塑料筐,挪动沉重的脚,脚上好似捆有上刑场的脚镣。大滴的泪珠滚落下来,眼睫毛被黏成一小绺一小绺的。陶晓丽多想回头看一眼心爱的人,多想象从前那样跑到赫文亮身边细语绵绵,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不能了,再也不能了。又有两滴泪珠落在了篮子里。
“文亮------”
赫文亮注目远去的陶晓丽。
“文亮,我刚才------”
“对了三姐,你刚才想说什么?”
“有人介绍个对象,明天我领你去看看。”
“不了,我不想看。”
“那怎么行,我和人家约好了。”
“三姐,我真的不想看。”
可也是,现在叫他相对象怎能行。“那好,你去接车吧。”
扳道房里,赫文亮盯着窗外,陶晓丽郁郁的脸总在眼前出现。
玻璃上的一双大眼睛与屋内凝滞的眼睛撞到了一起,赫文亮吓了一跳。
谭吉森进了屋,双手几乎贴在炉筒上,“呵,这天可真冷。”
“回来啦,还顺利吗?”
“非常顺利,这次出去又挣了一千多块。怎么样,跟你说的事考虑好了吗?”
“没什么好考虑的,我跟你干。”
“那好,我们明天坐九点半的车去安丹拿货,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天就能回来。”
“行,今天请假咱们明天就走。”
临行时,谭吉森千叮咛万嘱咐:“这事不能和任何人说,就是亲戚朋友也不能说。”
“放心吧,我不会跟别人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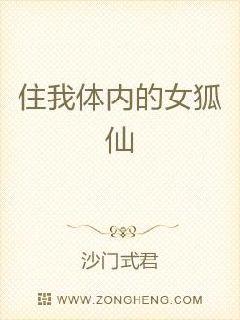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