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求生(上)
天水河从中洲流下,汹涌地流往东方无尽海洋,顺道将东云洲拥进怀里。而从东云洲南岸下河,乘一叶小舟,只需三五日便能到去到青丘了。东云洲北岸与河东隔着若水遥相呼应,但若水水流湍急,难得敢有冒险的商旅一试。
如今天下大乱——帝国分崩离析,主动抽身东南域,使得东云洲,青丘,连年山甚至一部分雨师地界都四处征伐,各自称王。东云洲虽是偏僻一隅,但对权力与统治的渴望依然不逊他处,连年征战,百姓的衣物一月更比一月残。
像平常似乎永不停息的战事一般,黑色的重甲军士如同洪水般奔涌而来,整齐肃穆但却面露疲惫的矗立在巫山城外围。
今天巫山城外的风格外的肃穆,天上的飞鸟和水里的游鱼都屏气凝神,除了日头还战战兢兢地转动着,这方天地间的人眼所见的物件,那老树上的枝叶,那老城上的坚石,那石路上的细尘,都失掉了往日的轻松......
那些士卒全身铁甲,左手持一深黑色铁盾,右手中一根两米有余的长槊,背上则背着两柄亮银色的弯刀。头盔上的雉鸡翎飘扬着,往哪里飘荡哪里便有呼呼风声。
将士身上所附的铁甲,不知何时便忽的燃起一层透明的红焰,说是焰火,却仿若幻觉一般若隐若现,但若是定睛看去,那一层层的暗红,闪动着火焰般的舞蹈,真真切切地附着在这些铁甲之上。但相比于火焰,这层诡异的暗红更像是一层保护粘膜,但那弱不禁风的厚度能够有多大的保护作用,谁也不晓得。
一万凉阴铁卒,如一张大若天空的额黑布,压得地上的虫鱼花草全都抬不起头来。
所有的目光都在它们身上了,仿若这些铁甲一齐耸动,就能把眼前这座小小的巫山城推倒;那些个肃穆的军士一人喝一声“杀”,就能把这城里大大小小的生灵惊得魂飞魄散;倘要是让那士卒冲锋,令这刀锋染血,鼓声开始震天,长槊终于横陈,地处偏僻的巫山城怕是再等来援兵之前,就会被踏为平地。
他们倦怠但依然有着熊熊战意的目光直视前方,但心神却只记挂与一人——正立于阵列之前却面色如水的人。
他头戴一顶束发金冠,一身红黑参半的天王甲,后披艳红色大袍,座下一匹汗血宝马,名唤红日。金冠之下,此人脸长得极正,但却不显得愚笨,两条吊眉也长得粗壮,眉毛时常蹙着,眉头也显得规矩,有板有眼的定在两眉之间。一双大眼中依旧闪烁着黑色的光芒。鼻梁极大,在双眼和脸颊之间显得有些拥挤,但棱角却极清晰,如鹰隼一般的凌厉。浓郁的胡须被打理的井井有条,短而黑的山羊胡衬得此人愈发得雄壮。
只见静若磐石的他,忽的抬起手中宝剑,笔直指向天空,又缓缓落下,剑心隔着萧索的秋风指着巫山城的城楼,这城楼好似不禁便打了个寒噤。
“冲城!”他脸色微变,出声不大,但浑厚得很。
“杀!”紧接着,便是来自一万铁骑山呼海啸般的咆哮。
锦旗凛凛,雉鸡翎和着摇曳,冲锋的速度愈来愈快。
战火稍燃,尸体刚刚开始堆积,巫山城便脆弱地沦陷了。
城主府内,那红袍将军领着三四个副将,虽然打了胜仗,但却如同被人灌了毒药,个个面露苦色,也不敢和那将军正眼相望。
“凉阴城被谢长远夺了,汝等有何看法?”那将军背着身子,敲打着桌案。堂上鸦雀无声,只这稳定而沉闷的敲桌声。
“凉阴城乃我军中枢,必须夺回,望君上给臣弟一支人马,臣弟这便和那谢长远去拼个有生无死。”
“报——”话音刚落,一军士便冲入堂中,跪倒在地,捧书而上,直言道:“左将军来报,左浦城与巫山城的粮道被截断。”
砰——那红袍将军怒发冲冠,一拳打在旁边的圆柱上,登时,新鲜的血液便从手心里流了出来。
这堂内只有这将军抑或愤怒抑或无能的喘息声,“我军本是正面失利,不得已攻此小城,这也被他谢长远算中了么?首府被袭,粮草被断,真天亡我也......”
......
隔天。
“喂,你们听说了么,十四帐的那拨人,去抢了别人家的牛,烤了吃肉,还掳来了那农家的小女,一夜欢畅......”说话那士卒神色飞扬,眼里满是艳羡。
另一个士卒却皱了眉头,道:“这要是被将军抓了,还不得杀了?”
“没有的事儿!”那士卒更兴奋了,接着说道:“昨天夜里有位百夫长知道了这事儿,前去上报——你们猜怎么着?——没下文啦!人家该吃吃,该玩玩,第二天起床脑袋还好端端连着脖子。”
围坐在一旁的将士们一个个匪夷所思,要按着前几次那军法,这种家伙不是脑袋搬不搬家的事情,而是怎么搬家的事情。
说话那士卒示意大家不要争吵,听他来讲:“我说兄弟们,我们在刀枪火海里摸爬滚打,能活到今天,那就算是祖坟冒青烟了。下一次,说不定就身首异处,去找那些老兄弟了。你们看看人十四帐的兄弟,活的多滋润。都是长了嘴带了把儿,咱们怎么就不去快活一把?”
听了这番话,这群士卒登时没了声音,不过,大约几个呼吸之间,便再度传来了掷地有声的回话。
“我跟你去!”
之后便是接二连三的应和。
这莫须有的消息和莫须有的十四帐很快就传遍了整座军营。一时间,欲望的心火瞬间壮大,变得火光冲天。大批大批的士卒三五成群地逃出军营。
没人知道这消息的源头来自何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那个时候,那位红袍将军走出帐门,听到没来由的谣传,看到军营里的骚动,粗糙的拳头握起又放下,最终转身走进了帐中,于账外事充耳不闻。
再下一刻,便是你尽能想象得到的女人的嚎哭和婴孩的悲泣了。
这些个将士倒也齐心,三四个人成群,分好一户人家,便用那带着铁扣的军靴一脚踹开老旧的木门,这小院里那条黑黄相间的老狗便狂叫着扑了上去,若是换了常人,见这狗凶恶,即使胆气大,也免不了有几分惧色。
但闯进门来的这几位,可全都是从血泊和尸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杀人的刀枪剑戟都见得多了,更何况是这装腔作势要咬人的狗子了。
只见那黑狗煞有其事地恶扑上来,可尚在半空中,铁靴子便冲着它着脑袋猛踹过来。
登时,这黑狗瞬间飞出两三米,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于是这几个士兵只见再次传出了快活的氛围,边向院子内走去边有声有色地说笑着自己的趣事。
这院子不大,但好歹还四四方方地种着些小菜,菜园子边就是小径,不宽但四通八达,正屋偏屋院门,还有那颗长得极壮的桃树,都能通的到——看得出来这院主人也颇有些情致,不是那些个庸庸碌碌之辈。
这几个兵痞便顺着小径,就近进了这件偏屋。
偏屋极为狭窄,但收拾得十分干净,一张书桌靠着窗户,上面是齐整的宣纸和笔墨,字写到一半,看上去有些神色,但功底不扎实,只是卖钱糊口的水平,远没有大师的风范。墨痕还未干,清风一吹,墨浓处还能偏斜几分。
“你们是什么人!”一个文弱秀才般三十来岁的人拦在这偏屋的门口,厉声质问道。
“滚开!”一个兵痞一马当先,不容得他说第二句话,一脚便将这秀才踢进老旧的书柜里。
其他几个眼疾手快,趁着他收拾着秀才的空儿,钻进了屋里,上上下下的搜刮起来。几个都是力气大手脚笨的粗人,摔摔砸砸自然是不可避免,因此这秀才还没从那一脚剧痛中清醒过来,这屋子里便鸡飞狗跳了起来——残破的宣纸飞到了门上,砚台碎在书桌上,墨水一洒,整个地面和半面墙全都染了黑,士兵们骂骂咧咧着那泼墨的蠢货,但自己搜刮的动作却从没慢下来。霎时间这屋子哪还有半分之前的模样。
踢倒这秀才的士兵搜刮了这秀才的全身,别处一无所获,但在这秀才的左手无名指上竟拔下一枚玉戒指,这玉戒指上雕着些复杂的图案,这士兵心情浮躁,哪里还有时间看这些细节,便和其他小玩意儿一并,匆忙间便胡乱塞到了自己身上。
“仲良?怎么回事?”忽的屋外传来一声清脆的女声。
“阿立,快跑——”那叫做仲良的秀才一听得屋外的喊声,便也顾不得疼痛,起身喊到。
这一下,几个士兵也是反应过来——原来这院子里还有女人?
男人找女人的速度可比老狼扑小羊的速度快得多了,这几个兵痞更是几年都没见过女人,个个发了疯的要冲出门外。
正当这个几人火急火燎的档口,被一脚踢飞的仲良竟不知哪来的力气关上了门,挡在门前,流着血便对着门外喊着:“快跑!”
喊声却被一脚踢断,仲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这仲良身体虽然素来柔弱,但这次竟没有像刚才那般,整个人飞腾出去。
“碍事的家伙!”这人朝着仲良的脸啐了一口痰,又对着仲良的肚子猛地踹出三四脚。
砰——一声清脆的断裂声,这偏屋的门中轴被折断,仲良不成人样,肚子和屁股从这破洞处挤出门外,带血的粗袍子也一并挤出去,看上去极为可笑。但是他的手脚和脑袋却依然直挺挺地拦在门前。
他手指扣着墙壁,指头尖已经伸进这木墙几寸,血迹也慢慢从指缝中渗出。
“妈的——”那个士兵抽出背上的刀,朝着仲良两条纤弱的胳膊各是一刀。
手起刀落,士兵们久历沙场,绝不会出现岔子。
紧接着再跟上一脚——仲良和门剧烈地抖动了几下,却依然停在了原地。
“妈的——脚!”另一个士兵低头一看,却发现这穷酸秀才两只脚也各自攀着墙壁,像吸铁石般紧紧扣进墙里。
刀光又闪了两下,红色便附在满屋子的黑色上,看上去竟有些可怕。
“哈哈——”终于,那士兵收起刀来,再是酣畅淋漓的一脚,这断了胳膊断了腿的仲良,便跟着残破不堪的木门,一并飞了出去,大片大片的血喷涌出来,惹得四周都充斥着一股血腥的味道。
几个士兵欢笑着快速跑出了门,正巧碰见那个叫做阿立的竟刚刚从正屋里出来——这女人居然还颇有些姿色,身材不算窈窕但是纤细的恰到好处,皮肤更是白皙的很,与那十二月天里飘的雪花一般无二,脸蛋也姣好,五官都标致得很,浓郁的长发盘起来,虽然有了些枯色,但仍挡不了她这一脸的可人美丽。
这场景便宛如是丢了一只毫无抵抗力的鲜美小鹿给一群饿了大半年的老虎——众人皆是一哄而上,唯独感刚刚那个出刀的士兵,却被仲良用最后一点力量紧紧咬住裤腿,让他不能即刻冲向正屋。
这士兵便怒了,再次提刀,朝着仲良廋弱带血的脖颈便是一刀,刀下人头落,仲良的脑袋睁着眼睛便被这士兵甩在一旁的菜地里,绿油油的菜叶就全都染上了这鲜红的血迹。
“哈哈——”他不知痛痒,撒了欢似的跟着兄弟们的步伐跑进正屋里。
随之而来的便是阿立的悲戚的哭声。
......
不知道过了多久,几个兴致满满的士兵才一边扯着自己的裤子,一边走出这已经充满血腥气味的院子,嘴里絮絮叨叨得说些这女人那女人的,一两句过后全都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他们脸上眉飞色舞的快乐,当真是不能从打胜仗那里得来的。
这几个士兵走后没有多久,这小院内竟然又进来一位道士模样的中年人。
这道士倒是仙风鹤骨,一席浅蓝色的道袍和道观,惹了不少尘土但还算得上整齐,手中握一柄拂尘,黑柄白毛,极贵重的模样。但他却似乎与那些士兵是不同的货色,先是耽搁了些时间将仲良的头颅四肢全都拼好,再点一把火,配着那颗老桃树,一并烧了——城里尽是烽火,这火也惹不得旁人瞩目。
这道士便盘坐在这火焰之前,念着些古怪的言语,腰间再抽出几张繁杂的符箓,也全都仍在火里烧了。如此这般,便算是做了场法事。
这火依然烧着,但是这道士口诀念完,便起身顺着小径进了正屋。他进门后一怔,正屋内的情景比之屋外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屋不小,但依旧满是一股不可名状的丑恶气味,这道士拂尘拨了拨空气,想要驱走这恶心的味道,但这味道如狼似虎,再又扑了上来。
屋里乱作一团,各种摆设散落一地,金贵的被带走,不金贵的被摔烂。那被仲良唤作阿立的女子,全身赤裸着死在床上,白皙的但了无生机的皮肤印的这屋子里所有物件都愧疚不已;两条纤细的胳膊尽是些紫红色的印子,微微一挤便似乎要流出血来;两条腿以一种奇怪而且恐怖的姿势瘫在床上:大腿以夸张的角度外翻着,小腿被扯了外翻着压在下面,似乎骨头已经断掉,不再能反弹起来,两条腿看上去就像木偶人般,被人随意拉扯撕断;令人作呕的液体和红色的血液还留在床上,多多少少竟还保持着踊跃的生命力;阿立的脸蛋已经被扭捏地不成样子,嘴唇整个红肿着,破裂处自然流出了不少血,额上同样有几滩惨白的液体,想要从眼缝间滑落下来。
这道人两齿一碰,微微念道:“畜生。”但这些对于他来说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并没能引起他更大的情绪。
毕竟乱世之下,人间炼狱。
他拂尘一甩,拿了床脏乱的被子给这含冤的女人遮了遮身子,但这女人到底是死了,且死的不明来由,竟不知是被人狠狠掐着脖子窒息而死,还是被人殴打致死,亦或是被强暴致死。死于非命,大抵说的就是这般惨状了吧。
惨死的人大抵十年后化作一抔尘土,痒一痒歹人的眼睛;歹人依旧不为所动,在明天天亮之前,就能造出更多的死人和歹人。这乱世之中,要么是歹人,要么是死人,非此即彼,没有余地。
“吾道当行。”这道人难得的沉吟一句,这句子便恍若他的明灯一般,印的他的目光直贯千里万里。
正这时,这道人已经准备走出这正屋,没料想这女人死的床上的床头边的小柜中突然钻出一个瑟瑟发抖的脑袋来,猛然间看到这屋子还有外人,便赶忙再钻了进去。
这道人见状,便明白过来:他还疑惑看那院中男人打斗迹象,多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才落得一尸六处,这不短的时间里这女人应当跑出了这屋子才对——原来浪费这么长时间,是为了安顿这懵懂无知的少年,倒也真是难得一片父母心了。
“少年,我见到你了,不过我不是歹人,歹人已经走了,你大可出来。”这道人侧坐在床上,安抚道。
这少年似乎并没什么防备之心,听了这道人两句话,便乖乖地走了出来。
道人打量着这孩子——他似乎已然有十三四岁,到了懂事的年纪。
“刚刚发生的事情,你都看到了么?”道人轻声问道。
这少年点点头,并无言语,他满脸的泪痕和疲累,估计一个人躲在柜子里从缝中瞥见,用耳朵听得的一切,已经不是他这个十几岁少年能承受的了。
“你父母双亡,你,奈何?”道人语气中越有一丝心疼。
这少年也是机敏,一把攥住这道人的拂尘,之后便紧紧攥在手心,不愿放手。
这道人见状,生出一丝恻隐,便道:“我认真与你讲,跟着我要吃大苦头,可能不日便要去见你爹娘,你最好不要跟我。”
这少年不听,道人起身之后,也紧紧攥着拂尘,大有一副你去哪里我便去哪里的势头。
“罢罢罢,权当我离尘孽障又多几分。”
离尘拉了这孩子的手,冰凉的紧,便走出院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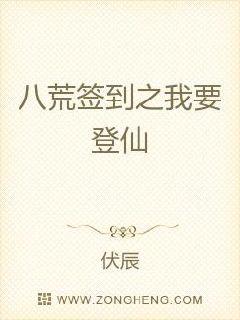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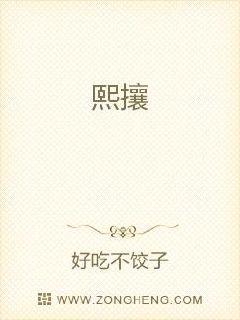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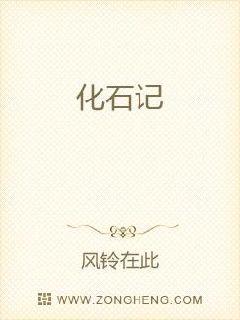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