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 魔剑主
张禁想不清楚,这四字如何出现在他的神识之中,进而化成一条漆黑的锁链,将他牢牢缚在半空。
他大惊失色,想要咆哮却发不出一丁点的声音,他无法感觉到疼痛,却可以感觉到那锁链带给他的深深恐惧。
“你的灵魂,我收下了。”
锁链延伸成了牢笼,变成一颗黑色的球,挂在天上,像是日蚀中的太阳。
楚流离看着它,却从这世间万物找不到丝毫与它相似之处,那深邃的漆黑总是让她产生很多复杂晦涩的情绪,有狂暴、有失落、有绝望、有哀伤,但最多的,还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疯狂。
但她仍然静静地看,哪怕冷汗已经浸透衣衫,因为她知道,那就是力量的源泉。
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走在钢索的边缘,或许下一刻就会刮起一阵狂风,将她推向那无底的深渊。
于是风来了,在那黑色圆球的边缘吹起一阵阵难以言喻的波纹,时空仿佛因此而错乱,楚流离明明知道自己正踩着大山坚实的土地,却怎么也无法制止心中那失重坠落的错觉,她全身颤抖,仿佛有无数只止不住哀怨的手对她抚摸、拖拽,让她的世界里很快便只剩下阴影一种色彩。
或许这就是深渊吧。她这样想着,艰难地呼吸,艰难地维持着自我,以此抵抗如潮水般灌入意识的黑暗低语,但成效甚微。
她开始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维,无数条混乱的念头在脑海中闪过,她想要抓,却什么都抓不住。
她犹豫着自己该不该向那无边无际的黑暗妥协,跟它融为一体,让它成为自己的全部,却又在千钧一发之际警醒过来,分清这绝对不是她自身产生的观念,只是黑暗强加给她的诸多诱惑之一。
楚流离有些累了,在面对过一次死亡之后,她才发现原来还有一种更可怕的东西名为孤独,她在黑暗中不停地向下飘落、飘落,飘了数年之久,从一名青年姑娘漂泊至垂暮老朽,却不曾有人对她说一句话。
不知为何,楚流离突然想起那个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她模糊地怀疑,这会不会就是他眼中所见到的世界?
“剑青?”她尝试在黑暗中呼唤他的名字,不出意料,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剑青…剑青…”
她一遍一遍地试,一遍一遍地喊,喊得撕心裂肺,哪怕徒劳无功,也要让自己的声音传遍这黑暗里的每一处角落。
她不知道自己喊了多久,也不知道她的声音能不能驱散那孑然无依的孤独,但她就是不肯放弃,直到她听到了同样不知从何方传来的那一声:
“我在,一直都在。”
……
朝阳初升,黎明伊始。
勤劳的人们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对于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比吃上一顿饱饭来得更加重要。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农夫们在金黄色的原野中哼唱山歌,藤条编成的背篓里装满了刚刚采下的粟米,有别于大人们的忙碌,牧童懒洋洋地躺在青牛背上,用竹笛吹奏出一曲曲丰收的喜悦,又从缺了一角的草帽缝隙中,满怀羡慕地望着天上与飞鹰一闪而过的剑仙。
靛脚踏飞剑,握着楚流离的右手,不敢用力,怕她吃痛,也不敢放松,更怕她从狭窄的剑上跌落,一不留神又从指缝间溜走。
这不是他擅长应付的场面,比杀人时还要紧张得多,他还为自己的心神早如钢铁一般,再也掀不起这般波澜。
他只好去想些别的事情平复心境,风雪关在北方,所以他往北走,但他还看不见大雪山,说明走得还不够。
这就是靛的思维方式,直接有效,但乏味无趣,像是一台机器。
脚下的剑其实飞得很稳,况且以楚流离如今的修为根本不必担心会从飞剑上面掉下去,但她还是任由那个黑衣男人牵住她的手,试图平衡着他冰冷的体温。
楚流离并非没见过像他这么冰凉的手,但在此之前,那通常只出现于死人身上。
他不开口,两人就显得无话可聊,楚流离忽然有点怀念那个神神叨叨的他,但那个他就像是刚刚从身旁溜过的云烟一般,一旦错过,再想回头便已然杳无音讯。
这世间大多事情都是如此,若是看得开了,怕是早就成了神仙,谁都看不开,道理至少也都懂了,也就少了些人再去纠结,反正日子还得过,过着过着该忘的自然就忘了,至于忘不掉的,早晚都得成了魔怔。
路还很长呢。
楚流离告诫自己,应当趁这时候养精蓄锐,稳固道心,把那将死之人的神识彻底抹除,留他魂魄中的道行为己所用才是。
她随即抹杀了收束于识海之中那可怜灵魂的最后一丝反抗,将它彻底化为扩充自己神识的养分,用着一种与吞噬金丹时异曲同工的方法。
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她正在噬人魂魄。
诚然这似乎是一条魔途,但至少在这条路上,楚流离并不觉得孤独,她终于明白,原来自己早已失去立身证道的资格,缺少至亲之人的陪伴,证道?证给谁看?
这段领悟来之不易,她花了一天一夜,反复琢磨着断离剑诀中的一个魔字,才发现原来自己迟迟无法突破便是败在了它的身上。
若不成魔,如何使出魔剑?若是能够断得彻底,离得干脆,又怎配被称之为魔?
仙人无欲,魔有。
她看到北风吹来了第一片雪花,剑心微动,一道剑气自震位而生,有雷霆之势,却伤不及那雪花分毫。
楚流离得意地笑了笑,极为罕见地放纵出声,像一朵洁白雪莲染成了赤红娇艳的牡丹。
此时她终于听到黑衣男人那熟悉的声音,只是冷淡的语调听上去又极为陌生。
“只斩魂魄,不斩凡俗,你的剑成了。”
“你不是他,对吗?”其实楚流离早就看出一些端倪,但若是以前的她根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那人沉默一阵,点了点头。
“我该叫你什么?”
他想了想,说了一声:“剑青。”
“那不是你的名字吧。”
“没什么差别。”
靛突然觉得有些烦躁,但绝对不是对她,只是苦恼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反倒是与他心意相通的飞剑开始不停颤抖,仿佛替他解围一般,在极短时间内发出一连串像是嘟嘟声的剑语。
“我懂了。”楚流离静静地聆听,过了一会之后又缓缓说道:“那以后我都叫你们剑青。”
剑语声变了,宛若一串叮当作响的贝壳风铃,听上去便令人觉得开心,但作为始作俑者,靛却始终听不懂,它到底向楚流离诉说了什么。
……
北方有一座雄关,横跨南北,分隔东西。
数百年来,任凭西方战火纷飞,自雄关以东,百姓无忧,尽可安居乐业。
但时至今日,世道却开始变了。
西方早有女王一统天下,四海之内莫敢不从,东土大唐却仍然缩在壳中,抱着天下第一的美梦睡得正香。
如今橙衣大军压境,旌旗连成十里长河,那守关将军才堪堪知道,什么叫做噤若寒蝉。
他不敢做声,看着面前发须斑白的老人,瘦小佝偻的身躯叫人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手中冬青雕成的钝剑曾饮过上万兵马的鲜血。
他自然知道那老人是谁,因此根本想不到,就在今晨老人忽如鬼魅一般出现,一剑斩了他贴身暖床的丫鬟,像是提鸡崽一般单手揪着他的脖子,将他带上城墙。
他记得那时从大雪山顶峰刮来的寒风很冷,但再冷,也冷不过他李宵心中突如其来的恐惧。
一夜之间,未闻金柝,山下高原却搭起了一片黑压压的连营,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处处张弛有度,透着一股子冷血无情。
“真人…”李宵是个糙人,斟酌好一阵子,才想出这么一个蹩脚的称呼。
没人知道风雪夜归郎姓甚名甚,却都知道他来自北国,功力深不可测,从不开口讲话,但修得绝不是道。
他看了李宵一眼,像是在看一具尸体。
李宵心神一沉,哽在喉咙的话再不敢出口,彻底打消逃回长安的念头。
他是当朝驸马,娶长林公主,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只不过是那位公主十三面首其中之一,只因相貌英俊,又是庶民出身难乱朝纲,才被大唐皇帝选中,封了驸马。
唐帝不算昏庸,却因年迈而对长林公主格外宠溺,早年明知李宵短浅无能,仍为他赐了官职,后来又得知他不再受公主宠爱,便发派去了边关镇守,替她图一个眼不见为净。
但风雪夜归郎根本不在乎李宵是谁,更不会去管他是兴是衰,若他想逃亦或敢降,那便一剑杀了再说。
山上天气变化很快,等不多时,便飞来几片乌云蔽日,随后那关下也奔来一人一马,着金甲,持金枪,一身风霜,血染荣华。
她如明月一般清高,背负新月橙旗,单枪匹马,便敢向守关三万雄兵叫阵。
“挡我者,杀无赦。”
她驻马关前,扬旗呐喊,只一句话便让世人听闻什么才叫“凤凰鸣矣,于彼高 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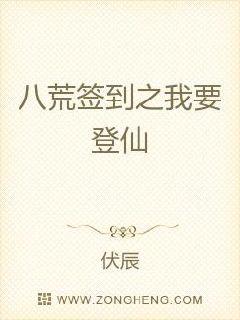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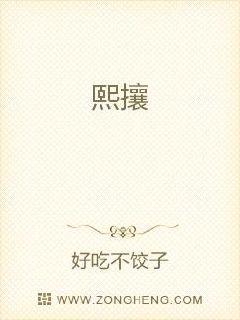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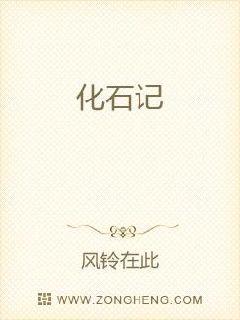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