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土匪
又默默坐着,余新生低着头:
“保保,你要注意观察,不要随便说话,传到了王书记的耳朵里,是会有麻烦的。有人找你说话不要轻易表态。有啥事,没人时来找我。我走了,怕有人来碰到。”
说完拉开门走了。魏师傅还在想,自己刚才是错怪新生,他是不方便说话。
魏师傅已是满头大汗,人要虚脱了。他用力在铲一个苞谷梗疙瘩,锄头随着苞谷梗疙瘩飞了出去,‘扑通’一声人也摔倒。听到后边的响声,有人回过头看了一眼,看见魏师傅‘睡’在红苕藤上,脸朝下一动不动,那人焦急地喊道:
“魏师傅摔倒了。”
听到喊声,队友们回过身,丢下锄头跑拢来,把魏师傅搬过来放平;魏师傅脸色苍白,嘴唇乌紫,一只手冰凉。
有人拉住冰凉的手说:
“急火攻心,中署了。快,哪个到田边去舀点水来,给他揪把痧。”
又有人说:
“掐人中。”
有一人就上去掐住了魏师傅的人中,多一会,魏师傅的脸色才有了点血色。
水来了。大家把魏师傅移到土边的桐籽树荫下,有人上来拉起魏师傅的右手,让魏师傅手指弯曲捏紧,顶住那人肚子。那人用手沾了水,拍在魏师傅右手杆弯关节,弯起自己右手食指中指,用力揪魏师傅的弯关节皮肤,几爪下来,魏师傅的右弯关节处,乌紫了一大片;接着,那人双手又握住魏师傅手臂,用力向下麻,回过头要一根绳子,在手臂上捆扎起来。
这时,魏师傅也睁开眼,疲惫地望着大家。
人问:
“老魏,有啥子没有?”
魏师傅没说话,有气无力地摇头,肚子阴痛难受。
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说道:
“魏师傅,这两天压力大,精神上受不了,最好还是送到大队医务室去看一下,稳当点。”
“没事,揪痧过后,手杆捆上,只要麻胀过后就没事。”
“你们看,他的脸色还是不好,到医务室看一下稳当。”
“易师傅,我们两个送他去。”
易从兴没有犹豫,拉起魏师傅背起就走。易从兴一人拖三个娃儿,老婆多病,做不了重活,自己除了在生产队上班,抽空还编点蔑货卖,卖蔑货也是小心翼翼,街上随时都有市管会的人来没收东西。编蔑货还是不足以支撑家庭,就只有偷了。不能饿着孩子,他们可是祖国的花朵儿。知道魏师傅在家打衣服进学习班,缝纫机也被没收,易师傅有些鸣不平。魏师傅可不像自己,多少还干了点不光彩的事。一个大队的,魏师傅也知道自己家穷,打衣服多数时间是不收他的钱,易从兴也知恩图报,有时就编个蔑篼篼、筲箕的送魏师傅,去了还叫自己吃了饭走。魏师傅父子俩是好人,为什么好人就遭殃呢?易从兴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就里。
按照胡医生的吩咐,易从兴把魏师傅放到凉椅上。胡医生看魏师傅脸色卡白,毫无水色,摸了脉,站起来走进柜台前坐下,写了单子,递给中年女赤脚医生,女赤脚医生接过单子看,走到药柜前拿出两个药盒子,取出两支针剂,用摄子敲掉针剂帽帽,拿出一支针管,摄子拈上一颗针逗上,插入针瓶,将药剂吸入,又用摄子夹上一坨棉球,在魏师傅左手杆上擦拭两下,将针头扎了进去,药水很快推进了魏师傅的肌肉里。接着女赤脚医生又拿过一包葡萄糖,舀了两勺葡萄糖在搪瓷盅盅里,冲了一盅葡萄糖开水,摇了几下,水稍凉点,递给魏师傅喝下。
胡医生平和地说道:
“没事了,老魏,回去休息半天就行了。”
魏师傅想站起来,腿没力,还想趟一会。
胡医生:
“别急,休息一会再走,他有点心慌,让他平和一下。”
话音刚落,满脸汗水的女儿安静含着眼泪跨进门,哭着喊道:
“爸爸。”
魏师傅闻声,鼻子一酸,眼里瞬间包满眼泪。在场的其他人鼻子也酸了。
魏师傅叫了声:
“哎哟!”
艰难地伸了伸麻木的右手,大家看到魏师傅右手一片乌紫肿胀,血管突起。安静忙拉过来,吓得失声哭了,说:
“爸,你怎么了?”
易从兴恍然大悟,忙解释:
“没事,刚才我们给他揪了痧,手杆捆起,‘死’了血,绳子松开就好了。”
听了易从兴的解释,安静才止住哭,也看到手杆上捆着的绳子,忙伸手就去改(解)。
胡医生看见安静心急火燎地解绳子,伸手制止:
“慢点!绳子已经陷到肉里去了,用力要拉伤。”
听到胡医生的话,安静才放慢了动作。好一会,魏师傅肿胀的手杆的颜色稍微正常点,脸色也不再卡白。
胡医生和颜悦色:
“老魏,受了什么剌激?心跳得这样厉害?”
魏师傅眼里掠过一丝惊慌,生怕人知晓今天早上发生在知青点的事,特别不想让女儿安静知道,没说话,只摇头。
易从兴想开口,被魏师傅用眼神制止。
安静看出了爸爸的慌乱表情的内容,其实爸爸不说,安静也知道早上发生的事。上班时,大家都在议论哥哥骂王书记是土匪的事,大家也没有回避的意思。还好没有人说其他,她没开腔,只是默默地铲草,心里是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哥哥也没来铲草,不知道哥哥现在怎么样?亓梅也没上班。有个去办事来晚了的社员说,魏师傅被人背到大队医务室去了,魏安静一听,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丢下锄头就开跑,直奔大队医务室而来。
没有得到答案,胡医生也没继续问。大家在一条街上住,彼此都熟悉,魏师傅一家做裁缝,胡医生一家开药铺。解放后,胡医生成了乡卫生院医生,魏师傅还继续做裁缝。为了充实大队合作医疗点的发展,公社医院部分医生下放到了各大队新成立的医务室,胡医生来到了东风大队,机缘巧合,魏师傅一家也下放到了东风大队第二生产队。有了三灾二害的少不了又来麻烦胡医生,尽管魏师傅住在街上,到公社卫生院,比到大队医务室要近一些。但是,生了病还是愿意到大队医务室来看病,原因简单,一是吃了这么多年胡医生的药,也就信了,二是便宜,看一次病,大队医务室只需缴五分钱就行,何乐而不为。当时的农村社员也没有那么娇气,绝不会一生病,动不动就往大医院跑,基本上都是在大队医务室拿点药就行,严重的打点点滴输点液就解决。虽说大队医务室条件简陋,医资力量不强大,倒也解决了社员群众的生疮害病的困难,也未出现过一次医死人的医疗事故。有次差点出事,幸亏胡医生有经验,处理及时,那个犯脱阳的社员硬是化险为夷。
眼看魏师傅脸色不再像刚送来时那么吓人,安静赶紧去扶准备起身要离开的魏师傅。魏师母也急匆匆跑到了大队医务室,一脸的焦急,生怕丈夫有个意外闪失;看到丈夫没有什么大碍,悬着的心落了地。还是关心地问起:
“安静,你哥哥呢?他到哪去了?”
安静被问得哑口无言,她也不知道安新去那儿了,只知道他没来上班。
“走吧,话那么多。”
魏师傅轻声说道。魏师母只好不问,送丈夫回大队学习班去。
当大家都离开,剩下魏师傅一人,他的心情还是狂乱得难以言说。他在反复回想自从缝纫机被没收,到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切,冥冥中有一些不能言说的东西正在发生着,向他父子袭来;让他这个父亲左右为难,对儿子安新他也难以启齿。他只好在心里忍着,让他忍得难受,终于在铲草时摔倒。但是,作父亲不但不能向安新说,更不能向家里其他人说,免得他们担惊受怕,只能自己扛着。尽管自己没有伟岸的身躯,为一家人遮风挡雨,但是自己也有一颗赤诚的心,愿意为一家人,殚精竭虑。
进来第三天,夜深了。
魏师傅正准备放下蚊帐,关灯睡觉。易从兴的床还是空的,看来今天晚上,他又不回来了。魏师傅有时觉得学习班办得奇怪,进来的人,有的很随便,比如易从兴吧,白天上班肯定要来,晚上学习是经常迟到,甚至晚上还可以不回来。大队干部都知道,易从兴他不会跑,或者说他根本就跑不了,生病的女人和三个年幼的子女,需要他照顾,他们离不开他,他也舍不下他们;其次,办他的学习班也只是做做样子,不然偷盗难以杜绝,其他也会效仿。大队每年的贫困补助还是少不了易从兴的;他也不是好吃懒做的人,毕竞只有一双手,要撑起这个千疮百孔的家,他已经是费尽了洪荒之力;四十开外的他,头发已经花白,脸上也是沟壑纵横,或深或浅爬满了宽阔的脸庞,有了一丝难以言说的苍老。其他就没有那么自由,有的晚上还要‘过堂’,严重的晚上还要受点绳索皮肉之苦。魏师傅除了进来的第二天上午,受了半天王书记的审问,再也没人来问他。
魏师傅看见干儿子新生,总是黑着一张脸,不说话。学习班的人都有点怕他,但是他从来不动手捆人打人,他说话声音大,手上力气也大,手下的民兵都服他。一个身材魁武的人,在自己的婆娘面前却显得是那样的无能为力,让旁人都不可思议。是有什么把柄落到女人手里,也不像,或者是身体上有什么缺陷,也没听他女人在私下说起过;母子俩对媳妇也都束手无策,一个家庭搞得鸡叫鹅斗似的。一旦新生真发起怒来,婆娘又规规矩矩。然而,他不可能天天发怒呀,家庭毕竟是一个讲情、不是争强斗狠的地方,也不是天天讲理的地方。他在不遗余力地挽救,最终他的努力付之东流,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余新生在心里说着再见,我们的相识是一个错误,我们的结合更是一个错误结束前的纠缠。再见吧,既然不能相濡以沫,那就相忘于江湖吧。魏师傅看着干儿子的婚姻如此糟糕不堪,他也把双方请到家中劝过,也让安新旁敲侧击地观察过,得到的答案也让魏师傅也大吃一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余新生的婆娘有‘外遇’,还传得沸沸扬扬。魏师傅先前抱定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观念,在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难道他还没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魏师傅现在的处境也让他无能为力,安新又遇上麻烦,更是帮不上一点忙,内心反倒有了十二分的愧疚。
魏师傅打完帐子中的蚊子,正伸出手拉开关索索。啪啪,有人敲门,声音很轻,不像是民兵来找人时那种擂得山响的敲门声,是谁啊?这么晚了还来敲门,不可能是新生吧,很少看见他在知青点过夜。魏师傅犹豫了一下,没有立即开门。啪啪,又敲了两下,魏师傅还是起床开了门。
只见门口站着个女人,没看清,把魏师傅吓了一跳。夜半三更,女人来敲门是啥意思?难道是董必芝,下午收工时,她主动找他说了几句话。她是因作风问题进来的,被人捉了现行,地方也特别,在男的家猪圈屋,这事在农村本算不了什么,但她偷错了人呀,她偷的那男人是大队王书记的妹夫,不是自己妹妹偷人,王书记能忍,可王书记的妹忍不了,她要上吊自杀,哥哥岂能袖手旁观,不能把妹夫拉去游街示众办学习班。王书记的妹妹认定是董必芝主动,都跑到家里来了,得办她的学习班。难不成说几句话,她晚上就…魏师傅心里掠过一丝紧张,便嚅嘘道:
“你是….”
还没等魏师傅问完,对方亲切地叫了声:
“魏师傅,是我。”
听到声音,魏师傅也看清了来人,是李世芳,绰号媒婆。她也是学习班的一员,学习班一共有两个女的。魏师傅站在门里没动,也没让进的意思,只是试探地问:
“有事?”
李世芳轻笑了声,算是回答。眼里有想进去坐一坐的意思,看魏师傅好像不愿意,讪笑道:
“天这么热,睡得着?”
又说:
“我想问你件事。”
语气肯定,等待魏师傅表态。
魏师傅让开,李世芳径直走进来,在易从兴床上坐下。魏师傅重又撩起蚊帐,坐下等着李世芳问事。李世芳没有急着问事,开口拉起了家常:
“魏师傅,你们家安静有二十一了?”
魏师傅警觉,她哪知道这么清楚:
“马上二十一了。”
李世芳又说起了另外的事,关切道:
“魏师傅你们三家裁缝铺,你们家的位置最好。做衣服的人应该最多。”
魏师傅警觉。她是来探口风,魏师傅没有接着她的问话说:
“做不了了,缝纫机都遭公社收了。”
“哎。”李世芳也叹惜一声,对魏师傅的遭遇表示同情。不无遗憾地:
“魏师傅啊,现在做什么都难。”
魏师傅感觉奇怪,李世芳东一榔头西一耙子,她到底要说啥子,她这么晚来的目的是啥?魏师傅搞不清楚。魏师傅记得,李世芳比自己晚一天来大队学习班,她实际上早就进了公社学习班,才从公社学习班转‘学’过来的。她进学习班的头衔是‘人贩子’,她说自己冤。帮人‘说媒’,做好事积善缘,最后把自己‘说’成了人贩子了。她说年青人相互之间不认识,中间得有人牵个线搭过桥,连戏上都有槐荫树作媒的唱词呢!西厢记中的红娘,那些远隔万水千山的年青人更需要人来撮合。自己说了这么多年的媒,没出过什么差池,都怪背时的唐兴良,他说他在江苏南京那边有个亲戚,求他在当地找个媳妇,他一个大男人,没有这方面资源,便把自己的大女儿嫁了过去,并亲自送过去,那边亲戚希望他多介绍几个过去。他一回来就来找她,双方一拍即合,约定她负责在当地寻找适婚姑娘,唐兴良负责在那边找婆家,酬金二一天作五,几个回合下来,收益还不错,双方都没有收手的意思。资源也有枯竭的时候,合适的人选越来越少。这天,李世芳碰见一对小年轻正闹矛盾,男的丢下女的独自走了,女青年在那里嚎淘大哭。李世芳灵机一动,走过去安慰那哭泣的女子,耐心劝慰很快平息了女子的哭泣,也获得了女子的好感。一来二去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忘年交。眼看时机成熟,李世芳试着介绍起朋友来,把她现在的男朋友也作了比较,女子正处在赌气之中,听她也说得入情入理,冲动之中,相信了李世芳的花言巧语,随唐兴良去了南京那边,女子发现与之前说的大相径庭,坚决不答应,但是为时已晚。女子远离父母亲人,孤身一人,只得束手就擒。安顿下来,女子寻找机会与家人取得了联系。家人报了案,唐兴良李世芳被抓了起来,唐兴良知道罪责难逃,是自己连累了李世芳,把全部罪责担了下来。接着,批斗会游街示众,唐兴良判了五年徒刑,李世芳落了个进学习班的待遇。
说完,李世芳关切地问了句:
“魏师傅,你们儿子什么时候结婚?”
魏师傅如实回答:
“旧历九月十六。”
“好啊!”
李世芳笑笑,又问:
“亓梅与你儿子,般配?”
这不是屁话嘛,两人好得如胶似漆。魏师傅觉得问得莫明其妙,但是没有反驳,他想听下去。
李世芳盯着魏师傅再问:
“魏师傅你是怎么进来的?”
魏师傅觉得这不是明知故问,自己走资本主议道路,在家干私活,被捉了现形。他想开口,还没等魏师傅说话,李世芳又说:
“打衣服,鸡鸣场有三家,他们两家好好的,没有被收机器啊!魏师傅是不是你得罪人了?或者…”
李世芳故意停了下来,给魏师傅思考的空间。魏师傅想不出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人,他们一家在鸡鸣街上的声誉是有目共睹。
李世芳看出来魏师傅是个忠厚之人,知道的肯定也不多,便婉转地提醒:
“是不是另有人喜欢你们儿子或者未过门的媳妇,把你连累了?”
说得委婉,云淡风清。
她这么一说,魏师傅像学生受到老师的启发,大脑里灰蒙蒙混沌的东西出来了,像小鸡嘬破蛋壳。都是那背时的王鲁川,是他一直在追自己儿子的未婚妻。
魏师傅想过一脸的愤慨。李世芳知他明白,开门见山说道:
“魏师傅,这事我不说,你也明白。”
魏师傅是明白,他劝过儿子安新,他没有听。儿女之间的事,父母只能劝,不能强迫,更不能棒打鸳鸯,要是那样,悲剧性后果,随时都可能发生。在鸡鸣街上就有这样让人不堪回首的例子,隔壁合作商店孔师傅女儿孔令嫒,喜欢上一农村小伙子,父母坚决不同意,结果姑娘废了,一天神精兮兮,班也上不了,窝在家里。此时,魏师傅也是心如乱麻。
李世芳的媒婆不是浪得虚名,那是真枪实战打出来的,各色人际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说得双方心服口服,心花怒放或者心痛难忍。简单的几句话,让此刻的魏师傅的心像凿了一个洞,汩汩向外冒血。李世芳在期待,魏师傅在煎熬。
李世芳又探讨地说:
“魏师傅,你说是不是喜欢上一个人,真的丢不下?要是那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给一个家庭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像扔手榴弹似的,一连扔出去几个,个个都击中要害,在魏师傅心上炸响,满堂开花。魏师傅的身体微微震颤,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这件事对家庭的危害。其实魏师傅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件事同样也在影响另一个家庭。李世芳吸取上次说媒失败的教训,没有去谈对方的优势和地位,而且说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家庭的影响,有点孝顺的人,当家庭受到影响或遭之不幸时,都会思之再三。魏安新会看着自己的父亲身陷囹圄,家庭陷入绝境而无动于衷?她不动声色观察魏师傅的表情,她感觉到魏师傅的表情已经够难受了。她不失时机地说:
“魏师傅,这事其实很好办,也很简单,就看你愿不愿意,如果愿意,就一句话的事。”
魏师傅满脸涨红,嘴唇颤动,再不是媒婆刚进门那么无动于衷。李媒婆一连串的问题,他也在心里想得明白,一句话:退婚。可他开不了口啊!他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要是那样,对亓梅和安新的打击是不可想象,真要有个三长两短,就追悔莫及。
李世芳又说:
“魏师傅,我知道你直接去说,肯定开不了口,就是找你们的媒人罗么娘,你也开不了口。不要紧,只要你同意,而且坚决,由我去说,谁叫我揽下这差事呢?你也看到或者听说过退婚的事,都是父母一句话,子女一般不会反对。如果那样,或许你家安新下半年工厂招工还有希望呢!”
说得魏师傅胆战心惊,六神无主,有气无力说了句:
“李大姐,这事让你费心了,容我说通了安新回答你。”
这样的回答是妥当的。一是贸然答应,兑不了现,那也不好下台;二是他想清楚如何去说,安新才能接受;三是说了,双方都接受了,他的缝纫机能不能拿回来,魏师傅的想法是实际的。
李世芳比魏师傅大,快五十的人了。这次还是从大队王书记那里领了任务来,为了把事情办成,王书记特地把她从公社学习班‘转’学过来。她也知道这事有难度,但是,她也说过比这还难的媒。那是双河镇的一对男女,男的在部队当兵,姑娘在家务农,菜蔬队有一小伙子看上了那姑娘,托她说媒,她先拒绝,破坏军婚是要坐牢的,她不想冒这个险;但男方许以厚礼,很有诱惑。她还是冒险一试,把姑娘说动,退了婚,嫁到了菜蔬队,她担惊受怕了好久。上次去亓梅家说媒,媒没说成出了大事,她是不敢再去亓梅家。魏师傅进了学习班,以她对魏师傅的了解,她认为这媒能说成,只是要多费点精力,反正在学习班,时间有的是,大家天天见着面,说事也方便,也不耽误工作。
李世芳得到了魏师傅的答复,没有立即离开,反而是静下心拉家常,她要让魏师傅紧张的心情得到平复,同时也要取得魏师傅的无限信任,至少在这件事上自己没害他的意思,是在帮他,将来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也不会怪罪自己。
这一夜,魏师傅真的失眠了。
接下来几天里,魏师傅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对安新说这事。
今天早上,安新终于出事了。魏师傅现在关心的不再是国庆节后是否结婚的事,而是如何让儿子安新,能否躲过有可能的牢狱之灾。
魏师傅望着窗外落日余辉,在鸡鸣山巅的松枝上涂抹得惨淡灰红,他久久凝视,眼里有了晶莹的泪花,慢慢变得一片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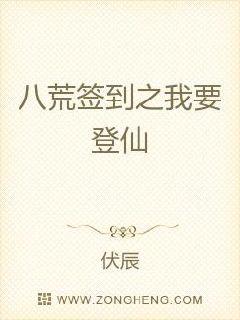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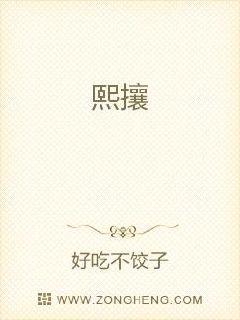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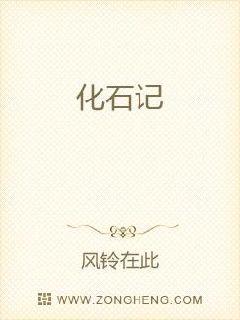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