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理
深褐色、干瘪、带有树皮的纹路,以及与之相反的光滑触感,因为脱水只能依靠其骨架来推测原本的体型,肋骨的纹路清晰可见,腹部严重的内缩,脖颈以上、四肢皆被截断。一副躯干,好似风干的风味腊肉,不过既然看起来内脏完全没有被处理的样子,多半也不会让人产生什么食欲。寻常人或许难以想象,一具似乎没有做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是怎么保存的如此完好的,以至于肢体截断处的血管、经络、骨骼连同脂肪的痕迹都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但这也可能是它被与这个房间里其他“疑似异常”的物品一起随意保存的原因吧。
“不太合适。”将用来开门的双臂与干瘪躯干对接以后发现这副躯干主人原本的体型大概在一米七出头,不仅是躯干脱水风干的原因,其比起高大的白褂男小上不少。于是,满足了自己恶趣味的男人再次擦了擦似乎再也干净不了的嘴巴,将双臂丢在了地上,带上躯干离开了。
狼,独臂者的称号。虽然他不相信一具从世界各地拼凑起来的诡异干尸能有什么用处,但他依旧招集了自己的家族。虽然不断有朋友、战友变成旧识,但任务必须执行。虽然就如同失去自己的姓名一样失去了手臂,为了希望,也义无反顾。所以跪拜在此处,呈上贡品。
白袍的祭祀取下了面前的黑色锦布,露出遮盖的盔甲。寻常金属的铁灰色,头部是整块的金属板,略显圆润,两眼留出了横向缝隙,而口鼻部则是一个个细小的空洞便于呼吸,头盔几乎包容进了整个脖子,然后在下方附以大块的链甲用以衔接身体。身体部分一样是厚重的金属板片,大块无缝的金属连同肩膀一起包裹。而手臂以及腿部则是一件由链甲构成的金属内衣,躲藏于大块板甲的防护之下,连接着身体的各个部分,填充着板甲下的脆弱缝隙。三层交叠的金属手套保证了手臂的运动与安全,由上身板甲下延出的裙摆则保护了板甲长裤与上衣可能的缝隙。磨平而不反光的表面,唯一的痕迹,就是由四个等腰三角形构成的十字,三角形的底部内陷,顶角相交,标志着骑士美德:“忠心、虔诚、诚实、勇敢、荣耀及荣誉、无惧死亡、对穷人与病人伸出援手、尊敬教会”。
陈旧的铠甲愧对神明,所以蒙与黑色的锦布。现在,光明重新青睐了它,就算照耀它的,在这个夜晚只有烛光。而祭祀则褪下白袍,以黑布裹身羞于见人。
银质的托盘,其内摆放一只同质酒杯,内盛红色汁液,左右各置放半块圆饼,托盘中间则是那具分散的尸骸。先是双腿,以膝关节为中点对折,并列排放,以一根未编织细草绳固定。其上是躯干,截断的双臂则复于原位,交叠覆于胸前,腹部之上则是头颅。狼单膝跪地,单手托盘,待祭祀临近,面部微起,张开下颚。而祭祀则将白袍轻披于肩,伸手入盘,从两半圆饼上各捏下一小块,俯身下去,将饼喂入狼的嘴中,再单手举杯,轻托下巴,喂食汁液。起身用叠好的白袍交换贡品,却不敢多瞧一眼地上的独臂者。双臂托起,缓缓踱步,将银盘置于盔甲前的石桌之上,再次捏下两块小饼,拿起酒杯,喂食那银盘之中的头颅,那头颅将受领的红汁尽数吸去,未漏一滴。仅剩自己未受此餐,同样的,口含圣饼以津(口水,铭感词)液润之,但举杯时却再难入口,反复笃定便来到俯身者面前,撩起衣袍双膝触地,以蜷缩之态示人,念道:“我有罪!”见此,狼披手中白袍于身,将手置于其头顶,轻声道:“我并不怪罪你,就如同他定会免赦你的罪,去吧。”闻声,祭祀便起身迅步来到石桌前,额头的血混着红汁一同饮尽,礼毕。缓步,将尸块一一对应地置于盔甲之上。如同沉入水面的石块,却不起一丝波纹,好似夜晚一般的安静,进入了盔甲内部,就算盔甲内部是实心钢制人偶似乎也毫无阻碍。一切完毕,黑袍祭祀伸出赤裸地双手进入了盔甲,穿过了水面到达了深处,然后摸索。年老的身体显得吃力,仿若泥浆中的行走,在盔甲内的每一刻都在夺走这位内心坚定者的生命力。红润的面色开始枯槁,借由虚弱的身体将那把纹路奇特的匕首从盔甲的胸口抽出,而匕首的抽出似乎给盔甲留下了痕迹,一个空洞。随着刀身的收窄,空洞中开始逃逸光线,原本只是星星点点,让人以为是错觉,随后愈发耀眼,照亮了周身,照亮了黑袍,接着连同祭祀的肉体、骨骼一同穿透,在拔出的最后一刻,光射向了上方,点亮了那遮蔽了天空无数年的厚厚云层。
怀抱着头盔,立于帐前,凝望远处天空的异相,军团长明白,或许要出事了。仅仅是灯光无法搅动云层,实际上帝国数年来一直在寻找飞上云端的方法,但那云只会使人迷失,而云层不对任何事物作出反应,无论是人、飞行器还是枪械、炮弹甚至心能者的轰击,除了被吞噬别无其它,仿若是神之领域不可侵犯。而望及阵前,则是广袤的塔里他森林。不同于帝国常见低矮灌木,靠近热带的塔里他皆是高大的乔木,将近一半的森林有着超过十人合围的硬质树木,靠着连结整片大地的菌丝供给营养。链锯、炮弹、炸药,这些都没有办法有效地突破,至于身披动力铠甲的帝国战士们而言,树木的间隙都无法让单人快速通过,林间作战更是无稽之谈。绕过森林进攻?这座以国名命名的森林已经说明了问题,对于地处中心的帝国而言,塔里他这个国家几乎包围了帝国一半的疆域,这座森林则是横向的壁垒,犹如一座天然的长城,南至占拜庭,东至依兰斯。对于这两个正在进行宗教转化且态度不明的国家而言,可能的军事行动不仅危险,而且还会受到来自上层的压力。虽然现在脚下踩踏着的已经是塔里他一半的土地,但还是不够。这是一次宗教灭绝战争,更是一次失地收复运动,主要的目的就是森林背后得国都,诞生之地耶鲁斯。当然,对于军队系统而言,只是需要消灭一个对帝国版图成包围态势且拥有足够潜力的国家而已,可若失去了教廷的经济、政治支持,单独的派系绝无可能独自统领一只远征军便发动对塔里他的战争。派系的争斗若发生在一支远征军中,那绝对是让人难受的事情。不过,六个月的僵持让事态正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一名副军团长正在前来视察的路上,理所当然的是一名“不太好说话的家伙”。同样的,虽然靠近热带的天气延缓了寒冬的到来,但帝国早已是深冬,辎重补给渐渐成了问题,因为对方坚壁清野的策略以及开耕时间过晚,导致仅靠在塔里他占领地的抢掠和短期耕种完全无法满足庞大的消耗,所以决战也将要到临了。
拔动匕首时太过用力,也因为身体暂时的虚弱,所以向后倾倒,而光在这时包围了他。祭祀的黑袍被光染得雪白,面前之人似光的实体又似光的阴影,无法用语言形容,因为无形之物又怎么会囊括成有形呢。但,伸出了手,似从无尽庞大之体上延申出的阴影勾勒出了手指,点向自己,于是身躯不再倒下、面容不在苍老、额头的伤痕已然消失,连身体也恢复了力量。奇异而又坚定,就算时间连同祭祀的身体一起停止,导致本就无法动弹,但对健壮身躯的感觉却异常坚固地刻印再感知中。不可理喻!是的,超脱地肉体感知的内容,却结结实实地烙印于凡人,便成了幻觉。然后幻觉的阴影改变了,原本收拢的手指摊开,掌心朝上。讨要,心中地想法出现,而自身却未意识到,无法动弹地手就伸了出去,物归原主,匕首还给了主人。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无法获得任何感觉,也无法知晓自己做了什么,一切只是幻觉,一瞬间的幻觉。所以,在下一个瞬间,所有的幻觉冲击在了祭祀大脑之上,而光已离开,阻止自身倾倒的是身着白袍的狼。
当白袍的手搀扶住黑袍那双重新恢复力量的赤裸手臂时,他明白,那发生了。
呆呆地望着原本应于自己手中的短刃,挂在了那具铠甲之上,它的握柄似乎是亚麻制作的,至少除了刀身以外都被亚麻包裹,所以坚硬而又舒适,末端有一小孔,细小,就算手掌覆于其上摸索也不会有异感。现在,那个空洞中穿过了一根纤细的草绳,用于固定尸骸的那根草绳,似轻扯即断,但依旧牢牢地挂在盔甲的脖颈之上。刀身是直刃,末端的三分之一处开始收紧,整体并不反光,造型上偏向于枪矛,呈现黑紫色,整体长度大致略短于小臂,包括刀刃皆有不明含义的楔形图案浮雕。来回摇晃,似被人拨动,而那个散发光线的空洞也像是从不不存在一样,那么发生了什么?不及细想,那铠甲本身也似乎跟着短刃晃动起来,害怕又是错觉,所以将重心靠在了白袍身上用以恢复身姿,却发现狼双眉皱起,双颚略开,轻眯的双眼紧盯着前方,身体有些绷紧,蓄势待发。与之相反的,看到自己的儿子如此神情,祭祀有些兴奋,立即回转头颅,嘴角扬起,睁大了双眼,它动了,他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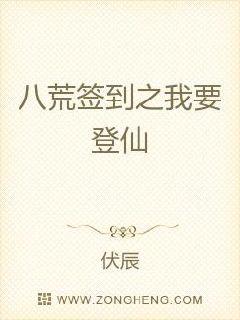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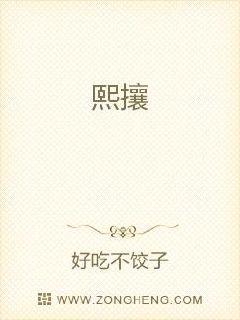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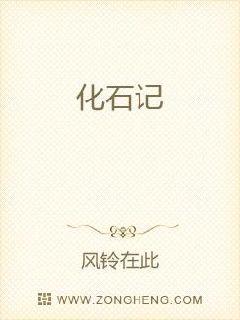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