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尼什维洁
房间里的火炉烧地正旺,维克多利亚则在床上眯着眼,左右翻动,又将被褥掀起,穿好了那件黑长衣。
“啊,那家乎不在。”
他自言自语,挠了挠脑袋,看见爱娜琉斯床上摆着的银色利器,银质的剑鞘实属少见,更别提那剑鞘上镶嵌的宝石...
他走上前,握起长剑,意外的,这把剑极轻,他感觉到的只有剑鞘的重量。
“不错。”
他拔出长剑在阳光下舞了两圈,又将那剑刃顺着阳光斜立,银光照耀,华美至极,细密的纹路在剑身上舒展,最后形成一朵初绽的夏华。
就在这时,门被人推开,维克多利亚匆忙将剑收起,藏在背后,一连串动作迅速而熟练,说实话,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偷偷使用爱娜琉斯的剑了。
“维克多利亚?”爱娜琉斯望着对方奇怪的表情,感到疑惑,“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是的,没什么。”一枚银币从他的手心滑下,几个简单的手势,银币就消失,又出现在爱娜琉斯的身后。
“叮——”
清脆的金属声使爱娜琉斯瞬间警惕,她向前踏出一步,抽出身后的匕首,但却发现身后没有任何人。
长剑归位,没有被发现。
维克多利亚缓了口气,“啊,应该是我夹在门上的银币,防止有什么人进过房间。”他解释,但语气僵硬,除了圣武士外没人会相信。
“是吗。”爱娜琉斯拾起银币,丢给维克多利亚,“大可不必。”
“有防人之心总是好的。”维克多利亚有模有样地说着,拉出椅子,坐在桌旁。
“主叫我们信赖姊妹兄弟。”爱娜琉斯说着,走回床铺,看见随意摆放的长剑皱起了眉,她盯着维克多利亚,刚想说什么,却被他的话打断。
“学士和你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爱娜琉斯回答道,昨夜的事她记忆犹新,“那些赤目怪物...据说是魔女的子嗣。”
“就这些?”
“我从学士那听闻到的就是这些。”爱娜琉斯坐到维克多利亚身旁,为自己倒了一杯清水。
“你有什么收获吗?”她问道。
维克多利亚微妙地笑了笑,最后决定将魔女的事告诉她,“当然,不过还没来及跟你说。”他将自己的杯子装满酒水,推到爱娜琉斯的面前。
“喝完,我就告诉你。”
“不可能。”爱娜琉斯低头,望着酒水里自己的倒影,“不可能。”她重复道。
“那就没辙。”维克多利亚准备伸手拿回酒杯,而爱娜琉斯则按住了它。
她盯着维克多利亚,不知道在想什么。
“记住,我就喝这一杯——圣武士不饮酒,这你是明白的。”
“那就请吧。”维克多利亚将手撤回,托着下巴,在看到圣武士将那杯酒水全部喝干后,他才露出奸计得逞的表情。
“讲吧。”圣武士两颊通红,但并未察觉到有什么异样,她不安地扯了扯衣领,似乎觉得浑身在发热。
她的酒量极差。
“再等一会。”
“不可能!”
“好吧,好吧。”维克多利亚摆摆手,在她的耳边说道:
“我见过村中所谓的魔女了。”
......
村长宣布了威尔的死亡,十几年前的恐怖阴影再次笼罩了整个扎卡叶甫,无形的恐慌在村民中蔓延,那段早已被尘封的传说也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
人们的失去了敬畏,而永恒的冻森带来了惩罚。
不知是谁如此传言,这种说法仅在一上午间就传遍了整个村子,人们眼中美丽富饶的山林也变成了吞人的恶魔与诅咒之地。
无偿给予的自然此时竟对人充满恶意。
就像是十几年前,学士来到此地之前的那样。
在这样微妙的时机,大雪降临了,它隔开了每一个人的联系,令这些渺小的生灵躲回了自己的庇护所,在温暖的炉火前细细品尝久违的恐惧。
昨天死的是克兰,今天死的威尔,那么明天又会是谁?
白昼在不经意间已让位给了夜幕,大雪一刻不停地肆虐着,但比起往夜的谷风来说,它安静地就像是恬淡少女的笑声。
林中,一对白皙的足袭在雪地中踏着,婉转的哀歌在风雪的扰乱下极为模糊,但透过呼啸声的旋律却使人难以忘却。
她是克兰的长女。
或许每个村中都有这样一位,或几位神奇的人物。
尼什维洁,她在一场长达半个月的暴风雪中出生,在她离开母亲温暖的子宫时,灭绝一切生命的风雪奇迹般地停止了它无休止的咆哮,往日里沉默的座狼们纷纷长嚎,像是在庆贺她的降生。
她生来不惧寒冷,这份天赠之礼令她与寒冷为伴,即使是森林吞噬外来者的那种极度严寒也只会使她感到温暖。
但这毕竟与圣武士的祝福不同。
同样的恩赐,不同的目光。
仅凭主之名,圣武士生来便高人一等。
悲乐为谁而奏?
是为威尔,还是她的父亲克兰?亦或是为她自己?
不久,哀歌消失了。
正是四下无人之时,在风声的掩护下,一个声音在低语:威尔——威尔...
威尔的墓被安放在村旁雪岭的最高处,躺在其身旁的便是与他相伴多年的好友,克兰。这个地方从不埋葬死者,学士倒是常来此冥想,祷告。久而久之,像是有主的意志,在岩峰中生出一颗南方特有的黑橡树,树木粗糙的表皮上长着一些神秘的咒文,只有学士能读懂。
作为村中技艺最为精湛的猎人,同时也是人们征服了冻森后的第一批殉难者,学士将它们安置在了这里。
随着大雪,少女来到了这个神圣之地,她缓步走到二人的墓旁,先是对自己的父亲,克兰的墓鞠了躬,又走到威尔的墓前,抚摸着作为简易墓碑的木十字架,动作轻婉柔雅,像是妻子在抚摸自己沉睡丈夫的硬直头发。
她一直在说着什么,但呼啸的风声为她遮掩住了一切,包括她长久以来对威尔的特殊情感。
北境仇视神秘,从它的猎巫传统中就可见一斑。
总有无辜者因此成为人们倾泻恶意的容器。
这位猎人却在众人的谴责与谩骂,鄙夷与凌虐中保护了她,在不远路途遥远,前来施以火刑的牧师前以灵魂发下誓言,撒了弥天大谎。
自此,她成了村中唯一的自由者,当她被威尔带回村子时,所有人不知从何而来的怒火被绝对的权威浇灭。
但人们没有原谅她的罪。
人们只是当她死了,自此,她的名字便成为了任所有人羞辱的符号。
她的父亲,母亲竟然也是如此。
又迎来了几次盛夏,她多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不知受到了怎样的教诲,他们的童真居然在尼什维洁的面前失了色,他们也如村民,如她陌生的父母那样——把没有犯下任何罪的她钉在了耻辱柱上。
她成了与座狼行秽的荡妇,与恶魔畅谈的亵渎者,出卖灵魂给魔鬼的可憎之人。
讽刺的是,这位无罪的不可饶恕者却仍信仰着主,她日日夜夜都进行着祷告,从不忘对着无边际的缄默发出由衷的赞叹,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她无色的世界中的唯一色彩是谁?是那位猎人,威尔。猎人沉默寡言,话语中少有什么情感,但他的善意已胜过这世界上所有人。
如此一来,威尔就是她世界的全部了。
可她的世界死了,这又反而使她想尽一切努力活下去,活着,为威尔死去的灵魂祈祷,直到永远...
即使是仁慈的主也会默许她的复仇,任她的沉默碾碎夺取她世界的罪人,可她应向谁复仇?向整个山林,向这片从她祖父的祖父,甚至主创造人之前时就存在的永恒冻森复仇?令火焰焚烧每一颗冷杉,令无数生灵死于不灭的山火?
火在北境的霜冻中难以燃起,就像她不知从何而来的罪孽无法清洗。
忍受吧!主会公平的判决一切,她的洗罪日迟早会到来。
不知不觉间,午夜已然到来,空中浓厚的雾霭再次消散,月盈星损,空中的亮光又只剩下了那轮满月。
满月是不祥之先兆。
她仰望着皎洁的满月,怀疑起人们口中的各种传说,如此美丽的天象为什么会是不祥的象征?
风向改变了,但少女并未察觉。
她不知道,此时的扎卡叶甫已被先前蒙蔽着满月的雾霭所包围,朦胧间,无数的黑影在其中闪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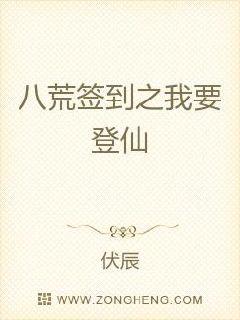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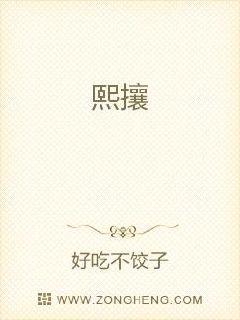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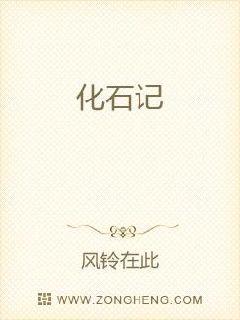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