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正交困
就见文息的神色陡然变化,虽然仅仅一瞬,但在他脸上,却显得十分浓重。
“她写了一份血书,然后就自杀了。”
“她怎么会知道事情原委?”周隐疑惑:“始终好像,都只有公子年,公子勤还有我,知道。”
“不过……我好奇的是,公子为什么要来。”
周隐看着孟欲阑,过了一会儿,抬抬眉毛:“你想做世子对不对?”
就见孟欲阑的神色突然悲伤起来,但不减嘴角的笑意,也不重语气:“我不想。”
“蔚帝还是父王,他们活的都很累,不是吗?”
“可是,公子年与公子勤相争,唯一的黄雀,就是公子。”周隐毫不讳言。
“没错。所以我写信,引你来救他们。”孟欲阑从周隐手里接过画,放到桌子上,拿纸镇抚平。
“我救?”周隐看着孟欲阑。
孟欲阑反而笑笑:“你救。”
一阵风吹过来,刚刚抚平的纸,又飞扬起来。
周隐离开公子阑府,文息就问周隐:“府君相信,鹿温是自杀?”
周隐停了停脚步,然后道:“聪明人不会自己了断自己,会让比自己聪明的人了断自己。”
“……”文息没有说话。
“死无对证,眼下,活人的事更重要。”周隐回头看了一眼文息,阔步向前走去。
大殷殿。一切都如同他离开时那样平静,平静里藏着风云。
孟欲丞站在大殷殿外,看到周隐走过来,就如同飞过来一样,心花怒放的看着周隐:“你回来了,终于来了……”
周隐朝孟欲丞行礼,接着绕过她,往大殷殿里走。
“南恒周氏公子隐,见过孟国公。”周隐掠袍下跪。
孟国公的神色,比月余之前的神色,还要憔悴,或者年迈。
“赐座。”
夕沉弯弯腰,然后朝殿内殿外喊:“赐座——”
周隐坐在案后,看着孟国公。
“公子为什么还要回来?”孟王看着周隐。
“因为此事与我有关。”
“此事与你无关。公子年与公子勤的事发,是拜鹿温所赐。”孟王伸手敲敲自己案牍层楼旁的桌面。
“是我要调查青世子之死,才会牵扯出另外两个公子。”
“但他们不用公子来救,他们还有自己的谋士。”
“然而只要国公想要他们死,他们的谋士也无用,不是吗?”
周隐看着孟王,孟王看着周隐。二者都看不出对方在想什么,却还要看着对方。
因为看不出什么,才要最先发现对方的破绽。
“可我不想让他们死。”孟王摇摇头,率先将眼睛移开,看向自己的桌案。
就这时,夕沉微微欠身,然后朝孟王道:“国公,还是先休息吧。”
周隐随着孟王起身,朝他行了礼,看着他老态龙钟的离开。
夕沉走下台阶,来到周隐面前。
他微微弯了腰,然后朝周隐道:“公子确实不该回来。
公子若不出面,两个公子要么全部贬废,要不全都好好的。但公子出面,就叫前者可能性大了些,并且,此刻两位公子,一定会处决一个。”
周隐看着夕沉:“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夕沉笑笑,道:“不是一定要这样,而是不得不。”夕沉拱拱手,言一句告退,就离开了。
周隐低着头,转过身,往前迈了两步,就看到孟欲丞站在门口。
“怎么样?”她看着周隐,希望得到答案。
“郡主希望是什么样?”周隐看了她一眼,然后往前走。
“我希望,他们都不会死。”孟欲丞道。
周隐冷冷的笑了一声:“你看看前面。”
周隐伸出手,指着前面。
孟欲丞看过去,云雾里,藏着的是鎏余宫的宫阁以及高墙。
“什么?”孟欲丞扭头看向周隐。
周隐道:“你看到什么了?”
“我什么都看不到。”
周隐摇摇头,笑道:“瞎说。你看到了。”
“只有宫墙。”
“你看不到吗?东孟,平荒之上所有的人都不希望别人死。可如今的局势,就关乎他们的生死。”周隐语气苍凉。
“难不成,立个储,还能动荡天下吗?”
“当然。”周隐看着孟欲丞。
孟欲丞看着前面,慢慢皱起眉头:“我不想明白。”
“我不懂你,我真的不懂。”孟欲丞伸手捂住眼睛,摇了摇头,站在原地。
周隐看着她,然后伸出手,把她的手从脸上拿下来,最后收回手:“没关系。”
孟欲丞突然不敢看周隐了,她转过身去,等着周隐自己离开。
“就算是死,也是公子勤遭到厄运,公子年,我会竭力保住。但我还是会全力保住他们。”
“府君打算怎么保?”文息跟在周隐后面,问。
“事情原委都已经知道了,公子年只是传了假令,他可不是最后拿着兵器的。”
文息低低眼睛,回答:“府君想简单了。”
“……”周隐驻足,看着文息。
“设计出血书一局的人,不会让公子年逃脱的。”
“你觉得,谁设计了血书?”周隐皱着眉头,神情愈加肃谨。
“我说是孟欲阑,府君信吗?”
“当然信。我不信你信谁?”周隐果断回答。
文息看着周隐,迟疑一刻,眼神飘向了他身后。
“但是,孟欲阑说他不愿当王。这样做,事与愿违。”
周隐又疑虑起来。
“可是,府君确定,他说的是真的吗?”
“他信道。如若真的要避世,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可他没有避世。”周隐自问自答。
他转过身,看着前面的路。
刚走出去两步,他又扭过头,这次不是看文息,而是看,还在原地站着的孟欲丞。
我不懂你,我真的不懂。
他心里某处的肉被狠狠地揪了一下,她不懂我。
可,谁又懂得谁呢?
周隐再次看向前方,往前走去。
这次到了憩所,果然又一次遇到了詹雏。
詹雏下了辇,在下人引路下,进了周隐的屋子。
“公子。”他拱手行礼。
“詹先生。”
“公子为何还要回来?”詹雏问了和孟王一样的话。
“你竟然问了与孟国公一样的话。”
“因为国公也觉得,你可以撇开这件事。”
周隐回答:“不,我撇不开。一旦哪日我对东孟有用了,此事就会提到桌面上。”
詹雏笑笑,道:“我相信,公子这次回来,是来救我家府君的。”
“……”周隐没有接这句话。
文息看了周隐一眼,然后道:“府君谁也不救,府君只救自己。”
詹雏看了一眼文息,又看向周隐。
周隐想起有些怠慢,就立刻与詹雏入席了。
“其实想要救我家府君并不难,调查星火林的望侯便是,只不过是,不好调查。一旦调查,公子勤必死无疑。”
“可是,公子勤为什么没有动静?”周隐问。
詹雏笑笑:“二位公子都在禁足之中,今日我来,也是废了千辛万苦。”
周隐抿抿嘴唇,看向詹雏:“所以今日,詹先生来此作何?”
“我来,请公子,揭发公子勤。”
就见詹雏合手磕头。稽首之礼,实在之大。
周隐吞了口口水,问:“詹先生果然还是要我去揭发。”
“若不杀伐果断,犹犹豫豫,到最后,谁也活不成。”詹雏抬起头,言正神肃的慷慨道。
“……我只能这么做了吗?”
“不然公子还能做什么?公子那日什么都没看到,需要您做这个假证明,虽然是假的,但也是真的,我家府君,没有参与最后那致命一击。”
“血书里,是这么说的吗?”周隐问。
“血书是夕沉当着百官的面读的,岂会有假?写这个血书的人还真是煞费苦心,要把公子年公子勤一同拉下马。”詹雏看看自己的手心,笑道。
文息抬抬眼睛,没有说话,而是转脸看向门外。门外的风吹起地上的落叶,荡啊荡,像是河上了的涟漪,一层一层荡到她的手边,被她捞起来,往衣服上泼。
周隐会做什么决定?
“周隐。”
他又梦到了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再次从四面八方传来。
“你是谁!”周隐朝前面喊,再次拨开雾,来到榆树下。
没人会回答他。
他刚刚辨别出来,这是个女人。
他看到潭水里已经没有了莲藕,空落落的什么也没有。
他看向树上的布条,上面只有一个“易”字。
“周隐。”他转过身,他害怕再次醒过来,就慢慢转过身,却没有看到人。
他看到一把扇子,扇子上画着棵墨色的榆树,角下绣着署名,隐约看见一个“然”字。
他再次醒了过来。
这已经是清晨,他要找个合适的时间,去鎏余宫。
“我到底,该不该这么做?”
文息站在周隐身后,周隐站在屋门口的廊子上。
“那要看值不值。”
周隐无奈的摇摇头,苦笑:“可惜,我就是不知道,值不值。”
“做了就知道了。”
周隐看着文息,笑笑:“对啊,做了就知道了。”他背着手,仰头看着淡蓝色的,透着愁苦的天。
“我要你去一趟净间观。”
当知天命,何为天命。
周隐行礼后,坐到孟王赐的座位上。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孟王道。
“星猎那日,没有公子年参与。”
孟王倏地抬起头,看着周隐。下一瞬,就见孟王突然一拍桌案,站起身。
四下婢子奴才都跪了下来,周隐也立刻来到案侧跪下叩首。
“你……”孟王气的胡子都在颤,他伸出的手指也在颤,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几乎要把肋骨抖出来。
“国公玉体要紧啊!”夕沉哀哀劝道。
周隐抬起头,拱手朝孟王:“正如国公心中所想。握着屠刀,朝青世子砍下的,正是公子勤。公子年,当时已经出了星火林了。”
孟王突然倾塌在座位上。那个困住他半生的座位。
“寡人知道。”孟王伸出手来,覆在脸上。
周隐深深地叹口气,然后道:“难不成,国公有两全之策?”
“寡人,本可以,佯装搜查,按在鹿温头上一个诬告。烧了她的尸骨就算了。”孟王慢慢抬起头,自嘲的笑笑:“果然,假象胜不过事实。”
周隐抬起眼睛:“烧了鹿温的尸骨?”
周隐突然站起身:“难不成,为了掩盖真相,可以这对待一个这样的死人吗?”
“她只是个奴,老天会保佑她,眷恋她救了两个公子而让她飞仙。”孟王站起身,看着越礼而站的周隐,慢慢皱起眉头。
“可如今,你就算证明了公子年的清白,鹿温的尸体还是要烧。她怎么都有诬告罪。”
周隐握紧了拳头,站在那里,如同脚上粘了面糊一样。
殿外突然刮起骤风,却只一阵儿,就过去了。
孟王看看天色,冷冷一笑:“这就是神的震怒吗?不过如此。我还以为,神要比人强多少。”
“国公一定要烧了鹿温吗?”
“不是寡人一个人烧的她,不是吗,公子隐。”
鹿温对周隐而言,似乎算是教给了他一些东西。
类似于生而为人的担当。以及身体里有神的血液而产生的使命。
还有,如何不恐惧真相。
“这就是真相。你要刨根问底,你还要马不停蹄的来到东孟。公子隐,你还只是个公子,寡人确实曾经赏识你。不过看到你方才那样的怒火,乃至你犹犹豫豫问寡人,会不会让公子年活着的时候,寡人肯定了夕沉的说法。周隐,可能还不如你的陪读。”
周隐往前一跬,然后道:“我周隐是不如人,但我问心无愧,念什么经做什么佛,小爷我,从来不怕。”
周隐挥挥衣袖,行辞礼后,转身离去。
夕沉看着周隐的背影,朝孟王道:“国公,老奴能否收回看好文息那句话?”
孟王看了夕沉一眼,然后冷笑一声:“越是一只留不住的狼,越要叫他知道自己多没用,以免,为他人所用。”
周隐离开了鎏余宫,与文息回到了憩所,就看到孟欲丞在那里等他。
“周隐……”
“我要离开了。”周隐没有看她。
“这么快吗?”孟欲丞问。
“对。我还答应别人了事要完成。”
“哪个人?”
周隐看向孟欲丞,他没有说是谁,而是说,那件事他也想弄明白。
孟欲丞笑笑,看着渐渐低沉下来的暮色,道:“真是奇怪,你明明是早上走的,为什么回来时,天就要黑了?”
“这不是夜色,是云色。”周隐抬头看了看。
文息拱拱手,朝周隐道:“这不是云色,是府君的心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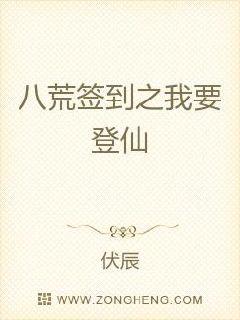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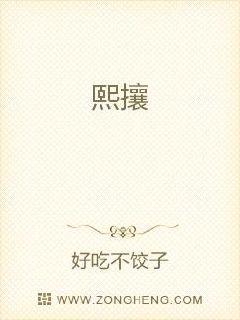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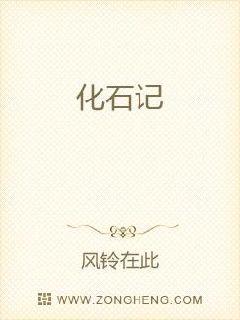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