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祭月之末
天咫城并没有什么四季的区分,一层不显眼的湖蓝色结界将整座城市笼罩在内。其外是冰风、暴雪、极冻与严寒,其内虽称不上鸟语花香的桃园奇景,但至少是一片风平浪静。偏居一隅的孤城,如同独自追寻终点的旅人,世世代代的虔诚守望着。
主塔楼是城堡区最显眼的建筑,甚至比圆顶塔楼上的瞭望塔还要高出几分。它粗壮结实,身形工整,瓦片上闪着熠熠的青光,活像个膀大腰圆的将军。
景玄的家就在这里。
从孤夜原带着他的妻子薇拉回到圣狩山的那天开始,主塔楼就易了主。
老族长带着本家四十多人迁去了圆顶塔楼,把诺大的主楼留给了这对夫妻和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修川。
按理说他们一家与老族长这一脉血缘疏远,本来并不应该受到如此优待,但镇压魂狩的重任艰巨,孤夜原的力量不可或缺,为了留住生性散漫的“东方御灵神王”,族长自然心甘情愿的将这处宝地慷慨相送。
此时景玄正躺在床上,他虚弱的只能把眼睛睁开一小条缝,但视线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真切。他继承了王歌家族典型的白皮肤和碧蓝如汪洋的眸子,与修川不同,他的发丝漆黑如墨,此时陷在枕塌之中活像是一摊海草缠在头顶。
余伯和先前的枯瘦老者站在窗前,压低声音谈论着什么。
“孤夜原这一走,圣狩山立刻就变成七大镇守中最弱的一环,不但我们镇压的那只凶兽在封印下蠢蠢欲动,连霜月森林里的小鱼虾米都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奥斯忒人昨天就询问过关于封印的事,他们也察觉到了不对。”
“预言师们总是未卜先知,这不奇怪。我好奇的是,孤夜原为什么要走?”
“谁也不知道,没人拦得住他。”
“可为什么选这个时间,稍晚半天就能赶上景玄的启灵日。”
“恐怕是故意挑的日子,只为了……”
景玄听到了父亲的名字,因而努力的想要捕捉到更多内容,但他太虚弱了,甚至连窗边两人的身形都看不清晰,更不用提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一道瘦小的身影朝他走了过来,直到那人走到床前,他才认出那张爬满皱纹的脸。
“海觉大人,我……”景玄气若游丝,发出的声音几乎自己都听不清楚。
海觉轻柔地扶住景玄肩膀不让他起身,平静而又不容置疑地说:“你受了些轻伤,现在正需要好好歇息,幸好修川的灵压没能震动你体内封印,要是灵力外泄,恐怕启灵仪式都会出问题。躺着,我和余伯守在门外,等时间差不多,就带你去祭坛。”
景玄迟钝地点头,他觉得脑袋一阵昏沉,转头看见余伯也面带微笑走了过来。
他清楚若不是余伯找来了海觉先生,自己今天恐怕还要伤的更重一些。修川与他如此为难也并不是一次两次,只是以灵力来强行碾压他还是头一回,恐怕这与父亲不告而别也有些关系。
房间内再没有什么声响,两位老人退了出去,空荡的厅内只留下思绪辗转盘旋着。
你终于还是走了。景玄默默的想,他原本以为自己的心应该像四周冷清的空气一样毫无波澜,但不知道为什么,一股挥之不去的缺失感总是萦绕心头。直至今日,那个与自己血脉相承的男人从不曾像一个父亲一样给过他哪怕一丝温暖,塔楼里的管家与附庸抚育他长大,而那个人却连一个对话的机会都吝啬赐予。
为什么会流泪?景玄闭上眼睛迷茫的摇头,眼泪像山间的溪流汩汩淌下,润湿了脸。
午后的阳光不错,把阴影驱赶的无处可藏,但极北的白昼终究还是带不走瘆人的寒冷。
主塔楼的走廊内大多没有窗户,精致的装潢和明亮的灯火让这里没有阴森可怖的感觉,即便如此,余伯依然觉得这地方有些不近人情的厚重庄严。
学生在屋内小憩,他和海觉就在门口轻声聊了起来。启灵仪式会在太阳落山之时召开,他要小心不能让景玄错过了正事。
海觉是家族里辈分崇高的老人,他亲近老族长一脉,算是族长的表弟。四百多年前他下山历练认识了余伯,两个人的交情已经持续了大半辈子。
余伯是魂锁道的大师,但在伏灵修炼一途上没什么天赋,能活到这把年纪全靠着王歌家族的秘术维持。四百年过去,两人早已不是初遇时的翩翩少年,摇身一变都成了时日无多的迟暮老人。
人越老,越感觉到时间匆忙。余伯眼看着自己眉心的神力印记一天天黯淡下去,心里只想着能把自己对魂锁道的钻研传授给唯一的学生。家族规定不允许孩童在启灵前接触任何灵术,因此直到今天他才能教授一点点最基础的东西。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余伯心里有些无奈。
看着老朋友神色黯然,海觉正想发问之时,景玄已从屋内推门出来。
“这才半柱香,休息的怎么样?”余伯有些心疼,这孩子正在天真烂漫的年纪,却不得不受骨肉疏离的痛苦。想来这一家人都命途多舛,景玄的太爷爷因窥探封印阵被逐出家族,致两代人颠沛流离,父亲孤夜原被传召回来不过四年,又经历丧妻之痛。余伯常看见景玄微笑着回应塔楼里那些侍从,却总觉得有一丝愁绪藏在那幅平和的表情之下。
“谢谢余伯,我已经没什么事了,海觉大人,今天要不是你在,我……”
“假客气!”海觉抿了抿嘴,佯怒道:“这时间还早,你不好好歇息,急着起来蹦跶什么?修川小子还没把你收拾够?”
景玄的脸色还是那种不自然的苍白,虽说行走已经无碍,但虚弱的样子旁人一目了然。“大人,我想去祭月之末看看。”
祭月之末,世界的顶端,景玄的母亲薇拉的葬地。
那年今日,孤夜原将绝景峰一分为二,磅礴灵力将半座大山揉塑成一座矗立在绝巅的高塔,取名祭月之末。
塔顶,美艳却苍白的女人安眠在森寒的冰棺里,笑容温婉。这一处离月亮最近,她生前最爱这样的地方。
塔身上刻印着薇拉的灵络,从她纤细的身体一直延续到底端。这些灵络金光流动,时明时暗,像是棺椁里一颗种子生出的根。
可惜她终究已经去了,再美的景色也于事无补。如果自己没有出生,如果那个男人没有在母亲分娩之时离奇失踪,如果家族敢于去揭开重生的禁忌,一切或许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他无数次的幻想过自己出生的那个夜晚,雷电轰鸣着袭击死气沉沉的城堡,暴雨和怒风在黑夜里肆意妄为,母亲孤单的躺在床上,无助地看着面无表情的侍女,顺着死神的轻唤缓缓地坠下眼皮。
他不记得她的容貌,没有听过她的声音,也不曾在她的怀抱里安睡过,但他感谢她所做的一切,她把他带到了世界上,这是最美好的事情。孩子对母亲的爱意,总比星空还浩瀚深沉。
听到祭月之末这个名字,余伯和海觉面面相觑,那是禁地,除了孤夜原的家人,没人能突破重重禁制前往那里,谁也不愿意触动孤夜原的逆鳞,东方御灵神王的名号在他们耳朵里,可比孤夜原这个名字要响亮的多。
景玄很顺利地说服两位老人不要跟随,母亲的忌日,儿子扫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不懂两位长辈眼神中的忌惮,但在向他们保证一定能够赶在启灵仪式开始前回到祭坛之后,他们都放心许多。
从城内到祭月之末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事实上,只要是在城市的结界之外,每向上迈出一步,都是对死神无声的挑衅。
每一次去探望母亲对景玄来说都是一次历练,他没有灵力傍身,只能依靠肉体去抵御风雪。圣狩山脉是北方高峰聚集的险地,绝景峰更是其中首屈一指的巨人,山坡上的积雪深厚处,直能没过景玄的头顶。
他在小径上辗转腾挪,完全不像一个十四岁的孩童。狂风在耳边呜咽,咆哮着叫嚣着仿佛要撕碎一切,景玄渐渐感到吃力,他毕竟有伤在身,不像平常那样灵动迅捷,但此刻时间紧急,心情也迫切,容不得他稍微歇息,因而即使疲劳侵袭,他的速度也丝毫未减。
景玄攀登的这条小径藏身于绝景峰最平缓的西南坡,山体挡住了自北而来的寒风,相比而言环境可以说是温和。小路上灰白的石阶整齐排列,刀凿斧刻的痕迹班班可考,显然是前人造就而非天然形成,他从小就自这里上下,对登山的技巧早已得心应手。
然而登顶绝非如此简单。
早在景玄五六岁时,登山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孤夜原在一个没有阳光的下午把他带到这里,指着隐没在云层中的峰顶只说了三个字,“爬上去”。然后接下来的四天,直到景玄筋疲力尽的倒在路边,孤独的攀爬都没有停止过。
纵然这条小路绕过了杀机四伏的冰川、冰凌、岩隙和暗缝,纵然笼罩其上的结界抵御了风雪、保留了氧气,甚至连积雪反射的炫目阳光都过滤在外。但对一个瘦弱的孩子来说,这样的高度依然是不能逾越的天堑。
随着景玄一天天长大,他逐渐成熟的身体也变得坚强起来,而那条路也像是有生命一般,从风平浪静变到波涛汹涌。他数次陷入惊心动魄的险境,每一次都有新的挑战让他不得不全力以赴。
景玄迈过最后几级台阶,双腿杵在原地不住地颤抖,他双手轻轻交叠在胸口,强迫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努力的去汲取山顶稀薄的空气。
一切都很熟悉,群山蜷卧白雪之下,云是一层轻薄的纱。一眼望去,千里内险峰与深渊交织纵横,冰川与岩壁决绝挺立。生命的律动偃旗息鼓,不敢偷偷发出一点声响。
高塔近在咫尺,顶端却依然隐没于一片深蓝之中。清晰的纹路遍布整个塔身,间或有金色光芒在纹路之间浮现,从塔底一直向上蔓延。金辉爬满了灰蓝色的塔身,冰霜之灵肆意涌动,涤荡出阵阵彻骨的寒意。
景玄缓步上前,轻轻地碰一下,他想。
他伸手触摸塔壁,像是爱抚一只惊慌的宠物一样小心翼翼,等指尖与闪着金光的灵络接触的那一刹那,一股怪异的挤压感瞬间将他包围了起来。
身体仿佛融化成软糯的糖浆,在密实的管道里艰难蠕动。景玄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化成了五色流光,飞速的在自己脑海里来回穿梭着,而下一秒,一种被重击后脑的感觉又把他从梦境中驱赶出来。
转眼便已到达顶端。
恍然之间,深蓝的塔顶平台替代群山充填了视野,北方雪雾中的汪洋冲击着圣狩山脉连绵不绝的岩壁,凌空的太阳也被半透明的屏障遮挡着不那么耀眼。
虽然很小的时候景玄就已经见识过塔身上所贮藏的灵术,但突然的移形换影还是让他一阵的头昏脑涨。自己也马上可以掌握这样的术了吧,景玄微皱眉头,想到余伯的教导,细微处还是有些疑惑。
他知道灵络是人们用来感知、控制灵子的器官。就如同人的面貌性格一样,每个人灵络的形状都迥然相异。它们大多数都是像蛛网一样复杂但有序的纹路,密集的分布在人体内每一个角落,也有极少数人的灵络集中在几个特殊的位置,比如预言家奥斯忒人的灵络几乎全部生长在眼睛与大脑周围。
灵络再造术也是景玄从父亲的藏书中认知到的一个词汇,大致就是一种通过刻画出灵络灭亡前的形状来还原其本来活力的技术。景玄当然搞不懂那些复杂的仪式和繁琐的咒语,但想必这就是父亲眼里唯一一抹还没有褪色的光芒。
景玄面对着瀚海汪洋呆立了几秒,紧接着回头向南走去。祭月之末的塔顶是一座棺形露天平台,四周没有护栏,边界之外就是滚滚的云层和遥远的山脉。这里的灵络更为细密多变,全部汇集到平台南边冰霜凝结而成的灵柩中。一个模糊的身影在冰晶下安睡,和煦的笑颜仿佛即刻能融化万年冰川。
“妈。”景玄也笑了,他轻轻地呼唤,脸上的神采与沉默不语的母亲别无二致。他静静的坐在冰棺旁,伸手想去触摸一下母亲温婉的脸颊,但坚冰隔绝了体温,任何努力都徒劳无功。景玄早已习惯了被棺椁拒绝,他缩回手,把头埋进膝间,低声讲起了半个月来发生的一切。
太阳走到了西头,景玄轻轻的吟语被吹散在了风里,寒冷来袭,只有薇拉安静的微笑是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唯一的慰藉。
如果你还在,这个家会不会好一点,他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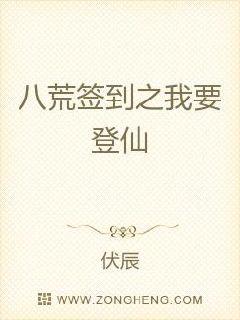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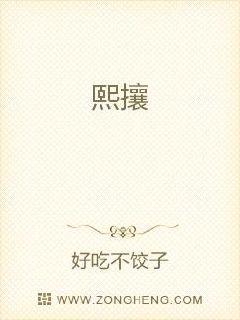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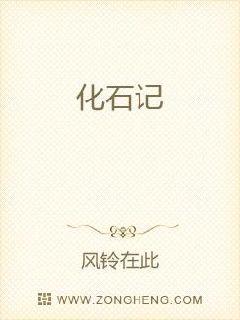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