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王树挨打
王树得到儿子被抓挨打的消息,已经是第二天晌午时分了。他心急火燎地戴上斗笠,扛起一把锄头,抓了几个玉米窝头掖在怀里,就顶着烈日出门了。三兄弟昨天晚上格外兴奋,没吃什么东西,再加上又挨了打,一定已饿得四肢无力,头昏眼花。
王树有些心痛。
王树虽然瘸了一条腿,路却不禁走,一盏茶的功夫,他就已经站在张有亮家的大门外了。
张有亮家的大门镶铜包银,铁环铜兽,看上去十分气派,有点像古书里说的候门深似海。王树放下肩上扛着的锄头,像锄地一样,往手心里吐了泡口水,踮起脚尖,铿铿地拉响了门环,尖着嗓子大喊:“开门,开门啦!有人吗?”
阳光把王树的影子投射在墙上,很夸张,薄如蝉翼。他的影子被墙角折叠了一下,然后,又匍匐在另一面墙上。左看右看,横看竖看,就像皮影戏里的皮影,把王树拉动门环的动作模仿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
过了很久,镶铜包银的大门轧轧一响,裂开了一条缝,两个守门的僮仆牵着一条狗,耀武扬威地走了出来。
其中一个在王树面前站住,白眼一翻,恶狠狠地说:“哪里来的莽汉在这里撒野?你瞎眼了吗?今天府上有事,概不见客。滚!”他指了指墙上贴出的告示。
另一个僮仆手一松,牵在手上的恶犬腾空而起,把铁链子挣得哗哗响,绷得笔笔直。
王树倒退了一步,扬了扬手上的锄头,说:“我找我的三个儿子,他们犯了什么王法?让你们拘在府里严刑拷打?你们还讲不讲道理?”
“哟!仙童、人精、地煞那三个坏瓜是你的种,看不出,看不出!他们勾引良家妇女,毀人清誉,可以关一万年,死一万次!你还好意思说?”
“什么勾引良家妇女?他们那是两情相悦,自由恋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关你屁事?”
“两情相悦?自由恋爱?你也不撒一泡尿自己照照,你那三个儿子是些什么货色?关着是命,打死活该!”
“你们就有理了?私设公堂,草菅人命,我要到郡守那里去告你们。我就不信,世上没有王法?张有亮能一手遮天?”王树拍着巴掌,上蹿下跳。揣在怀里的玉米窝头骨碌碌地滚了一地,僮仆手里牵着的狗两眼放光,一口一个吃得干干净。本来是想给儿子垫补、垫补,却便宜了这个畜生。
“滚!大小姐割腕自杀,老爷心里烦得很,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小心挨揍!”一个僮仆恨恨地瞪了王树一眼,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院子,轧轧地关上了大门。
“我偏不滚!不放出我儿子,我决不会罢休!”王树重重地一跺脚,趋前一步,铿铿地拉响了门环,一声比一声急,一声比一声响。
可大门一直紧闭,根本没有开的意思,就像一个哑巴,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开口说话。王树急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操起地上的锄头,对准门环,吭哧吭哧地砸了下去,一下,二下,三下,木门上砸出了一个斗大的深坑,就像老汉缺了的门牙。
府里的狗汪汪地叫个不停,急促的脚步声响成了一片。大门吱呀一声开了,一群黑衣人在一个管家的带领下,拖枪拽棒,鱼贯而出,把王树围得水泄不通。
管家倒剪住双手,绕着王树兜了一个圈子,指了指大门上的凹坑,说:“老汉,门上的坑是你砸的?你有种!你这是打狗欺主,私闯民宅,无法无天!”
“你们不明不白抓了我的三个儿子,不放,我还要砸,一直砸到你们放了为止!”王树脖子一昂,毫不畏惧。
“你敢,你再砸一个试试!”
王树轻蔑地看了管家一眼,捡起了地上的锄头,一瘸一瘸地走到大门前,双手举起,奋力砸了下去。
管家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大喊:“打,给老子往死里打!我这是为民除害!”
王树左遮右挡,拳脚、棍棒雨点般地落了下来,一眨眼的功夫,王树就成了一个血人。
可谁也没有想到,王树还会从血泊中爬起来,挣起身子,口齿不清地大喊:“兔崽子们,你们打吧!不打死老子,老子明天还会来砸门。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牛皮糖?什么叫炖不烂的老牛筋?”
囚室里有些闷热,散发出一股霉腐的味道,成群结队的蚂蚁来来往往,不停地往窠巢里搬运着粮食。
张府原本没有专门的囚室,囚室是张有亮用来贮酒的酒窖,或者说,他腾出了四间酒窖中的一间做了囚室。张有亮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喜欢收藏各种名酒。他的酒窖里陈列着用橡木桶贮存的各式名酒,甚至包括法国波尔多庄园的顶级拉菲。
酒是岁月酿造出的精华,液态的精神存在,综合了历史、地理、季节、阳光、情欲等诸多元素,西方人叫忘魂汤,东方人称猫尿。男人靠它麻醉自己,女人因之堕落。
仙童、人精、地煞嗅着酒香,枕着双手,横七竖八上也躺在稻草堆上,头像喝醉了酒一样晕晕乎乎,记忆里殷红一片,全是苔丝从血管里喷出的鲜血!
苔丝割腕后,张有亮自顾不暇,妮可、艾米莉趁乱把仙童、人精、地煞从刑具上解救下来,弄进了这间囚室。混乱中,黑暗里,仙童、人精、地煞全神贯注,听见满院子的人都在奔跑,惊叫着给苔丝止血。
幸亏苔丝有母亲查曼,她随身携带着一种丹丸,叫九转还魂丹。查曼随手取出几颗,用温水慢慢化开,一手外敷一半内服,百病消散,九转还魂,是波斯人的不传之秘。
受了苔丝割腕的刺激,查曼的态度有了鲜明变化。她坚决拥护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是各人自已的造化。可张有亮仍然主张包办女儿的婚姻,要给她们创造所谓的幸福,口气却软了下来,明显的理屈词穷。这样一来,对仙童、人精、地煞的死活,他也懒得去过问。
仙童、人精、地煞关在酒窖里,妮可、艾米莉一共来看过三次。一次是送九转还魂丹,一次是送吃喝,一次是来通知王树挨了打。
九转还魂丹是一种神奇的圣药,由鹿茸、柴胡、麝香、虫草、藏红花等十几种名贵中药熬制而成,精华荟萃,异香扑鼻。敷在患处凉丝丝、热烘烘的,有一股暖流冉冉地从涌泉穴升起,直贯丹田。
至于吃喝,妮可、艾米莉吃惯了米饭拌羊肉,自认为羊肉是世界上最佳的美味,给哥仨送来了一腿熟羊肉和一把切肉的弯刀。
有肉不可无酒。妮可、艾米莉精灵古怪,支开守酒窖的小厮,顺手拿来了两瓶顶级的拉菲。兄弟仨吃着熟羊肉,喝着红酒,再佐以美色,真恨不得张有亮一辈子把他们关在这里。
第三次来,妮可、艾米莉神色慌张,支支吾吾,在哥仁的反复追问之下,才吞吞吐吐地说,王树把大门砸了个透明窟窿,被护院的家丁打了,伤得不轻。哥仨满脸愁容,六神无主。不难怪,刚才院子里闹哄哄的,人喊马嘶,原来打的是父亲王树。
命运是一个天才的编剧。高兴了,会巧妙运用时间、地点、人物这几大要素,把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编排在一起,创造出奇迹;不高兴了,会把时间、地点、人物出场的顺序全盘打乱,制造祸端,颠覆一切。
树影幢幢,新月如钩,茅草屋里一片安宁。抑或是为了打破这种安宁,山谷里传来了阵阵猫头鹰的叫声。月光下,王树慢慢地睁开眼睛,抬起头,病恹恹地咳出了几口鲜血。
仙童、人精、地煞立马围了上来,端茶的端茶,捶背的捶背。王树欣慰地笑了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瞳孔里泌出了两滴泪水。泪水晶莹,明亮,就像两颗挂在草尖上的露珠。
毕竟是行将就木的人,哪里经得住年轻人的棍棒和拳脚?王树伸出一只长满老茧的手,摩了摩哥仨的头,满脸慈蔼。
仙童、人精、地煞忍不住哭了起来。王树咳了咳,歉意地笑着说:“孩子们,别哭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们长大了,我也活够了。有一个秘密传了二十七代,憋在我心里也经几十年了,不吐不安,不吐不快!”
“嗯,嗯!”哥仨看了看王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孩子们,王质遇仙的传说你们听说过吗?”哥仨摇了摇头。王树笑了笑,接着又说:“算起来,我们都是樵夫王质的后代。王质是西晋人,家居浙江衢州,一辈子以砍樵为业。一天中午,烈日炎炎,王质进山砍柴,耐不住酷热,走进一个山洞避暑。想不到山洞别有洞天,内有石桌、石椅、石凳,两个和尚正在下棋。一个挎酒葫芦,一个摇破蒲扇;一个疯疯癫癫,一个满头癞痢。
疯和尚执白先下了一子,嘻嘻哈哈拍了拍手,说:‘癞头僧,你个臭棋篓子,下完这一局,我就不失陪了,我得马上赶到傲来国升仙岭,度书生张嵘、乞丐麻五、屠户李旦羽化成仙,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灵药你带了吗?’癞头僧摇摇破蒲扇。
‘带了,带了。’疯和尚晃了晃手上的酒葫芦。‘不带也不要紧,反正岭上藤子多的是!’
‘诀呢?熟了吗?’癞头僧又问了一句。
‘熟了,熟了。在心里!’疯和尚响亮地拍了拍胸脯。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质躲在暗处,听得一字不差,真真切切,动了寻找圣药、羽化升仙的念头。王质柴也不砍了,带着这个天大的秘密下了山。才知道,父母已经去世多年,手上的斧头柄都烂了,斧子也生了锈,当地人因此把王质砍柴遇仙的山叫做烂柯山。”
说到这里,王树长长地吐了口气,如释重负。歇了歇,接着又说:“祖先王质的这个秘密,传到我已经整整二十七代了。我从七岁起,跟着父亲东渡扶桑,在扶桑找了二十七年。二十四年那年,我又不远万里,飘洋过海,找到了东胜神州傲来国,一找就是整整五十年。在紫云谷,我终于、终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是关于圣药的。”
王树压低了声音,脸色越来越苍白,声音越来越细。他低下头,咳出了几口鲜血,本能地张开嘴,可怜的呼吸就像呼呼拉动的风箱,又粗又浊。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王树伸出一只手,像捞救命的稻草一样,在空中捞了捞,却什么也没有捞到。仙童见状,赶紧伸出自己的手,让王树牢牢抓住。王树抓到救命的稻草,呼吸渐渐平稳,脸色也开始由白转红。
哥仨终于松一口气。
“仙童、人精、地煞,你们哥仨听着。”王树的声音有些沙哑,显然气力不足。“我经过千百次的试验,终于发现了龙须藤的秘密。龙须藤也叫血藤,截取下来,可以分泌出一股像血一样的红红汁液。喝了,凡人会身体变轻,精神饱满,肋下生风,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我琢磨,这种汁液就是传说中升仙的圣药,疯和尚葫芦里装的那种。”
“爹,那您还等什么?喝嘛!喝了它,伤也好了,仙也成了,岂不美哉?”地煞无限憧憬。
“傻孩子,我不行了,升仙得有兰心蕙质。”王树摇了摇头。“我都八十多岁的人了,寿限已到,人都有一死,这是自然规律。”
“怎么不行?您一直把它当茶喝,一直喝到升仙为止。”人精紧紧抓住王树的手。
“做人嘛,不能太贪。我一个废人,喝了圣药,没有升仙诀,也是白搭!”王树叹了口气,接着又说:“你们哥仨就不同了,你们是龙须藤结下的果,采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天生有仙根,禀赋又异于常人。”
“爹,那我们到哪里去找升仙诀呢?”仙童紧紧追问。
“人海茫茫,天地之大,也许很远,也许很近。”王树双目炯炯,语带机锋。“我敢断定,我们在找升仙诀,而升仙诀的主人也在寻找我们,只是尘俗难脱,机缘未到。”
“爹,找到升仙诀,您就可以不死了,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再也不用分开。”人精眼睛一亮,来了兴趣。
“是的。”王树点了点头,泪光闪闪。“找到它,我们就可以脱离六道,超身世外,长生不老,不堕轮回。”
“那还等什么?找啊!”地煞一拍大腿,仙童、人精也大声响应。
“孩子们,十三年了,我就在等着你们这一句!你们都给我跪下,仔细听着。”王树伸出一只手,在秕谷枕头下摸了摸,掏出一个黄布包袱,像说相声抖包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开,赫然竟是一把斧头和两块只有半边的虎符。接着说:“从晋时王质遇仙开始,这把斧头传到我,已经是二十七代了。现在,我正式传给你们。仙童,你是哥,你接着,你要带头发誓,这一辈子都要锲而不舍、世世代代地传下去,哪怕是飘洋过海、上天入地?一直要找到圣药和升仙诀为止。当然,你们并不是孤军奋战,你们还有两个生于扶桑的兄弟,一个叫王安,在聚德郡当捕头;一个叫王超,在宫里做侍卫,这两块半边虎符就是你们接头的信物。看来,天不佑我啊!孟亚,你等等我,老夫来也!”
仙童、人精、地煞万万没有想到,王树的伤势根本没有好转,而是回光返照。王树交代完后事,开心地笑了笑。接着,瞳孔放大,脸色呆滞,攥着虎符的手一点一点地松开,五根指头就像五瓣萎谢的菊花。
仙童、人精、地煞抱头痛哭。
人,堕入人道,立于尘世,就得折腾,就得接受命运的考验。命运有时像个顽皮的孩子,会无端地捉弄你,来几个荒唐的恶作剧;有时呢?它又会像一把锋利的锯,来来回回,无休无止,撕毁你的肉体,锯噬你的灵魂。它的残酷,只有遭受过的人才知道,就像鞋不合脚?婚姻幸不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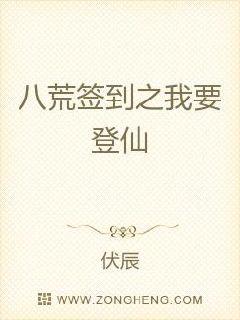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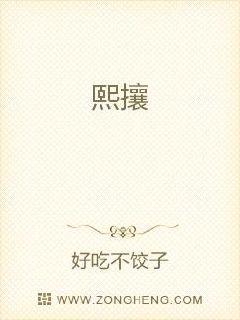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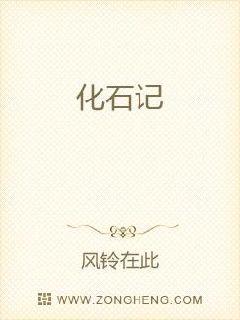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