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立场
他一言不发,却已经暗中篡改了结局。
——首语
等到白孤踏进卧室的时候,玄君阳刚好将手中最后一摞整理好的资料放在了他的桌子上。
“怎么了?”当发现玄君阳站在自己的桌前,非常细心地将一本《理想国》压在自己的手稿上时,白孤发出了疑问。玄君阳对他所研究的哲学是不怎么喜欢的,他认为那是懦弱者麻痹自己、企图将世人都拉低到自己水准的荼毒言论。
对于这个,白孤倒也不在意。这就是玄君阳讨厌他的地方,他不像玄君阳一样高傲而计较。
“哦,”玄君阳回头看了一眼白孤,但他的眼神明显有些畏缩和飘忽,只是在明暗不定的灯光下没有被白孤察觉到,“那个……刚刚刮起一阵大风,把你的手稿和书都吹飞了,我帮你整理一下。”
“没关系的,本来那些手稿也没有固定的顺序。”说着,白孤走到了沙发边坐下来,跟在白孤身后的简·格雷也一同坐了下来。
看见简又回来,玄君阳问道:“你又回来干什么?没看到都很晚了。”
“你看!”简抱起双臂向白孤埋怨起来,“我就说他没事儿吧!说话这么难听!”
说完,她看向玄君阳,好像故意激他一样大声嚷道:“我今晚不走了!”
玄君阳冷笑了一声:“你是走是留,我本就说了不算。你跟我嚷嚷又有什么用。”
说完,他走到白孤与简的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三人一时都没有说话。气氛忽然变得很微妙,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压着他们起身不得,亦开口不能,只得像三具雕像一样冷在那里,任谁都无法打破这样的局面。
睁着大眼睛的雕塑压在合上的《未识之神》译本上,孤独而寂寞地坐在白孤与玄君阳之间,那模样好像是在抉择该投向哪一边。
还没有完全关严的窗户因为一阵微风拂过而极其缓慢地打开了一下,发出非常难听的“嘎吱”声。
再没有人说话,只怕一呼一吸都会变得难熬。
“白孤,”终于,还是玄君阳先打破了这毫无征兆却挥之不去的尴尬气氛,“我问你,为救一人而死两人,可否?”
“嗯?”白孤挑了挑眉毛,他很好奇玄君阳为何忽然问这样的问题,但现在三人所坐的位置令他觉得有些不自在。好像玄君阳此刻是在问他“牺牲你和简来让我活命,你愿意吗”一样。
“你们在说……什么……”简·格雷见玄君阳忽然说起中文,本想大声表示抗议,可是当她看到白孤略有错愕的神情时,声音却不自觉地变小了许多。
“我说,死两人而救一人,可否?”
白孤挠了挠头,坚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可。”
“那死两人而救一神,可否?”
白孤仍然摇头:“不可。”
玄君阳的脸色阴沉下来,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追问。
“为何不可?难道神都不如两个凡人重要么?”
白孤低下头,他觉得玄君阳的眼神有些锐利,令他感到不适:“我觉得,莫说两个人,一个人都不行。”
“为什么?”
“性命不是附加在上面的价值决定的,”白孤摇了摇头,他不想用自己的学识来给玄君阳解释,他只想用自己的标准来回答玄君阳,“在我眼里,性命就是性命,就算是神明也没有拿人命来交换的理由。”
玄君阳摸了摸下巴:“那白孤,你每天吃的那些鸡鸭鱼,它们的性命不是性命么?你每日吃它们,有想过珍惜它们的性命么?”
白孤摇了摇头:“我确实不曾珍惜过它们的性命。如果你想说人之于神,不过鸡鸭于人,我无话可说。但我所在的只是我的立场、人的立场,我也只能为我的立场而发言而已。毕竟“道理”极少与“现实”相重合,所以我也不能违背事物本身的模样。”
简在旁边听着,却根本听不懂他们俩在说些什么。只是从二人的神情上来看,白孤似乎在严肃地阐述着什么。
“我吃鸡鸭,鸡鸭可以反抗。只是它们失败了,所以要任人宰割。所以,当神明非要以人的血肉为食的时候,我们自然也不会任神宰割,”白孤看着玄君阳,他的眼神中有着光,“即便是神,也没有随意定夺的权利,何况是人。死两人而救一人,不可。”
“嗯,”听着白孤的侃侃而谈,玄君阳点了点头,放下翘起的腿,将身子慢慢探向白孤,开口问道,“如果是我的命呢?如果是死两人而救我命呢?”
“……”
面对这个问题,白孤终于还是沉默了。当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命被放置在天平上时,他是毫无恻隐、没有丝毫迟疑的。但当这个人是玄君阳时,他却不得不重新作出考量。他的心里鄙夷自己对于立场的游离,但他又不得不认同,这就是他。他是不可能愿意眼睁睁看着玄君阳去死的。
“不行,”白孤笑了笑,这笑容表示接下来的对话他将放弃严谨的立场,只作为闲谈,同时,他转用了英文,“如果是你的话,我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你去死。”
“那你该怎么办呢?”玄君阳也笑起来,伸手去抓住那雕塑的脑袋。
“我没有办法,”白孤摇摇头,“不过,既然你说要牺牲两个人救你的命,你看我这条命怎么样?至于另一个,你还是另外去寻吧!”
“喂!你说什么呢!”听到这话,将简·格雷一把揪住白孤的胳膊,好像他真的要被献给玄君阳一样。
玄君阳垂下头去,发出“哼”的一声笑来,他似乎已经预见到白孤的选择,像他这样温柔待人的人,也许真的能做出牺牲自己的事来。
“你这人还真是,”将雕塑抓在手里,玄君阳有气无力地笑着,“你放一万的心吧!我还有一万年好活,也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说完,他站起身来,手里依然捏着那雕塑:“乏了,我要去睡觉了。你们俩也早休息吧。”
看着玄君阳的侧脸,简·格雷没说话,眉头却已经皱作一团。
“对了,”玄君阳低头指了指茶几上的译本,“简,这译本能借我么?我最近的研究有了进展,如果研究顺利。我们在夏天就可以进行探险,今年下半年你们俩可以顺利结婚,两不耽误。”
“嗯……嗯,好,”简看了看白孤,应答着,“你拿去吧。”
微笑了一下,玄君阳弯腰从茶几上拿起译本,快步走出了白孤的房间。
“白孤!”待玄君阳消失在走廊拐角后,简才慢慢伸手揪住白孤的袖子,显出局促不安的样子,“你说的不错,我真的感觉到了!”
“感觉到什么了?”白孤笑了笑,伸手摸摸简的脑袋。
“玄君阳啊!”简皱起眉头,“我觉得他刚刚问你的问题好可怕!”
“只是开玩笑而已,你别当真。”
“可是你看他的模样,哪里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再说,哪有拿朋友的性命开玩笑的!”
白孤点了点头,却没有说什么。只是扭头看向那扇被风吹动左右摇晃着、喑哑不止的窗户,任凭简将自己的衣袖拽得更紧了一些。
……
“局势似乎又突变。先前能够看见的微弱的曙光此时又被猛地盖上去,使四周变得愈发黑暗起来。我看,你当长居伦敦,十年之内都勿动回国之念,若有心仪女子,谈婚论嫁,自然最好。”
“父亲近来身体欠佳,家中产业已由我全权操持,只是时局动荡,只怕要被征去多半。却不知这样的世界什么时候有个尽头。”
白孤推开窗子,外面没有什么风,不是闷热的天气,却只让他觉得发昏。
现在是七月,1927年的七月。
白孤回头看了看沙发上,简正躺在那里,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鲜亮的光块儿落在她的身上。她睡着了,伴随着均匀的呼吸,胸口微微起伏,闭着的眼睛偶尔地抖动一下,可能是在梦里看见了什么。
白孤悄悄走到简的面前去,端详了一会儿,又怕打扰了她睡觉。于是便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站在走廊里,靠着楼梯的扶手往楼下的客厅张望。
楼下的空间其实也并不宽敞,但因为厨房所在而时常被清理,幸而没有落上灰尘。
“你在外面站着干嘛?”走廊的那头传来玄君阳的询问。
白孤扭头看过去,眉头又不由得紧皱了一下——不到半年的时间,玄君阳的状态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他的发色倒是一如既往的黑,只是那种黑色少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一种哑光的、仿佛假的一般的黑。而与之相反的是他的肤色,白孤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就好像死去的人一样,没有血色、白得令人心悸。同样淡去的还有他原本黑亮的眼睛,好像被风沙剥蚀的黑色岩石露出内里棕色的本质,玄君阳的双瞳不知为何开始慢慢变成棕色,甚至在白孤不经意间的观察时会露出一丝红光。
白孤曾多次要求他去医院看一看,却总是被玄君阳用各种借口搪塞过去。只是见他的身形依旧挺拔而笔直,跟以前无二,白孤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每日些微的变化,竟让玄君阳不知不觉间仿佛变了个人一般。
“简睡着了,不想打扰她。”白孤舒展眉头,不想让玄君阳看出自己的担心。
“你对她也太好了,”说着,玄君阳一步步走过来,“你最近难道没有课程么?看你一直很悠闲的样子。”
这年将是白孤与玄君阳最后的学年,等这一年度结束,他们二人就将以教师的身份留在学校了。
“我的课程早就结束了,”白孤耸耸肩,“难道你还有很多课要去么?”
玄君阳笑了笑:“我是去找书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多月的时间玄君阳完全没闲着,他终于找到了关于那怪异雕塑的线索。虽然出于对简的嘲讽而没有透露研究的过程,但最终他的矛头指向了格陵兰岛。
“既然是银光坠落的所在,恐怕冰岛不过是银光坠落削斩大陆留下的碎屑罢了。不过,我倒是觉得书中记录的不过是一次陨石的坠落,根本不是什么神明坠落天空。”这是玄君阳得出的结论。
伸了个懒腰,白孤看着玄君阳:“希望这次能有所收获。”
玄君阳笑了笑,扭头朝向楼下的客厅,一双眼睛无神地睁着,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你说得对,希望不虚此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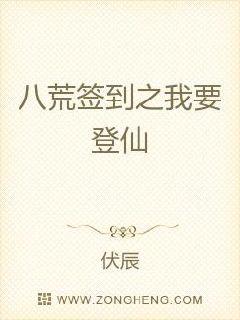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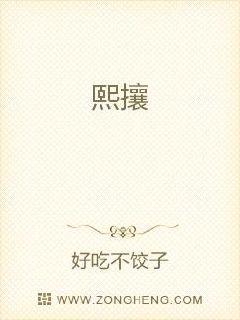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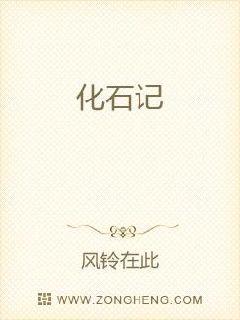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