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扬威抖擞颐使囚,无妄之灾强点兵
谁知那牢头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霍辜只当他胆小,劝他:“莫要多心,我也不做什么,不过是大家来见个面,一块耍子,将来干活时关系也好些。”牢头道:“司狱有所不知,这天牢的上一位司狱,正是在席上无趣想叫几个的女仙一块喝酒,叫成桓真君巡视时撞见了,直接免了位置,女仙也都调走了。”
霍辜酒没喝尽兴,便趁着酒兴到牢里烧烧他新官上任的火,遂带了人往天牢里去了。时夜已深,狱卒将犯人一个个叫起来,让他们出来,一排一排地跪了。霍辜象征性地讲了几句,见下面的人头也不敢抬,自己说什么都连连称是,觉着有些意思,瞧见了有趣的,就问起话来。
这牢里的人,不是老实木讷的闷葫芦,就是精细狡猾的泼皮,霍辜越问越是起劲。跪在倒数第二排的男子虽未被问到,也支起耳朵仔细听着这位新司狱的话,想象着一会儿被问到了该如何回答更能讨人喜欢,他听到霍辜说:“哟,这牢里竟有这么年轻的凡人!”
对方不答,霍辜又说:“你到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啊。”
对方沉默许久,小声的说:“我没有犯事。”男子听出来了,是天牢里那个鲜少言语的少年,人人皆传他神志不清,以作弄少年取乐。
“哈哈哈哈哈哈,也对,犯事的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犯了事,可你都进来了,做过什么浑事儿就说罢,哥哥们也不会笑话你。”
这时少年的声音大了一些:“我说了,我没有犯事。”
霍辜似乎被少年的姿态惹怒了:“没犯事啊?没犯事你能到这来啊?也不看看自己身上的囚服,难不成是我冤枉了你?”
“就是你们冤枉的我!我什么都没做,若非你们官官相护……”
“啊!”男子听见少年话未说完,牢头就突然叫了一声,似乎是牢头摔倒了。
“这混账东西!好大的胆子,险些推了老子。”霍辜骂道。
“胡说!分明是你先掐的我!”“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拦着点!”牢头一声令下,男子抬头起身,跟着其他犯人一起把少年七手八脚地制住了送到霍辜面前。“鞭子。”霍辜道。牢头连连摆手:“小子不懂事,打坏了如何是好。”
“要你多嘴?”霍辜瞥了牢头一眼,牢头连忙取了鞭子送到霍辜手上,霍辜扬起脑袋,用下巴向牢头指了指,对少年说:“道歉。”
“分明是你先掐我,他也跟着你来……”
“道歉!”“是你掐……”少年的话说到一半,霍辜手里的鞭子便“咻”的一声抽在少年脸上。牢头与边上几个犯人都劝少年:“你且认个错就是了。”“是啊是啊,他也不会为难你。”“到底是你推了人家。”“这么晚了,你且认了,大伙好回去睡。”其他人附和。
少年万般无奈,只得道一句:“对不起。”霍辜冷笑一声:“早说不就完事了,”一把将手中的鞭子摔在少年脸上,又对牢头说,“这牢里的人你可得教些规矩,拿出几分样子来,莫要再这样丢人现眼。”
方才这一闹,霍辜酒醒了大半,丢下此话便离去,牢头在后面追着送,回头用眼神示意狱卒收拾残局。
却说陆曜上回见着霍辜耍官威的模样,又打听了一番,才发现殿里的散仙这样的还不少,一个个官不大,架子倒足,只管五人的小队长,还自己在里面找了两个副手,副手又自己定规矩来约束其他人,嘴上都说的是在教规矩明纪律,让他们明白身为天兵要服从指令。事实上,若谁与这些野官儿搞好了关系,不仅可以不守这些假规矩,甚至还能有些特权,违反军纪也不被责罚,怪不得天兵之中看似管教的越发森严,不务正业媚上欺下的却越发的多。
自己不过是百年不在,竟成了这般样子,成桓想必也是蒙在鼓里,陆曜无奈摇摇头,即下今严查殿里散仙之中私设职位、私定军规者,一经发现,即以以下犯上问责,若又纵容他人违反军纪的,以共犯论处。
陆曜也明白此令绝不会立即生效,那群人八成会勒令底下的休要生事,做出一片祥和的样子来,那底下的人或是贪图小利或是迫于淫威也自然不会出来检举,即便如此,那些人最后定会因怒或妒而出言相抗,这才是该法令大显身手的时候。
此令一下,下面的散仙自然是怨声载道,自己辛苦了这般久,谁知跪也跪了,这位置还没了,又得讨好自己平日里管教的下级,生怕他们到陆曜那告状。这怨气多了就不好好做事,叫不动人的陆曜为了不误事,只得自己多跑两趟,反正也快到招新人的时候了。
一日陆曜听人议论说凡间天牢的环境不大好,便决定突击巡视一番,遂到了甬州天牢巡视,方进了天牢往里走了些,便见那甬州天牢的牢头许已惊慌失措地跑出来,心下起疑,拦下他问有何事发生。牢头只说无事,绕过陆曜跑出去了,陆曜疑心更盛,直往那牢头来处疾行而去,见一狱卒拖着一人而出。
狱卒见陆曜,乃大惊,忙跪地求饶,连喊饶命。陆曜问发生何事,狱卒说此人在狱中与人生口角,打了一架,谁知突然就没气了。陆曜见那人是个凡人,身形瘦弱,不过才十三、四岁的年纪,又问:“此人是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年方几何,所犯何事,入狱几年?”谁知那狱卒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支吾了半天,只道去找大夫,也跑了出去。
因发觉此人尚有些阳气,尸身未凉,复摸其项,隐有跳动,似还有救,陆曜便一心救人,没去拦他,一边摸出一颗救命丹药与人服下,一边施法传信叫同来巡视的玉琼来此。
陆曜施法颂诀,指尖冒出一道电流落在那人身上,电流在那人身上游走了一圈,究其病理,原是广泛性组织损伤引起的器官衰竭,故而出现了呼吸暂停、昏迷的症状。
方才给其服下的药物不过是令阳气不散血不凝滞,与他一时吊着命罢了,陆曜再度施法,右手掌中电流涌动,只见他左手捏诀,右手作剑指,在那人胸口上一点,那人体内的血液受术法催动开始流动,靠着法术供能强行让物质得失电子发生反应,叫身体机能再度运作,将那人的内环境恢复稳态。
施法之中玉琼赶来,陆曜寻思着这些法力想必能让他撑到见大夫,嘱咐了玉琼速速带人往附近医馆就医,又说明了此人身份不明之事,叮嘱她小心,便出去找那牢头、狱卒要问个清楚。
哪知他一出天牢大门,便有一男子扑上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扯住他,直喊:“陆哥哥!你可得救救我!”陆曜细看了那人的面貌,实在是想不起来自己与他有甚么亲故,一边将袖子从那人手里扯出来一边问:“松手……你是何人?何故来此,我又为何要救你……有什么话且松了手好好说!”
那男子不松手,只道:“哥哥不认得我了,我姓严名鹤字于飞,我父亲的表兄与你父亲可是故交啊!当年明康真君行冠礼时我也曾去过的,哥哥可曾记得?”陆曜仔细想了想:“不记得。”
“哥哥现在不记得倒不打紧,只是眼前有桩急事要解决,里头方才死了个人,那人原是害了我的,我托人让他吃些教训,谁知他到牢里也不听话,叫人打死了,如今死了人定会追查到我这里来,还请哥哥帮帮我。”
“你自个儿做了错事,我又何必要帮你。”陆曜手里一用力,将袖子自严鹤手中拉了出来,严鹤又上来抱住他的胳膊:“不要这样嘛,哥哥想要多少钱我给便是,我会请人来处理尸体,不劳哥哥费心,你只消的当作这人从未在天牢过,便无事了。”
“谁要你的钱了?”陆曜拖着严鹤往外走,“既然敢做为何不敢认,你为一己私欲动用权力,害了他人又坏了我真武殿的名声,帮你作甚?既然不松手我便直接将你带回天庭审问了。”
说话间,一道惊雷劈下,陆曜条件反射施法,化出一道雷将惊雷引向空地,又有数支箭射来,陆曜扛起严鹤侧身闪避,就在他应对之间,一众天兵以将二人包围,手持利刃冲上来,陆曜将人放下,拔刀以应,问曰:“尔等作甚?”
丹霄从远处走来,边走边喊:“通天府接人举报,宣肃真君动用私刑,杀害无辜,我等依照律令,为防毁尸逃佚直调天兵前来拿人。”
严鹤喊:“你胡说!如今我陆哥哥执掌刑狱司,他要抓谁便抓谁,要杀谁便杀谁,轮得到你通天府说个不字?”
陆曜喊:“休要胡说。” 这话明面上是转头对严鹤说的,也算是对丹霄说,“贵府无凭无据,如何说我杀了人!”丹霄一抬手,命天兵停下:“既然你不承认,那我们就进去,到时候见了尸首,看你能狡辩到何时!王谨!”说罢跟在他身旁的王谨神君应了一声:“小神在。”便走上前去,将一副锁链呈至陆曜面前,说:“先委屈真君了。”
陆曜不解其意,那王谨又道:“真君法力高强,一会子在天牢里地方窄,天兵也不能进去的太多,我等也是为了保险,既然真君无罪,戴一会子又何妨。”陆曜冷笑一声:“既是要看了尸身说我有罪,这尸身还没见着,我戴这链子算个甚么意思。”
“心虚了?”丹霄眯起眼睛,王谨从中调解:“在下相信真君是清白的,不过其他人不信,还要证明证明,真君还是快戴上罢。”陆曜见那二人一唱一和,颇为有趣,顿生一计:“我倒有个法子,我无需进去,天君也无需进去,只派几个天兵进去,若有尸体便拖出来验一验,若能验出是陆某杀的人,陆某自己将这链子戴上!”
“好!这派的天兵你来选罢,莫说是我与人串通好了欺负你。”丹霄道。即使丹霄这般说,陆曜也要用个随机的方法选人,以示自己没有串通熟人。陆曜便随手指了一列天兵出来。
那一排天兵得令进了天牢,过了半日方出来,对丹霄汇报:“启禀天君,属下已在天牢中搜查了三遍,并未发现尸体……”听这话时,陆曜注意到严鹤的表情并不是应有的如释重负,而是有些害怕,“……不过在一间空牢房中发现有新鲜血迹。”严鹤偷偷的松了口气。
丹霄连忙喊道:“来人!速速将他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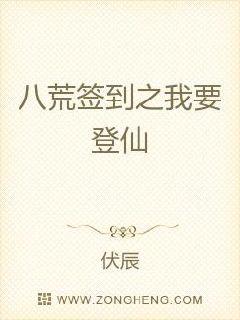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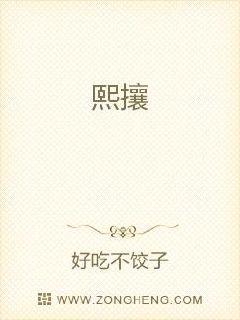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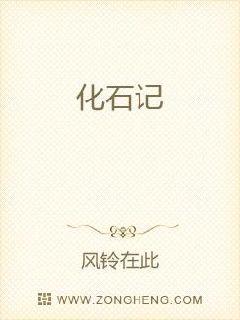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