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阿蔓不是草
地主老爷叫马厚福,有一个大老婆,三个小老婆。要知道这四个老婆的来历,还得从大老婆的爹说起。他财大气粗,叫他李老财主吧。李老财主四代单传,活着的时候,算是攒下了金山银山,可每天总是唉声叹气,就是因为膝下无子。女儿倒有一个,可那没用。按照族规,女孩子早晚要扫地出门,财产要在院中族长的主持下,按照亲疏远近继承。良田千顷,家私万贯,牛马成群,留给谁呢?难就难在他也是族长,不按族规办吧,族人都要指脊梁骨,按族规来办吧,院中最近的人也在五服沿上,舍不得呀。怎么办呢,唱出大戏吧。内人演了十个月的怀孕大戏,他在外面觅了一个男婴,又大摆了宴席,让众人尽知,有后了。如果世间没有意外的话,这故事可能就要结束了。可偏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老财主命根 子弱,担不得,小男孩八岁的时候,到河里捉鱼淹死了。一家人那个哭哟,惊天动地呀,族里人,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假惺惺嘘长问短拐弯抹角最后都映射到家产。把他气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头发都要竖起来。都是些什么人呢,平常没少接济你们这帮浑球,没想到都是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的王八蛋。还有那族规,简直就是混账规矩,生而平等的人,为什么重男轻女。破烂族规,必须得改。闺女我就不嫁了,我是族长我说了算,谁要说不算等他当了族长再说。谢天谢地,好在还有一个女儿,要不然,可怎么活呢。好不容易,女儿拉扯大,招赘了一个女婿,就是马厚福。马厚福来到这里十年,也没添个一儿半女。李老财主实在等不急了,先走了,死不瞑目呀,还是挂着他的家产没人继承。老多事,真是强求不得。
没办法,经老婆子同意,马厚福纳了一妾。几年下去,妾的肚子里也没动静。马厚福担心起来,自己真的还不如老丈人?可真够麻烦的。怎么办,再纳妾?老婆子不干了。“原来嫌老娘的地不好种,现在看来你是个孬种,干脆从哪儿来滚哪儿去吧。”这可不得了,都是休老婆,哪有休汉子的。真没辙了,马厚福索性就到外边偷偷的找女人,一下子找了仨。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人立马就怀上了。马厚福这回腰杆挺直了,头也昂起来了。把这两个女人都收到房中。大老婆起初不肯,闹腾了一段时间。后来想明白了,休了马厚福,自己也不能生,还是无济于事,只得忍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所有的事都要为子嗣让道。大老婆说了,添了女孩,也便罢了,若是添了男孩,必须随她家的李姓。马厚福不太乐意,刚要反驳。大老婆劈手就是一巴掌,“姓李,姓李,就姓李!姓了马,早晚都得滚蛋!”马厚福一琢磨,确实不能姓马。姓了马,院中李家的七狼八虎肯定又要来嚷嚷家产。自己得个实惠也就得了,何必计较那些虚名。
不久,两个孩子一前一后出生了。男孩就姓了李,女孩也没人计较姓啥,就依照“大仙儿”的指点,叫她阿蔓。
这个阿蔓,从小身子骨虚弱,经不起风,淋不得雨。一月一小病,一季一大病,几乎每年都要闯闯鬼门关。把马厚福折腾的整天喊:“造孽呀,造孽呀。”不过在大老婆的面前,他是不敢喊的,只要一喊,大老婆就会不耐烦:“舍了吧,舍了吧,让她去个大庙,那里的佛大能护的住。”马厚福可舍不得。阿蔓虽然是个病秧子,可心眼活,贼机灵,而且还是个美人坯子,万里挑一。在马厚福的精心呵护下,阿蔓已是及笄之年,出落的天仙一般,准能找个好人家,高攀上一枝,将来儿子再顶门立户,我看院中哪个混账王八羔子,还敢惦记自己的家产。
马厚福使人四处暗中宣扬,他家有温玉软宝,待字闺中。
果然,提亲的,说媒的,套近乎的络绎不绝,只是没有一个被马厚福看中的。
确实,一块好玉,就是要待价而沽。
邻村的大财主来了,马厚福摇头,心里说几个臭钱谁还稀罕。县太爷寻儿媳,他也不允,小小的县令,他还真不放在眼里。郡守纳妾,他还不点头,要嫁就得明媒正娶,怎能与人做小。碰头磕鼻子的媒婆,嘴里不说,心里也嘟囔,“架子太大,早晚得被人端。”心中不满那是肯定的,捞不到油水,只好悻悻的离开。大小媒婆唠里唠叨,逢人便讲,再添油加醋,这舆论造的势可就大了。
其实马厚福也有自知之明,不会盲目的一直妄自尊大,不久就应了一门亲事。那头是朝庭里的大官,而且还沾上皇亲国戚。见好就收吧。成了这门亲,就可以显赫乡里乡外了,马厚福那美梦做的,都能笑醒。
马厚福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臭放牛的下贱的长工竟然和阿蔓做出那样的事——竟然在背地里背着阿蔓。
阿蔓出门那天马厚福被县太爷约去了。拒了县太爷的婚事,马厚福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县太爷一怒就把他给抓起来。虽然能和朝里的大官联姻,可毕竟还没成,县官那可是现管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去了再说。马厚福硬着头皮跟着小厮走了,一路上琢磨着怎么为自己开脱,思前想后的怎么也不妥。见了县太爷,两腿都有点哆嗦。刚要跪下,却被县太爷弯腰扶起,而且是扶到座上,而且是扶到宴席的主宾座上,面前满满斟了一杯酒。奥,原来是想错了。县太爷不是问罪,而是拉拢关系,为了日后有人提携。马厚福把心放到肚里了,那么好的菜怎么不吃,那么好的酒,怎么不喝,那么好的话,怎么不听。什么事都满口应承下来,吃了一肚子的好酒好菜,晕晕乎乎的就回来了。刚一坐下,地主婆子就进来大喊大叫起来:“去看看,去看看,你那个不要脸的疯丫头在外面丢人现眼!大白天的让那个猪狗不如的阿牛给背回来了,我要不是站在高坡上去寻还真发现不了。”
“你这个臭婆娘满嘴喷粪,快闭上你的臭嘴!”马厚福上去就是一个嘴巴子。在马厚福眼里,阿蔓比宝还宝,比玉还玉,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今天酒也喝高了,管他天王老子,敢污蔑他家姑娘,就该打。打完之后,手却不停的哆嗦起来。
地主婆被打得嗷嗷直叫:“反了你了,竟敢动手打你老娘!你这个该死的糟老头子是活到头了。”一手捂着流血的嘴巴,一手又打过来。
马厚福不敢还手了,吓得慌慌的跑到院子里,看到正想吃饭的阿牛,一脚就把碗给踢飞了。“滚滚滚!想活命就快滚!”
赶走了阿牛,马厚福更加害怕起来,要是这事传出去,被未来的亲家知道了,麻烦可就大了。
看来,自家姑娘也该管管了。他大步流星走到闺房外面,不管三七二十一,借着酒劲冲阿蔓就大吼:“阿爹已经给你找好了婆家,以后再疯疯癫癫的乱跑,小心打断你的腿!”
阿蔓先是吓的一激灵,缓过神来,哭着嚷道:“阿蔓不是一棵草,想栽哪儿就栽哪儿。”
马厚福气得浑身哆嗦:“叫你娘来,把门锁了,没我的话,我看谁敢开门。”
马厚福转身又唤来了管家:“今天的事谁漏了嘴,小心你们的皮!”
马厚福气呼呼的回到自己房中,看到大老婆立在中央,手持鸡毛掸子,那是处罚自己的惯用刑具,马厚福这才忽的一下想起刚才狠狠打了这个母夜叉一巴掌,现在酒有点醒了,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于是腿一软,直接跪了。
家里的事还没消停,第二日,媒婆就引着人来送聘礼了。“那边大人对了八字,择了吉日,下月初六过门。可喜可贺呀!”
马厚福在心里算了一下,下月初六也就十几日的时间,可那丫头一时转不过弯来,真让人头痛。
马厚福装作若无其事的满脸堆笑:“同喜,同喜,有劳,有劳。”随后命人封了红包,安排了酒饭,将媒婆一行人打发走了。
媒婆一行人自是欢天喜地,马厚福可真犯了愁。饭也吃不下,觉也不着。真是作孽。
眼看婚期一天天逼临,马厚福一家人真的做不住了。用尽了所有的招数,那个倔丫头只有一句话:“阿蔓不是一根草。”
“你不做草,我们一家人都得做草。”马厚福生平第二次吼女儿。
“谁愿做草谁做草,我就不做草。”阿蔓也是生平第二次顶撞父亲。
“这草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后天就来八抬的大轿,一长队的吹鼓手。”马厚福咬着牙,跺着脚。
“愿抬谁,就抬谁,谁愿吹,就让他吹,反正我就不出这个门,出门我就死。”阿蔓的语气硬着哩。
“死也得出这个门,不信我就治不了你。”地主婆子在外面大喊大叫,什么事也没有解决了,气得像吹猪的一样,脸涨的黢紫,眼睛瞪的像铃铛,叉着腰,来回胡晃荡,凶神恶煞一般,马厚福在那里一个劲的哎呦,那几个小老婆都闪得远远的,傻傻的看,不敢发一言。他的儿子更是吓的哇哇大哭。马厚福这才换了一副面孔,走过去,抚着儿子的头,“不哭,不哭。”回头恶恶的瞪了一眼那个还在吼叫的母夜叉。
初六日真的到了,马厚福家准备了红纸也准备了白纸,准备了红灯笼,也准备了黑灯笼,准备了红袍,也准备了孝衣,我的妈呀,这是搞的哪一套,唱的哪一出。
马厚福说了,把红盖头挂在小姐的房门口,把白纱挂在自己屋内的梁上。迎亲的队伍到了,小姐要是出了门,红盖头就给小姐盖上。小姐要是不出门,白纱就套在自己脖子上。
大家的心都悬在嗓子眼,是喜是丧,是福是祸,都在今天了。
天阴沉的很,灰暗的很,闷热的很,像要下大雨了。人站着坐着都淌汗,手里的扇子偏偏摇不来一丝凉爽。大门外,远远的飞来了几匹快马,扬起团团尘土,倒像是被妖风裹挟,看了就让人胆怵。
骑马人在门前勒住了马缰,翻身下来,径直入内。马厚福心想:坏了,坏了,迎亲探路的已经到了,小姑奶奶还是不出门,看来自己的死期也到了。
马厚福脸如死灰迎上前去,邀其入内喝茶。
来人却说道:“不必了。奉我家大人之命传告,皇帝下诏遴选天下秀女,即日起,举国暂停婚嫁,待其事毕,再议婚期。”
这是做梦,还是在看戏,竟有这样的事,马厚福直接就傻在那里了,来人是怎么走的,都不知道了。不过确切的事实是:今日娶亲取消了。
闷热发酵的天空终于吹来一阵风,天气立马凉爽了很多,马后福头上的汗珠都消失了。他缓过神来,心中顿时巨石落地,眼生光泽,面露喜色。选秀选的好啊,选得太及时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万万岁!”马厚福嘴里高喊着回到屋内立即与老婆们说道:“走啊,到灵妖寺进香还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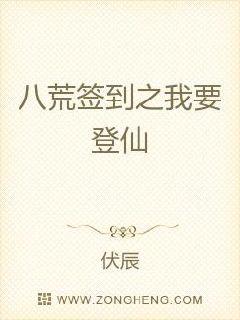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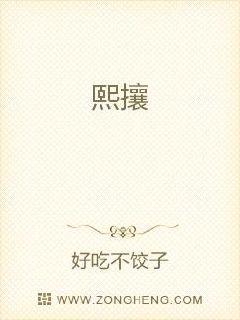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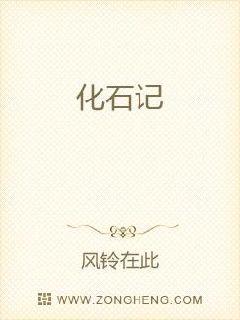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