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欺
“虎毒还不食子。”
入夜后的化天宫灯火辉煌,内廷总管淳于欺下令所有掌灯太监今夜不许轮休。此刻他倚在昆仑玉石雕刻而成的梁柱旁凝视黑夜中的皇宫内廷,忽闻到夜风中飘来一股潮湿的气息。今夜将会有大雨落下,他眼神中透着笃定。两旁侧立的小太监似乎对总管大人的话不明所以,但好奇却比不过他们心中的畏惧。因此只能收起好奇在一旁恭恭敬敬。
圣皇寝宫轩辕殿四周寂静如常,它的第一位主人已经飞逝千年,可现如今他的名声却在九州越来越响亮。轩辕神剑的事迹起初只留存于史书,不知何时何人通过何种手段将之流传民间,从那起神剑的威名便一发不可收拾。人们奉他为诸神的利剑下凡人间,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事迹流传久了便成了传说,从此之后轩辕殿的每一位主人都试图成为传说,可到头来他们发现真是难上加难。
“总管大人,圣皇宣您进殿。”
漆黑的牢狱中僧人猛然惊醒,多少个夜里他都重复着同一个梦境,醒来时总是浑身尽湿,一定是梦中的往事不堪回首。四下安静无人,僧人发现自己居然在一座单独的牢间。灰蒙蒙的眼眸在黑暗中极力寻找着记忆,可搜寻片刻后却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我是谁?我怎么在这?刚才的梦…”
“你醒了,赶快起来跟我走。虎大人有话问你。”
一声粗狂的嗓音突然漂浮过来吓得僧人心惊胆战,守卫不知何时出现在牢门前面,手里举着火把似乎要把他看穿。胆寒过后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痛的感觉袭来,僧人发现自己双臂缠绕着厚厚的绷带,里面又痒又热搅拌着钻心的刺痛令他冷汗直流。即使如此他还是被枷锁囚禁,双臂举在胸前看上去毫无自由可言。
“你最好老实点。教士大人为了你的双手可费了不少力气。”守卫是个满脸麻子的粗野汉子,脸上的表情十分狰狞。漆黑潮湿的牢底暗无天日,他的脸没化成厉鬼就已经很好了。
“大人,找我何事?”
“你少给老子装蒜,我告诉你秃驴。识像的最好从实招来,否则虎大人有的是办法让你张嘴。”
麻子守卫不仅表情恶劣,言语还颇为不敬。反观僧人依旧跪坐地上,脸上的表情也很迷茫。对方的语气让他觉得心凉,也有些不明所以。他目前脑海中最后定格的画面和刚才的梦境一模一样,难道他还没从梦中苏醒。这阴森的地牢只不过是和那金碧辉煌的宫廷一样是一种幻象。
“大人,我。”
“你他娘的少在那磨磨蹭蹭,赶紧起身跟我走。还有别叫我大人,你他娘的见过哪位大人是守牢门的?”
麻子守卫的恶意令僧人有些迷惑,他虽记不得自己的身份,又不明自己所在之处。但心中向佛的那份虔诚仍在,许多经典奥义他马上就可以从脑海中调取出来,好好的和面前的麻子脸辩驳一番。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不知哪里得罪过大人,方才苏醒大人就一直恶语相加,我。”
僧人的话再次被迫打断,只见麻子脸伸出铁桩般的胳膊一下子揪住了僧人的脖颈像提鸡崽儿似得把他悬在半空。僧人只感觉自己双脚踏空,一股强烈的恶心感在胃里翻腾。
“秃驴,别在青龙神的地界放你那什么佛主的狗臭屁。我们北方人只信青龙神。”麻子守卫显然对僧人的信仰有成见甚至是偏见。这不能怪他,整个盘古信仰四神几千年,有时青龙占上风,有时白虎领先,南方信任玄武,而那些朱雀的信徒则一直守在谷地里面。四神的信徒分分合合争辩了千年,哪会容得下一个从海上飘来的异端邪教。整个九州的异教徒几乎都被圈禁在净土寺,鲜有的幸运儿也只能像老鼠一样深入地下,惶惶不可终日的过着黑暗无边的日子。
“罪过,罪过。出家人不打嗔语。大人如此亵渎佛主,是要遭天谴的。”
僧人虽然还未从迷茫的状态中抽离,但信仰不容侵犯。他面无表情的看着麻子脸,渐渐脸上泛起一层红晕,紧接着听见喉咙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翻涌,最后喷出一片血光四溅。血光里夹杂着未消化的烂菜叶、糙米和已无可辨认的食物残渣,瞬间牢房里充满了酸臭的馊味,腥臭的血味和麻子脸尖锐的悲鸣。
天谴瞬间灵验,守卫赶紧松开作呕的僧人,用手抹了一把满是残渣的麻子脸。整个人仿佛被熔酸泼了一番乱叫乱跳,嘴里那恶毒的咒骂引得周围无数只眼睛投来好奇。
“大声喧哗,成何体统?”
侍卫长虎彪的威严在木牢中特别令人生惧。所有罪犯怕他,所有流民也怕他,所有的守卫更怕他。麻子脸闻声立刻紧闭大嘴,时不时还干呕几声。
“你就是那个叛僧?”
一个叛字仿佛利剑一般刺入僧人的心口,本就苍白如纸的脸庞显得更加凄苦。胸中的积郁倾泻而出,反倒令他神志清醒了一些。眼前站着一位膀大腰圆的壮士,比起麻子脸要高大好几层。对方心中笃定的将叛字加在他的身上,他不想辩驳,也无力辩驳。
“回大人的话,贫僧法号…额,法号。”
僧人毛骨悚然的望着虎彪,对方在等着答案,可这答案却一片空白。他甚至觉得奇怪,为何自己一身破衣被囚禁在这监牢中,他有何罪?于是乎他在脑海中搜索,粉碎的片段怎么也拼不完整,只能把话卡在半截。
“依我看定是那冲击波的余威伤到了他的脑髓,令他暂时失去记忆。”白衣教士骆杰缓缓从壮士身后走出,面无表情的望着僧人。“我看还是移步问话,这里的味道让我忆起那条流经教城的清水河。”
时空转换之间僧人已经被押送到木牢顶端的审讯之所。各类刑罚的器具罗列整齐的挂在西面残破的旧墙上,墙上似乎还有片片血痕,它们七扭八歪沿墙体向下描绘出这里曾经是一处恐怖的地方,这里应该不缺鲜血与嚎叫,大多数人都是走进这里最后被抬了出去,正如这位懵懂的僧人那可想而知的下场。
“大人,贫僧从幽暗中醒来,只觉得双臂剧痛,头脑混乱不已。贫僧无意隐瞒任何事情,还望大人明察。”
骆杰查看着流民薄册,对僧人的话充耳不闻。虎彪见状也只好附和着保持安静。这是一本泛黄的羊皮纸书,厚重的它诠释着近五百年流放荒原的人们那凄惨的下场,它上面的每一行字都有着一段丰富而辛酸的故事,只是字迹所述的主人如今都已在那黑色荒原上被寒冬粉碎了身体,泯灭了希望,封印了灵魂。
“净土寺灶火房柴火僧法能于圣元三年入寺,本名朱季是湖州弱水湾普陀村渔长。因在集市顶撞扶余山国贵商被判劳役五年。劳役中玩忽职守,引发堤坝透水事故至两人死伤后被判宫刑。圣元元年春入内廷编为掌灯太监,因散布邪教箴言被遣送净土寺圈禁。天归七年,私自逃离净土寺被抓,判流放。”
“你的眼睛是如何失明的?”
骆杰反复斟酌着簿册上的记述,这个叫法能的叛僧居然是一位阉人。而他们要找的内廷总管淳于欺恰好也是位太监。天底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老教士万万不可相信。他仔细辨认过僧人的容貌,秃亮的头顶罩着一张普普通通的脸,只有那灰蒙蒙的双眼令人关注。
“回大人,我脑子乱,只记得在寺庙内整天劈柴生火,那浓浓的炊烟总是熏的眼睛生疼流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双眼就成了这般模样。”
“少在那蒙事,你为何要逃离净土寺?何况你熏瞎了双眼,想从教城眼皮子底下逃走堪比送死。”
虎彪没有教士的气度和素质,他大手一挥直直把僧人从一角拎到另一角落,旧墙上那排排刑具在黑暗中闪着白光,直刺僧人的瞎眼。本是试探加威慑,可再看僧人平静如水,口中还念着佛主的经言,一副临危不乱的表情着实让虎大人尴尬半分。
“阿弥陀佛,我本是苦海泛舟之人。只因在集市上不平同乡吃亏上当点出那些桑贼的计量就被记恨在心。他们无事找茬,栽赃陷害终让我走上了囚路。自打归入佛门,我一心向佛寻求心中的平静。可那年冬食节的参拜日上我偶遇乡亲,念起家中老娘孤苦伶仃实在是大大的撼动我的佛心,最终酿成这流放之苦。善哉,众生皆有情,何日我能放下烦恼心报以佛门。”
大如山的压力来自那些白晃晃的刑具,反倒让僧人的记忆碎片整合起来。他感受着双臂的剧痛,豆大的汗珠顺脸流淌汇聚成滴水掉落,汗水拍打着坚硬的地面令时间飞转,他只觉身体不由自主变得软绵绵,一定是剧痛在作祟。
“骆师父,您看今天?”
虎彪知晓这僧人的身体一番折腾肯定吃不消,现在没别的就是有时间,他可以慢慢陪他玩耍,早晚戳穿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瞒。但是教士却没有停止的意思,只见白袍在夜风下轻拂,一瓶绿色的液体魔法般的现于掌心。
“啊?您这是要。”
上一次见教士使用真言散还是七年前那个狂乱的夜晚,那个被九州唾骂的罪人和那张绝世惊艳的俏脸深深的令虎彪感叹。骆师父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让罪人开口认罪,无奈只好将她遣送荒原。
“诸神降下旨意,倾听世间真言。在诸神面前请道出你心中的真实。如果有半句谎言,你将受到神谴,记住是真正的神谴。”
幽幽的绿瓶定格在教士与僧人之间,里面淡绿色的液体安静如水。四目相对,睿智的教士对着迷蒙的僧人反复求索,那场恐怖的爆炸夺去了十九条流民的生命。教士冥冥中有种不祥的预感,这可怕的事情一定还没完。
“我心中没有诸神,但是大人让我道出真言,我只有服从。”说话间僧人接过药水一饮而尽,动作麻利得像在喝着什么甘甜的美酒一般。静,空气中只有安静,只见僧人盘膝而坐,双手勉强做着参禅的动作。此时再多的言语已无用,唯等药水起效后真实的谎言自然就会被戳穿。
“虎将军,他没撒谎。”
安静过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只有僧人口中的经言萦绕耳边。白衣教士手中的药剂只是厨房剩下的蜜糖水,他只是想对僧人进行一番试探。他甚至在其中掺杂了些疗伤的成分,对他灼烧过的双手很有疗效。
真言散实际上是一种致幻药剂。里面充满了危险的毒素,每一种元素都对人体危害巨大,整个九州的百姓对它是避之不及,闻风丧胆。僧人重伤未愈,如果再饮下药剂则必死无疑。骆杰知道其中利害,想必僧人也不是白纸一片。试探是相互的,胆量是关键。
“等等,你和那孩子是什么关系?”
僧人闻听此言突然全身抽搐,倒地不起,嘴角白沫溅出一大片。守卫准备押送僧人回牢,虎彪将心里最后的疑问说出,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
“孩子无辜,孩子不能杀,不能杀。”
抽搐的僧人咆哮出野兽般的怒吼,双手不顾剧痛在空中乱抓,双脚乱踢吓得守卫连忙退身。整个人瞬间被打了鸡血一般,又好似待宰的肥猪吼叫着不明所以的语言。突如其来的意外令虎彪僵在当场,关键时刻还是教士反应快,他紧忙上手按住僧人的人中,令守卫按住其四肢以免伤及到人。大约过了几个呼吸,僧人转怒为静,竟然沉沉的昏睡过去。
“娘的,吓我一跳。这,这公爵大人也没说杀那小子。他在这激动什么。”虎彪只是奉命将马奴拴在铁匠火炉的边上,那原本就是他睡觉的地方。比较男孩救过二小姐的命,木神堡怎会做出如此恩将仇报之事。
“骆师父,您看这怎么话说的。”
“无妨,想必他也是精神太过紧张,一时癫狂。观察几天无事就与流民押在一处便可。”
僧人此时已进入黑暗的梦魇,队长与教士的对话他无从知晓。在梦中那片温暖而熟悉的蓝色海洋已被鲜血染红大半,所有人惨叫连连,哭泣震天,淳于家一百七十余口性命瞬间化为乌有,连那襁褓里的婴孩也未能幸免。
一只银鹰嘴角泛着令人恶心的笑容,淡定的望着眼前的涂炭。他尖锐的目光在四下搜索,生怕万一遗漏疏忽留下余孽那可就触怒将军的威严。
“回大将军,淳于家一百七十三口全都被焚烧殆尽。属下已再三清点,但有些尸骨已成灰炭几乎不可辨认。”
那个恐怖的夜晚过后,世上再也没有属于淳于家族的清晨。人们发现珍珠城被大火付之一炬,连只老鼠都没能逃出升天。众人远远的围观,没人关注身后一处不起眼的角落一个身披斗篷,头戴兜帽的阴影怀中抱着一位熟睡的女婴转身远去。婴儿被包裹的很严,一缕浅浅的蓝发粘在额角一边。她睡的很沉,似乎在做着美梦,肉乎乎的小手紧紧握着阴影的领角脸上露出纯真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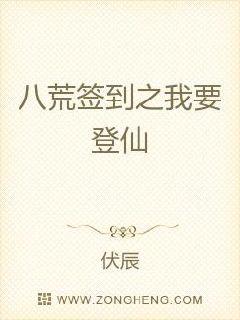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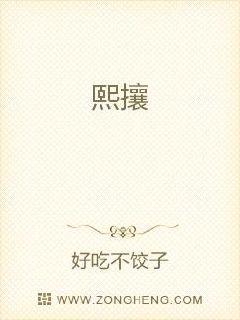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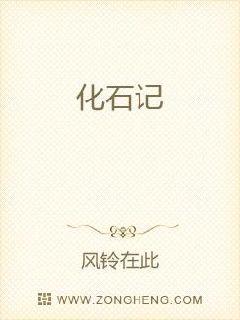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