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补阙
熹微正好,小宅忽跑出来一个头扎丸子的孩童。男娃一边跑,一边嘟嘴吹着口哨。村遭都是合乐欢景,邻家男女刚吃完晌午,正要出门做活,地里庄稼什货还晾着。
“小乐都,出门玩呀?”看见小乐都跑出来,大叔唤他一声。
乐都停下望望,大眼玻璃全是泪水,怜惜惜的看着大叔。
“坎子叔,我家雀雀丢了!两天没回来呢!”这雀雀是小乐都养的大黑狗,它还有个孪生兄弟叫豆豆,长得一个模样。
“嘿呀,明儿就入冬了,该不会给哪家看上了,请它进汤锅了吧?”坎子大叔扛着锄头,笑呵呵的逗趣乐都。
“啊!天呐坎子叔,你看见了!哪家啊?雀雀不好吃的!”这么一逗小乐都却着急了,玻璃里的泪水全淌出来,哭得更凶了。
“你个球货,看把孩子闹得,走!”一边的檐子婶拿锄把敲了一下坎子的脑门,又踹他一脚,“乐都不着急哈,肯定是去别的村找老婆去了,说不定回来就给你带好几只小崽子呢!”
“真的吗婶婶?”乐都听了好些,瞪着大眼睛问檐子婶。
“那可不,快回去吧,等两天就回来了。”
“嗯!婶婶忙吧!”
“好呀,亲婶婶一口呗。”
小乐都笑咧咧的跳过去,垫着脚亲了亲檐子婶。
“小乐都,也给大叔亲亲呀。”
“我不亲坎子叔,坎子叔讨厌!”小乐都揪起嘴巴,哼哼地扭过头就跑回院子去了。逗得两夫妻乐呵好一阵。
乐都脸上还包着眼泪,但只要豆豆和他玩起来,眼泪很快就干掉了。这时候他的娘亲从屋里走出来,手里裹着两个豆糕。
“锋儿,来,娘刚做了一笼豆糕。”
“豆糕!”
“烫喔,刚蒸的。”
“太好吃了!”
“快吃吧,吃完还有,我给你爹留两个。”
等母亲走进去,小乐都赶紧掰成两半,一半塞进了衣兜里,另一边丢给了豆豆。
“傻豆豆,别馋哈,等雀雀回来我要留给它的!”
小乐都真是少数孩子里能让人安心的,孩子气使然,却不让人生厌,眼神里都是纯真朴善。村子里差不多人都认识这个头发蓬松的紫黑皮肤孩子,是公认的可爱娃娃。
唯独西山老宅那边,初春刚搬过来的一户补阙,虽为人和善,却总在私下遇到小孩时表现嫌恶,包括乐都。这不,小乐都唤着豆豆在田坎上跑闹时又被补阙府上的小儿子看见了。
这小儿子正带着随从四处闲逛,精嫩的脸皮透着几簇红润,嘴却咧得老大。眼看排沟跑过来一人一狗,眼睛也瞪大了。
“温叔,昨日爹爹可有打了一条狗做了宴?”
“是的少爷。”
“天,真够怪的,你看那条像不像昨日的畜生?”
“哟,少爷,小的眼睛早就腐朽,看不得大貌,却也像极。”
“呀,真是撞了邪乎,我莫不是没吃狗肉,昨日的滋味都是梦噫!”
这补阙姓袁,膝下一子,名作沉甫,意在静心。袁沉甫昨日吃了一顿好餐,本是荒村野寨,撒泼了些时日,都在抱怨此处吃食甚少,没个馋嘴地方。昨日父亲就带回来这么一条健硕畜生,那犬牙尖目极,一看就没少吃荤,村里畜生少,也没人舍得杀肉喂狗,这定是荒山补野吃得膘肥体壮。
厨下婆婆烧得一手好菜,狗肉分作五份,炖煮烧炒妙不可言。袁沉甫享得好滋味,最晚还做了一夜美梦。今天竟又看见田坎上跑来这么一条,他忽怀疑自己昨夜是否真吃了顿狗餐。
等那孩子从远处跑过来,看见这两人鞠了一躬,带着狗又跑开了,他更混沌般抠了脑门。
“我定是馋糊涂了,温叔,昨日我们当真是吃了狗肉?”
“呀,小少爷,主家吃什么我倒不知道,但小的是定没闻见肉香。”这温叔乃一下人,主家吃什么酸甜苦辣定没他的份,昨日他正柴房调戏那掌厨的婆娘,倒也亲眼看见这女的怎么烧菜,想偷吃不成,倒是香味折磨他一晚上,尽早晨起口水都溜了一地。袁沉甫问他,他当是一脑子不满。
“那定是没吃过的,温叔我馋了,要不买下来,今天解我昨晚上的美梦吧。”看着那孩子逗着狗越跑越远,袁沉甫着急起来,也不管是真吃着没吃着,就闹着要温叔给他买下来。
这便是了,小老头就追上去,好歹问了乐都要买他的狗。结局想得当然,乐都自是不愿意,不仅不愿,还想到自己这不久刚走丢的雀雀,眼里又包起来泪花。
温叔一看这摊混事,脑壳也就炸了膛,连忙招呼自己不买了不买了,边招呼边往后撤退。可真就罢也不好应付自己的小主子,此袁沉甫当真是板书般的富家孩子,但凡能称作所谓的富家,需要两种满足条件。
一是别人认为他家中富庶,二是此人本身家中调教不算不错,他本人也觉自己富庶,便眼中只有上等人和下等人,自己算上等,在上可攀,在下便不必多说。
所以这孩子就是极为任性且目中无人,其中一分是孩子脾气,剩下九分就都是家中教养了。温叔眼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就愁起来。人中最难做的有三,其一就是这种居于两等的中间人,既不是上等,也不是完全的下等,而是下等的背叛者。
这种中间人有极多脑子,一半用来学着上等人说话,以此应付下等,一半写作下等人说话,用来应付上等。这时候他两半都转起来,转得极快,恰似水中漩涡,把可行的草木败叶都留在表面,那些没用的就冲下去了。
温叔跑回去,低头跟这小主子嘀咕几句,后者乐开了,看来想法不错,是上面的前一半脑子转对门道了。
下午时分,小乐都从田坎上跑回村子,在某大叔家的小赌坊前见着这么个老头,看着颇为眼熟,却仅有映象,似乎最近见过,但思绪不起来。那老头半道就给他截住了,乐都往左他往左,乐都走右边他又堵右边。
等乐都投过去疑惑的眼神,老头笑了,从怀里揪出来一小块麦糖,在乐都眼前晃了两晃,看乐都馋了嘴,温叔笑咪咪的把糖送进了乐都嘴里。
“嘿,娃娃,我们又见着了?”
“甜!爷爷我们见过吗?”乐都砸吧嘴,手指摩擦着鼻子。
温叔一看,这小孩不记得了,笑得更开。
“骇,娃娃你没见过我,我可见过你!”
“啊?你见过我?在哪啊?”
“呀,在梦里哇!昨晚上你还告诉我,你丢了一条狗呢!和这长得一个模样,可是?”
“是呀是呀!老爷爷你托梦吗?那爷爷是不是神仙,能不能帮帮我?帮帮我吧好爷爷,我家雀雀还没回来哩,我袖子里的豆糕都揣黏糊了!”
温叔一听,心里乐开花了,小孩骗起来便这般简单,比之年轻时自己忽悠那些笨蛋更简单 要是现在和自己的主子交道也这么简单就好了。
“嘿,娃娃呀,爷爷倒是想帮你,但奈何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不过爷爷这里有吃的,只奖励给可爱的乖孩子……”
乐都还在馋嘴温叔手里的各式小吃,这时候赌坊里悄悄摸出来几个大汉,看准了门口的黑狗便窝堆地从中间走过去。在小乐都的视线盲区里,老头丢了块冒气的白肉给那畜生。
……
时年六月,江南道洪州下定一位前右补阙。辞官告老,官职不大却得罪甚大,落致家中钱两无几地皮少有。无妨,便是一家老小尚还生动,也就极大的幸事。
六月下,右补阙袁府长子袁沉甫,好个伶俐儿郎,却因贪嘴吃食乡中狗肉染上寒症,体虚阳衰,届时瘟症盛行,果不然命绝七月。
绝命次日,唢呐哀彻白缎高悬,袁某悲从中来,竟也染中疟病,生气日渐衰微。
好歹此村一户了不得的人间,两月之间遭此横祸。袁某回想此前半生仕途,哀伤久绝,八月初便将小儿子袁案,字断泽,连同妻女送往丈人张氏家去。
结果同年十月,袁府果不然惨遭灭门,除当初送走的次子妻女,无一幸免。
但其间还尚发生一事,也即长子袁沉甫死后两月,九月中旬。此时袁大老爷正端坐大堂灶红木椅之上,皱瘪的臀骨并不严谨贴合该木板,且长时左边压力较甚。
堂下跪了一男一女二人,其中女子十分面熟,恰是柳溅锋,也即小乐都的生母杨氏。而一边的男子正跪于当前,腿脚伸直却哆嗦不止。
“老爷,少爷确是吃食狗肉中寒,估摸着该是那狗吃了甚么。此二人便是畜生之主。”
一旁的温叔上前说解。其实真事如何他心中透亮,当初在那赌坊门口,便是他手里那块下狗的毒药用量过多,后文山野中烤制狗肉处理不当,当夜袁沉甫疼痛难忍之时他简直快把床抖烂。
但现在,他一切都安心了。想起来,那狗肉的滋味当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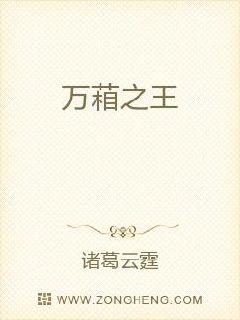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