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来一壶采花毛贼
沅浪和道长说话声音很小,其余众人都没听见,只看到沅浪一副“跟老子没关系”的得意表情和道长一副“我该不该说”的犹豫脸色。
上官盈尺听了沅浪的话之后,好像魔怔了,一会儿面露喜色,一会儿念念有词。
张贤启看了也不明所以,心想“如此说来,这道长难脱嫌疑,这上官公子亦不肯就此罢休,倒是好生为难。”
张灵昭不耐烦地说道:“上官公子,据你和这位道长方才所言,事情虽然是巧合了些,但毕竟无巧不成书。你既没有十分的证据,而且令尊也同意了让道长离开,你这样强人所难未免有些不讲道理。但话又说回来,这位道长毕竟有些嫌疑。你们二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真是比较棘手。”
上官盈尺听张灵昭如此说,见她虽说的圆滑,但她小小年纪聪明机敏,心想或许她真能找到其他线索也未可知,于是说道:“依姑娘所言,此事该如何决断?”
张灵昭狡黠一笑,说道:“依我无知小子所言,这道长并非真凶。”
上官盈尺方才说他们是无知小子,这会儿也不理会他语气中嘲弄之意,脱口说道:“姑娘何以见得?”
张灵昭故作高深,摇头晃脑说道:“此事极易分辨。依你方才所说,尊兄所受乃是剑伤,但这位道长用的却是拂尘。是了,你肯定会说‘道长随处寻一把剑来,杀完人之后又随处弃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那好,这个暂且不说。”
“但反而推之,若是道长杀害尊兄,何以次日要去拜会上官庄主,要知道日间他可是已经与你照过面了,那岂不是‘猪撞南墙,鱼投罗网’吗?”
沅浪听张灵昭说“猪撞南墙,鱼投罗网”,那不是明摆着说这道长是“猪”是“鱼”吗?随即忍不住“嘿嘿”笑了几声。
“小娘们儿,有性格,老子喜欢。”
张灵昭恼这道长方才偷袭无理,恼恨地看了一眼沅浪,继续说道:“若要说道长是故意挑衅示威,那也绝无可能。一来道长与令尊有旧,素无仇怨,二来以道长武功,只怕还没将什么锦绣山庄放在眼里,又何必‘猫闹鼠窝,自娱自乐’呢?”
张贤启此时也听出来妹妹一会儿说道长是猪,一会儿说锦绣山庄是鼠窝,连忙说道:“妹妹,不可无理。”
那道长听完张灵昭所说,只是微笑以对,上官盈尺却已面现不悦,怒目而视。
张贤启此时若再任由妹妹说下去,怕是要引起不必要的争端,急忙站出来说道:“舍妹顽皮,言语上多有得罪,还望道长和上官公子不要与她一般见识。但舍妹方才所言并非全无道理,还望上官公子三思而行,好尽快找出真凶,为尊兄报仇。”
上官盈尺虽恼恨张灵昭说他锦绣山庄是鼠窝,但听她方才所言,竟一时语塞,加之刚才沅浪说杀人凶手可能是姑苏慕容,心下意识到自己怕是真的误会了道长。
但他毕竟年少气盛,不愿当场自认其非。
思之再三,对那道长抱拳说道:“道长,今日在下多有冒犯,实属不该。但兄长惨死,此事一日不了,道长也终一日不能洗脱嫌疑,在下会继续查找真凶,后会有期。”
上官盈尺说着,又向沅浪抱拳道:“多谢沅少侠相助,若姑苏慕容真是杀害兄长的凶手,那时在下再来拜谢。”
“额,这就走了。姑苏慕容很厉害的,而且神出鬼没,喜欢把自己埋在墓里装死,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
“杀兄之仇,不共戴天!就算对手再厉害,我要将他碎尸万段,为兄长报仇。”
上官盈尺说完,也不再理会沅浪,对着那帮仆从说了声“我们走”,然后跨上马疾驰而去。
“这公子哥儿,一看就不知道什么是江湖。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事人情世故。损色!”
沅浪完全没意识到自己骗人不对,反而对上官盈尺这种江湖小白嗤之以鼻。
那道长见张灵昭三言两语便将上官盈尺打发走了,心下甚是高兴,对三人说道:“今日,贫道要多谢三位小友了。若三位不嫌弃,不妨随贫道到武当山一叙,贫道也当略尽地主之谊。”
张灵昭不无鄙夷说道:“原来你这道长却是武当山的,真是见面不如闻名。”
张贤启忙对道长说道:“道长莫怪,我兄妹二人初到贵地,人生地不熟,冒昧造访恐多有打扰。今日结识道长,已是三生有幸,敢问道长仙号?”
那道长说道:“好说好说,贫道俞莲舟。”
“我勒个去,你就是俞莲舟,额不是,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俞二侠?”
俞莲舟看着沅浪惊讶的表情,随即说道:“正是贫道。”
张贤启与张灵昭对视一眼,既喜且惊道:“原来道长便是武当俞二侠,却不知我……贵派掌门如今可好?”
俞莲舟沉吟良久,似是伤心难过,良久不语。
“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张三丰都百岁高龄了。现在你俩都十六岁了,张三丰估计早就位列仙班了吧。”沅浪看俞莲舟的深情,心中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张贤启也意识到问题,自忖如此问得未免唐突,只好说:“只因我兄妹二人素来仰慕张掌门仙风道骨,是以问之。”
俞莲舟声调迟缓又略带愤恨说道:“师父他早已仙逝。”
张贤启和张灵昭听闻之后,也不禁心下难过,只听俞莲舟说道:“方才贫道一直心中疑虑,不知哪位高人手下调教出二位少年英雄,敢问二位小友师从何人,父母是谁?”
张贤启本待要说“家父便是张无忌”,却见张灵昭向他微微摇头,他知妹妹自来机敏,便即讷口不言。
沅浪看在眼里,心想:“张三丰的死恐怕和赵敏有关。这小丫头心思精灵的很。”
俞莲舟见他二人情形,便知其中必有隐情,但他本就与这兄妹二人素不相识,此时倒也不便强求。
他阅历既深,知道张贤启虽是武功不错,但心思单纯,日后行走江湖恐怕要吃些苦头。
于是说道:“既然二位小友不便相告,贫道也就不强人所难了。只是如今这世道人心险恶,二位小友虽武功不弱,但日后行走江湖也要多加小心。”
俞莲舟转而又对沅浪说道:“沅小友,贫道今日与你相识,颇有些相见恨晚,想请几位小友到武当山上盘桓数日,不知老道可有这个荣幸。”
“道长何必客气,我等三人今日能结识道长也是三生有幸,本来无论如何要到山上叨扰数日,以表我等崇拜之情。可是,这两位小张还有要事在身,小可也不能丢下他们二人,独自上山,所以只好驳了道长的面子了。”
沅浪也学着道长回话,心中想着:“这老道肯定是别有用心,是了,肯定是觊觎我的三花聚顶,老子才不上当呢。”
俞莲舟听这沅浪文绉绉的回答,一时竟不能适应,只好说道:“那也是缘分使然,如此只好后会有期了。沅小友三花聚顶尚在初窥之境,且体内真气未能融会贯通,要记得每日子时、午时修习太极御气之术,假以时日,必有裨益。”
说罢,翻身上那骡子背上,依旧端坐不动,闭目不视,右手拂尘朝骡子屁股上轻轻一拂,那骡子嘶鸣一声,便得得向前行去。
待得一人一骡渐行渐远,消失在远处秋木掩映中。
沅浪吹了声口哨:“以为骑了头驴就是张果老了?装什么高人!”
张贤启对沅浪说道:“沅兄,我觉得俞道长说的对,你要勤加修炼,不然还要忍受那真气之苦。”
“好吧,老道长走了,又来个小道长!”
张贤启看沅浪对他的话并不在意,只好转头对张灵昭说道:“妹妹不是说要去武当山吗?何故方才又对我摇头?倘若说将出爹爹名讳,不正好与这位二师公相认?”
张灵昭看着哥哥一脸诚挚又疑惑的表情,叹口气说道:“哥哥当真是糊涂,怪不得爹娘时常说你仁心太过。你不见方才这位二师公说起曾师公仙逝时,脸上是何表情?”
张贤启听妹妹如此说,回想了一下,说道:“啊。我想起来了,这位二师公初时似乎很是心痛,但后来语气中略带些愤恨之意,却不知为何。”
沅浪在一旁听不下去了。“你这个猪脑袋,跟小……这位美女差远了。张三丰的死肯定与你娘有关,我猜八九不离十是因为身受假空相的金刚般若掌伤了元气。你这位二师公可是把你娘当成仇人了。”
张灵昭白了沅浪一眼,随即说道:“正是如此,而且武当派素来自称名门正派,不屑与朝廷为伍。娘亲当时是汝阳王的郡主,又多次与武林各大门派为难,故大家都说爹爹是为娘所惑,素来是不接受娘亲的。”
“更何况,爹娘自离开武当山已有十六年之久,杳无音信。此时你我贸然认亲,别说这位二师公是心思深沉之人,断然不会相信。即便他相信你我身世,在那武当山上,既无曾师公庇护,又无爹娘从中斡旋。”
“你我无半个相熟之人,人人对我既是怨恨,又是疑忌。那时行事岂非处处掣肘,甚至被当成过街老鼠亦有可能。届时要再行下山,只怕恐非易事了。”
张贤启恍然大悟,对二人的一番言论甚是佩服,说道:“还是你们二人想的周全,方才是我鲁莽,竟差点自献囹圄。既然如此,上武当山之事再从长计议吧。”
“谁和他‘你们二人’!”张灵昭唾弃道。
“额,这小娘们儿聪明是聪明,就是脾气太臭。”沅浪只敢在心中腹诽。
说罢,三人又休息了片刻,这才站起身来,向山下走去。
三人在山路上行了约半个时辰,将近山脚,隐约便见前方数里处一杆旧旗招展,隔得太远,看不清旗上所书何字,想来必是官道上给过路行人歇脚的茶肆。
张灵昭初次下山,极是兴奋,一路上欢快喜悦,此时更是童心大盛,对张贤启说道:“哥哥,左右无事,不妨我们比比轻功如何?看谁先到前面那旗子处。”
张贤启看看天色渐晚,须在天黑前找到歇脚之地,便微微一笑,说道:“好,妹妹输了可不许哭鼻子。”
“喂,你们太欺负人了吧?明知道老子不会武功,这也太能炫耀了吧!”沅浪哭丧着脸说道。
张灵昭做个鬼脸,抢先一步展开轻功向前奔去
张贤启对沅浪说道:“沅兄,轻功其时也不难,你运气把真气通过经脉灌输到腿上,然后用力跑就行。”说完,也不管他听没听懂,展开轻功向前追去。
“我靠!你们两个小屁孩儿,看我追上不打你们屁股。”沅浪一边说一边跑起来。
张灵昭在前面听到沅浪说要打自己屁股,心中一急差点运气不畅,立即调整情愫,这才稳住心神。
初时张贤启落在后面,只过了一会儿,便已然和张灵昭并肩而行。沅浪一开始完全不掌握运气下行的方法,只顾着猛跑。
说来奇怪,虽然奔跑迅速,但是并不觉得累。他心里高兴,边跑边开始试着运气,果然慢慢的觉得一丝真气向腿上行去,跑起来就更觉得有劲了。
所谓轻功,比的无非就是内力。张贤启有九阳神功护体,内力循环往复,无复生有,可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沅浪虽然不掌握运气精髓,但勉强能催动少量真气行向腿部经脉,虽然速度不快,但耐力长久。
张灵昭内力本来就偏弱,若是在短程之内,尚可仗着先机取胜,但时间一长内力消耗渐巨,自然就后继乏力了。
将到茶肆时,张贤启有心要让着妹妹,便放慢了脚程,张灵昭也毫不客气,一个蜻蜓点水,左脚用力,轻身飞起,落在张贤启前面,然后转过身来,笑着对着张贤启说道:“哥哥,可是你输了?”
张贤启也停下脚步,故作佩服之态道:“张女侠轻功天下无双,在下佩服。”
张灵昭“咯咯”一笑,看那茶肆边上放着几张桌子,有几个客商模样的人坐在那里喝茶歇脚,旁边停放着几辆货车,也有马拉的,也有人力的。她便抢先在靠里一张桌子边上坐下,喊了一声“伙计!”。
只听茶肆里传出一声“来嘞”,便见一个茶倌从茶肆里面走出来。
“呼哧呼哧!你们……你们太不讲江湖道义了,竟然欺负我一个老家伙!”沅浪气喘吁吁的来到茶肆,弯着腰一阵牢骚。
茶倌看着沅浪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竟然自称是老家伙,着实觉得好笑。
但他也没表现出来,一脸堆笑说道:“二位少侠,本店有上好的采花毛尖、白毫绿羽,请问要喝点什么?”
张贤启忙抱拳,说道:“这位小哥,我们不是来喝茶的,就是想问一下,从这里到最近的客栈还有多远?”
那茶倌听闻二人并不是来喝茶的,心下便有些不悦。“少侠,我就是个跑趟的伙计,对这附近也不熟。”
沅浪一看这情形,说道:“老一壶上好的……什么采花毛贼!”
“额,少侠,是采花毛尖。”茶倌便擦汗便纠正道。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采花毛贼,来一壶!”
茶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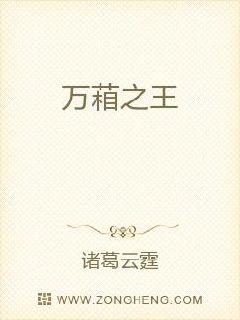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