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寒白屋贫
五十年前,皇城外。
夜色如水,照万物肃杀,金戈声寒。
王无鸣抖擞银甲,白雪覆兜鍪,三尺长剑映着他那倜傥面庞,只不过那寄生在额角的方形刺青却扎眼得过分——倘若不是那昏君听信谗言,以大不敬罪诛了他九族、判他流放鄂城,那他现在便该是一名安邦的虎将,而非揭竿的逆贼。
昏君圣旨断死生,那日王无鸣跪立囚车,往来白丁以目相送,半幅囚衣明净,今时昏君端坐龙椅,殿下臣子不敢昂首,一身龙袍龌龊。
王无鸣本该命绝于此,可昏君也万万没有想到王无鸣的那些江湖朋友竟敢光天化日劫了囚车、杀了他钦点的护卫高手,不过他并不关心,因为他知道王无鸣乃是忠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可是呢,王无鸣也是走江湖的,朝廷再大,也是江湖。
“大哥,待弟兄们解决那些禁军,你只管杀将进那金銮殿,取了那狗皇帝性命便是!”陆弈天长枪在手,枪刃迎雪展霜华。
“狗皇帝杀是该杀,可他无子无孙,杀了他天下必定大乱,倘若冀国趁虚而入,恐生灵涂炭。”张虎鹤感喟,目光投向银甲白马的王无鸣。
“驾!做皇帝这事不如让给大哥,二哥四哥你们只管站在那破殿外当个人见人怕的门神,洒家呢,便接了那混账丞相的职,管教我大业国海晏河清!”骤雪天打着赤膊的乃是赵人屠,他豪迈一笑,浑身筋肉活脱一副抛光上蜡的古铜铠甲,他的铁布衫已臻于化境,就连这雪花也近不得他身。
“你这厮啊,此般无赖秉性怕以后没人敢与你说媒!驾!”陆弈天扬鞭,胯下白马一声长嘶,蹄子笃笃踏碎了满城的白雪。
“呔,洒家练得乃是童子功,二哥你若要我娶甚么老婆,莫怪洒家翻脸无情!”赵人屠不满,一袭黑衣劈开风雪,怀里是那捂得滚烫的酒葫芦,酒葫芦里装的是全鄂城最好的竹叶青。
“六哥,这酒不在道上喝暖身子,留着去皇城作甚?”展诗不解,作为队伍里唯一一名女侠,她的酒量倒是天下无双,因而囊带的酒也没的最快,况且赵人屠的酒葫芦盖得不紧,阵阵酒香早就杀进了她的鼻腔,在她看来,那赵人屠分明是想吊着她的胃口,其心可诛!
“等杀了那昏君,洒家拿这酒和弟兄们一起喝,你这丫头自然有份!”赵人屠眉山锁起,倔强如幼儿,平日众侠客最爱拿他打趣,不过打趣之外更是敬重有加。
“这哪里分的了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可就没啦!”展诗目不转睛盯着那美酒,半天肚子才叽里咕噜发出一阵怪叫,酒虫上脑。
“到时候少不了你这丫头的!”赵人屠大笑,此刻众人已经隐约窥得那京城巍峨的城墙,上面有着旗子,有着昏昏欲睡的卫兵,偌大的军鼓堆满积雪,晦暗的篝火摇摇欲灭。
行至城外百米,众人翻身下马,张虎鹤弯弓走箭,六发流矢没于风雪,箭声破空龙吟,三发封喉,两发掀灭篝火,一发破了军鼓,以此为号,众人打点行头,轻功好的踏墙而上,轻功不好的飞爪铁索攀瓦当,那天的雪下得像着了魔,五十甲士雪夜入京城。
“王...”巡逻的斥候话未脱口,他的声音便随那漏风的嗓子化作了风雪里的喧嚣,展诗拔剑,顺势斫下另一名斥候的头颅,她的剑法并无所谓招式,野蛮任性,随心而动,是为天山忘忧剑。
“不过如此!”陆弈天大笑,面对三名精兵的围攻,他只是一个鹞子翻身避开锋芒,虎虎生风舞起那杆沥泉枪,那三名精兵中最为健壮者举盾欲将那凌厉的枪刃格住,可陆弈天一记回马枪扎来,壮汉却连人带盾被捅了个对穿,他死抱枪杆,嘴里鲜血井喷,好不惨烈,另外两名精兵趁机近身,但陆弈天只是一声冷笑,借着内功运力,左手一抖枪身便将那壮汉整个人如同劈柴般劈做了两瓣,枪还未落,陆弈天一记扫堂踢翻一名兵士,借着他的朴刀“叮当”一声格住了另一名兵士的劈砍,转而以双手擒拿,将他们两个径直扔下了城楼。
陆弈天左足勾起银枪,英姿焕发。
官兵作鸟兽散,被称为乌合之众的江湖侠客们竟一路杀到了金銮殿门前,彼时日出东方,天降祥云,城北有瑞兽踏雪,那是为陆弈天算卦的老天师骑着麒麟来给新君开天眼。
“昏君受死!”王无鸣嘶吼,那昏君正端坐龙椅,死到临头却睥睨众生。
十几名侠客鱼贯而入,张虎鹤弦惊霹雳,飞矢以那雷霆万钧之势直取那昏君眉心而去,这一箭就算赵人屠来接尚且九死一生,况且这四体不勤的皇帝,但说时迟那时快,一抹拂尘扫来,那刁钻的箭矢却被结结实实弹了回去,张虎鹤躲闪不及,只见那白刃穿过胸口变作了红刃,直挺挺飞出百十米射入了华表柱,摇曳的血迹像是从张虎鹤身子里牵出的一条红绳,彼时张虎鹤筋脉逆流早已没了活命的可能,他只是大呼一声过瘾,握紧陆弈天的右手便含笑而逝。
与此同时,冲入金銮殿的十几名侠士也已肝脑涂地,昏君冷笑,胜券已操。
“冬荣子?”王无鸣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那冬荣子乃是当朝国师,更是千年一遇的武学鬼才,据说他的修为已不亚于那神秘莫测的老天师了。
赵人屠早已气得吹胡子瞪眼,他胸脯一拍,摆好架势冲向冬荣子,但那拂尘却毒蛇般绕住了他的铁臂,只是一翻一拍,人屠铁塔的身躯竟像蹴鞠般飞出了大殿之外。
又有二十几名侠客冲入大殿,趁着混战,陆弈天一记金蛇吐信将长枪踢向昏君,但冬荣子却拽住一名使铁拐的侠客,向上一掷便替那昏君挡了枪,众侠士前赴后继,使流星锤的锤子被捏了个稀碎,脑袋被不知从哪儿来的金瓜砸扁;使关刀的关刀被一折两段,胸膛不知被从哪儿刺来的长戟贯穿;使暗器的向昏君扔去无数暗器,毫无死角的攻势却被那拂尘一卷,转身扫倒了一片自己人......
冬荣子道袍浴血作红裳,白须斑驳若地狱修罗,好一个拱手作揖,满脸皆是荒唐的礼让谦逊。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杀了冬荣子,不过有人猜他们是以冬荣子的徒弟风云侯做了要挟,那么其他的侠客呢?人们只知道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人说他们被永远埋在了那场大雪里,也有人说他们功成身退,更有人道兔死狗烹。
猜的半对半错,真相唯有黄泉下的故人知晓。
可故人何在?
“二弟...你投我以江湖,我报你以江山。”王无鸣撒手人寰,龙椅上的昏君早已吓得面无血色。
“二哥,以后难道要叫你陛下了吗?”赵人屠跪坐在地,铁打的汉子泣不成声。
“朝堂上是,江湖上我仍是你二哥。”陆弈天浅笑,他与赵人屠对坐,膝下血海早已冻得硬邦。
“二哥喝酒!”赵人屠一声咆哮,取下酒葫芦拍在了陆弈天怀里,他双手一捧,好似酒樽。
“好!”陆弈天两行清泪如溪,他卸甲见白衣,一手接过葫芦,痛饮一口便将清冽的酒水斟满了人屠的手掌。
“好酒!可惜不是女儿红!”人屠苦笑,一饮而尽。
“待你七十大寿,二哥亲自为你斟满女儿红!”
那日以后陆弈天被关在了那贫寒的金銮宝殿,但那殿上的雪却下了整整五十年,它们未曾消融,直至染白了大业国的江湖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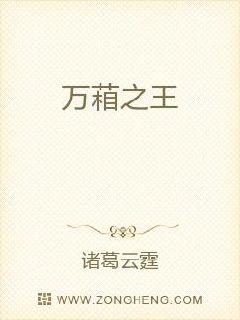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