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半卷别离,难言欢笑,半卷痴惘,难言放下。弹指间,匆匆的时光便已经过去,一艘画舫轻波临江,荡开阵阵涟漪,船桨一划再划,前浪方驱,后浪又趋,但船上的人似乎并不在意,也并未加快速度,就这么慢慢地停了下来。
江畔两旁,各自建有几座阁楼,皆是甘府的产业,用作闲时玩乐之所。此时门扉未掩,内中光景提映着灯火,酒色之气混着觥筹之声,笑语喧哗,交错传来。甘之饴轻轻地叹了口气,再过三个多月,玄素问鼎即将开始,届时,临安城将会选拔出新任城主,自己非被老爹逼着参加不可。但他一来并不想参加这种打打杀杀的比斗,二来他觉得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到时候老爹要是不管事,撂挑子给自己,他一定会累死,三来自己也并没有把握能赢,那就很尴尬……听说到时候会来观礼的人可不少,自己如此少年,怎好丢脸?甘之饴内心腹诽了半天,觉得问题还是出在羊身上,自己不过一根羊毛,就算落在这临安江水里,分量不够,照样沉不下去。说不定来一阵大风,刮折了面子不说,自己这根羊毛还得被吹成分岔。
想到此处,甘之饴忍不住打了个哆嗦,抬头一看,虽然天色已晚,看不出阴晴,但黑漆漆的,像是要下雨了。
阁楼临江而建,高有十五六丈,伸手推开窗户,水殿风烟轻送,细雨微调,浮光从影壁中掠过,跃动点滴烛火,虽是飘摇,却也有一派气象。甘之饴怔怔的看了半天,心道这雨真是不知时节,当春不下,现今已是暮春,反下如此小雨,显得糊弄之极。而且早不下晚不下,偏偏在自己心情郁闷的时候下,更显得不知好歹,使人置气。转头看了看另一栋阁楼,依旧灯火通明,推杯换盏之声不绝于耳,听起来非常热闹。这么一对比,自己这间阁楼冷清的就像冬天的月亮照在枯井里一样……连结个冰都是奢侈妄想。甘之饴心中忿忿不平,凭什么老爹在那里吃吃喝喝,让自己在这里静修,说什么问鼎之期将近,自己需得勤修苦练,不可有半点懈怠,方能精进修为,取胜才有把握云云。扯淡,甘之饴听人家说要求别人做一件事情都是用奖励法,怎么轮到自己就变成了“虐待”法?让驴上磨还不许驴打滚,简直是岂有此理!甘之饴越想越气,一声长啸,纵步踏出,临水平波,使开家传的《覆雨掌法》,就这么发泄起来。
打了几招后,便渐渐感到无聊,叹了口气,右掌一起,左掌横挥,劲力自下而上,水面乍生一道漩涡,双掌一翻一合一分,口中喝道:“江河倒悬。”一道掌力印下,劈开江面,两旁卷起狂涛,掌力却径直向下,狂涛如击,势若雷霆奔马,乘风蹈海。这一式乃是他家传《覆雨掌法》羁式中的厉害一着,掌起羁绊,使敌不能行动自如,而后掀起周遭山石土木,合围敌人,同时一掌直下,使敌上下左右四面受敌,既是取胜高招,亦不失为脱身妙法。此刻临江施展,威力更胜。一招使毕,其势未尽,涛浪径直卷向数十丈开外的一艘画船,势头凶猛,那画船甚小,俨然无法与之相抗。甘之饴心下大惊,暗道:“不好。”急欲救援,却不想一时忙乱,内息行岔了道,水面上不似平地,内息一岔,轻身功夫立时不稳,扑通一声,落进水中,眼睁睁看着那涛浪向画船卷去。
涛浪卷至,却见那画船轻若无物,竟似无从受力,随波而起,上下其浮,涛浪袭卷,浑然不觉。甘之饴瞅见,心下一呆,顾不得跃出水面,手足四肢并用,向那画船游去。
“甘老爷,令郎年纪虽轻,但少年英雄,武功修为已是不俗,且亦心性坚韧,兼之……嘿嘿,玉树临风,这临安城的各家闺秀可都盼着呢。”“若是能于玄素问鼎之上夺魁,甘老爷就是这临安城主,到那时候,只怕前来说亲的人会把门槛都踏破了呀。”“哈哈哈哈,刘姥姥,你这红线的生意到是好做。线牵一根,便栓两头,轿桥一搭,这银子就入账了啊。”“不过,犬子尚且年幼,婚配之事倒不用操之过急,呵呵,今日乘兴,不如大家一起喝个痛快,不醉不归啊,哈哈哈。”“甘老爷,今日既是乘兴,如何不叫令公子出来与我们见见,一起畅怀一番啊。我们也好领略一下令公子的少年英姿,冲霄意气啊,哈哈哈哈。”“诶,林兄弟此言差矣,犬子年少,当不得这般夸赞,若是于诸位面前失了礼数,岂不是贻笑大方嘛。何况少年人酒量有限,远不如诸位千杯不醉,与其叫他出来献丑,扫了大家喝酒的豪兴,那在下可真是过意不去啊,哈哈。”酒过三五巡,众人见甘之饴始终不出,心中暗骂:“甘林泉这个老滑头,左推右脱就是不让甘之饴出来,可若是不能摸清这甘之饴的底细,玄素问鼎对阵之时,未免难判虚实,对自家可不是什么好事,毕竟事关新任城主之位,且听说临安城地下赌坊对此次比斗下了大注,那白花花的银子谁不想捞一笔?可若是只知己不知彼,取胜夺魁尚且不说,这赌本一旦下错,只怕便是万劫不复啊。”
众人各怀心思,鬼胎暗算,诸般计较,皆是自谋利益,言语如机,非要逼出甘之饴不可。“甘老爷,听闻令公子饱读诗书,又鉴于丹青,博识广扩,在下不才,藏有一幅兰亭书圣躬身亲作的《写意江山图》,听闻观此图者,隐可见书圣绝代风华,若是能于其中感悟而提升修为,甚至破境也犹未可知。只是在下资质愚钝,观摩多次也未能有丝毫收获,不知甘老爷可否让令公子为我们大家品鉴解识一番呐,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说着缓缓从一个精铁所制的箱子中抽出一幅画卷,长约四尺,其上有龙章凤篆,刻有“兰亭”二字。“写意江山,如临烟雨。”八个字苍劲沉雄,笔走龙蛇,却又有一种跃然其上,扑面而来的飘逸之感。不过一幅小小的画卷,竟压住众人气息,目视之下,口不能言,神为之夺。
书圣之作登堂,众人初是讶异,而后面上浮现玩味之意,心道:“王尴尬居然把这幅画拿了出来,这下任你甘林泉如何老奸巨猾,再要推诿,恐怕没那么容易。”甘林泉闻言一呆,然后看见王尴尬缓缓抽出画卷,先是一愣,继而心中怒涛奔腾,暗暗咒骂:“好你个王尴尬,我道是个什么东西,原来又是这破玩意,十年前上任城主期选之前,你就用这画卷将人逼出来试探底细,现在又来故技重施,虽是书圣亲作不假,但谁不知道这画只是一幅山水远景,并非武学秘籍,你却借书圣名头,以提升境界修为叫人推脱不得,真真是气恼之极。”自己恨不得上去一把将这画撕了,再也看不见的好。但此间大庭广众之下不好发作,众人又是沆瀣一气,幸灾乐祸的要让饴儿出来品鉴。甘林泉心下着恼,不过碍于众人之意和书圣名头,却也委实犯难,正欲说几句话遮掩过去,突然阁楼下传来一道声音:“王尴尬,你这幅画看了没有半辈子,也有三十年,既然这么多年都看不出奥妙所在,不如索性大方些,让出来纳入临安城的武库,若是将来有人能参悟其中奥妙,也算你泽惠后代,不失为一件功德美事。如何啊?”众人闻听此语,齐声拱首,道:“见过城主。”王尴尬欲语不能,一张脸涨如猪肝,腮边酱出紫红,显得极为尴尬。
来人正是现任临安城城主周褚,约莫五十来岁,一张方脸,粗眉突颧,鹰鼻钩目,胡须略飘。正自拾阶而上,身后跟着一个十六七岁的黑衣少年,便是周褚的二儿子周围,传闻他武学天赋颇高,昔年曾被梦溪楼的楼主沈存中传了一部《清霜剑法》,亦为此次玄素问鼎的话题人物。
周褚入席,先是瞟了一眼王尴尬,见他唯唯诺诺,不敢言语,一时哑了火,冷哼一声,便不再理他。转头对着甘林泉道:“甘老爷,你既然已经让令郎参加玄素问鼎,总归是要与大家见面的,推三阻四,始终不让他出来,难不成要让他问鼎当天才现身?”“这又不是嫁姑娘,我们大家好奇,见上一面又有何妨?”甘林泉正打算说甘之饴其实就在旁边的那栋阁楼,心中却道:“不想让你们过去主要是因为过于冷清,这小子现在应该正在气我让他去参加玄素问鼎,一张臭脸不知道拉的多长,让他出来我岂不是非常尴尬,而且你们嘴上说的好听,万一要切磋,这小子心中不忿,出手之时故意打坏家具,我不是给自己添堵吗?”便说道:“今日已晚,饴儿……”话未说完,只见周围上前一步,气发丹田,纵声高喝:“闻名不如见面,甘公子,周围向你请教,何不现身相见。”这一喝清亮有劲,声闻数里,众人各自震惊,突然,窗外传来砰的一声,似是有什么东西被击中,而后“哎哟”,“哎哟”个不停,踏水之声连连,直退百丈有余。周围一个翻身出去,片刻起落,便已经踏在湖面,抬头一看,一人峭立烟波,衣带当风,眉目如星,含光望水,神逸飘飘,正是甘之饴。只是此刻这位甘公子气息浮夸,立于湖面潮湿却一直到了腿肚,一呼一吸之间有些不稳,湖水径没脚背,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狼狈。
甘之饴手足并用,四肢划水,像那画船游去,不知是因为下雨的缘故,还是湖水太冷,甘之饴身在水中,不时打几个喷嚏。离船三尺,甘之饴从水中跃起,翻身而上,内力运转,烘干衣裳,再行几个周天,驱散寒意,一整衣摆,掀开帷帐,走了进去。
画船内空间并不算大,摆设简单,高不过丈余,宽容三四人横行,帘幕并未卷起,窗扇却是打开,风从外面透入,拂过线珠,轻动玲珑之声。
甘之饴心道这画船虽然布局简单,但竟然空无一人,未免有些古怪。但他本意致歉,此刻既然已经上船,若是内中有人,自己转头就走,好像也说不过去,微一沉吟,便继续向前。方才在湖面施展掌法,并未在意,后又是游水而来,未窥全貌,不想这画船虽是不大,前后倒是颇有长度,直行了七八丈,见一三阶小梯,帘幕后掩映着一扇小门,原浆木色,未作雕饰,平平无奇。镂空的地方以锦缎做面,针脚极细极密,薄过蝉翼,隐约可见。内中烛火轻轻摆动,似有人影,檀香一线,正从其间悠悠飘散。
甘之饴双手一拱,向内中道:“在下甘之饴,呃……适才风波纯属意外,并非刻意而为,打扰到阁下很是不好意思,前来致歉,还望海涵。”但听内中一人声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介意。”甘之饴闻言一呆,却听内中那人继续道:“我并没有什么怪罪的意思,想来不过是无心之举,致歉倒也不必。”“我倒是好奇,这大晚上凄风冷雨的,你在湖面上拳打脚踢,是在干什么?”话音刚落,只听咿呀一声,舫门轻开,檀香如烟,扑面而来。一个人坐在桌子后面,说道:“拒之门外,非为待客之道,请进。”甘之饴一拱手,掀开帘幕,走了进去。左右首皆有一扇舷窗,右首那扇并未打开,下面放有一条长方盒子,碧色青烟飘摇,湖面风从窗纸上穿过,将青烟渐渐吹开。左首舷窗下放了一张古琴,像是新制不久,墨色玄首,琴弦却是红色,离桌甚远,看起来没什么用。舷窗半开,细雨斜斜的打在窗面上,沙沙作响。那人背后是一张床榻,舫门两边各有一根立柱,但上面也并未安置什么花草,就这么放在那。面前是一张矮脚方桌,一个水壶,几个杯子,空空如也。那人坐在桌子后面,说道:“这船上就我一人,外面看那划水的船桨不过是个小把戏,显得人多些罢了。”甘之饴挠了挠头,说道:“可依我看来,阁下你也不像个热闹的人啊……”那人哈哈一笑,说道:“主要是因为这船买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也不好把船桨扔了说少付些银子,就这么将就着装个模样。”甘之饴登时语塞,心道:“你看起来不过比我大了五六岁,怎么和我那个老爹一样不靠谱。”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只好剧烈咳嗽起来。边咳嗽边说道:“不知阁下如何称呼,敢问这是什么香?忒得呛人。”
那人道:“我叫,嗯……你可以称呼在下宋蒙,此香名为“虚传”,乃是以青埂峰下东北阴凉处所产的艾叶混合南疆天方夜谭的昙花制成,没什么用,无非香味清远,比一般檀香经久些,虽然比不上莲华不染的正宗佛檀香,不过拿来送人,倒也看得过去。”甘之饴哦了一声,随口胡诌道:“原来如此,在下不明就里,唐突了,这香果然如同宋兄所言,的确香味清远,沁人心脾,难得一见。”“不知这香是何人所制?”“正是在下。”甘之饴忽地猛烈咳嗽起来,就像吃鱼的时候被鱼刺卡到了嗓子,显得非常难受。宋蒙微笑道:“甘兄弟不必如此强忍,若是我换做是你,只怕早已按耐不住吐槽,实在是见笑了。”甘之饴道:“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我只是后悔为什么要问这香是谁制的。”宋蒙道:“既然如此,那喝杯茶吧,这茶名叫“后悔药”,是我刚起的名字,满饮此杯,诸般腹诽,一释冰消。”说罢右手端起水壶,左手持杯,倒了一杯水递给甘之饴,甘之饴伸手接过,口中说道:““后悔药”,这名字听起来不好不坏,虽然明知道只是一杯水,我还是慢慢喝吧。”宋蒙道:“甘兄弟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吗?不过这“后悔药”仅此一杯,下一杯就不叫这个名字了。”甘之饴随口道:“那叫什么名字?”“大梦初醒。”甘之饴叹了口气,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伸手又倒了一杯,说道:“不是我有什么后悔的事情,我只是不想去参加玄素问鼎,但是老爹让我去。我就比较苦恼,所以才在湖上发泄,不曾想打扰了宋兄。”宋蒙哦了一声,说道:“听闻临安城城主十年一换,便是靠这玄素问鼎,聚少年英杰,以问鼎夺魁而定,优胜者还可有机会进入儒释道三教与各大宗派修习。”甘之饴道:“是啊,可是即便不通过玄素问鼎,直接拜师又不是说不行,故此城中人的重心还是放在城主之选上,临安城也很多年没有人进入各派修习了。”宋蒙道:“说的也是,临安城最近一个进入大宗派修习的好像是七十年前王家的一位叔祖,入了兰亭。”“是啊,”甘之饴接口道:“死了三十多年了。”“自那以后,临安城再无一人进入大宗派修习,渐渐的,人们便不再关心能否进入大宗派修习,一心扑在城主期选上。”
宋蒙给自己也倒了一杯水,说道:“人各有异,入眼不同。若是有机会能进入更好的地方修习,人们大都不会拒绝,而入了大宗派修习的人,自然也不会回身再管前事,是以历来临安城的城主期选,几乎少有连任,同时又为各派输送了不少人才。可惜如今,究竟过去。一断一离,便是舍不得,也再难弥留。”甘之饴将水喝完,伸手去拿水壶,说道:“宋兄啊,我看你好像也不是临安城的人氏吧,怎么这么多感慨?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去参加玄素问鼎,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的,春天种种花,夏天拔拔草,秋天捞捞鱼,冬天呢,就窝在被子里睡觉,多好。何况便是修习又当如何,人寿有终,若是想突破寿数限制,起码要修行到十一境清圣境,超凡脱俗。可若是修到了那个境界,你不想管事,就只好隐居避世,身边又没有亲人伙伴可以言语,未免太凄惨了些。若是建立门派,又有无穷无尽的责任,座下虽有弟子,可是老荏新苒,又得几人?到最后,你的生活还是你的生活吗?至于更为玄奥的十二境与十三境,老实说根本没人知道,便是三教道祖和各派圣人也未曾踏足,不过我想,可能也差不多吧。”“宋兄,不瞒你说,我老爹名叫“甘林泉”,这名字呢,是我爷爷起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平淡长久甚幸,甘老林泉是福。我叫甘之饴,大概也是一种继承吧。我爹这大半辈子也确实过的挺平淡的,常安无事,除了偶尔不靠谱。也许是随了这二十年的性子,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非要我去参加玄素问鼎,唉,头疼呀头疼。”“宋兄啊,这第三杯水叫什么名字啊?”
宋蒙怔怔的看着右首半开的舷窗,眼神透出,外面的雨似乎渐渐的停了,雨止风歇,湖面一平如镜,赫见云开雾散,映入淡月疏星,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画船印入水中,轻轻荡漾。宋蒙口中喃喃:“十二境也差不多吗……”忽听甘之饴问第三杯水叫什么名字,便道:“没名字。”甘之饴道:“嗯?没名字?为何前两杯水都有名字,这第三杯水便没有名字?奇怪奇怪。”宋蒙斜睨一眼,说道:“没名字,这第三杯水就叫“没名字”。”说着给自己又倒了一杯水,却并不着急饮下,就这么放在了桌上。交谈良久,甘之饴已经知道他有时候会突然脱线,却没想到这“没名字”就是这第三杯水的名字,实在让人措手不及。甘之饴“咳咳”两声,说道:“啧啧啧,没名字,宋兄,你起名字未免也太随意了些吧。”宋蒙道:“这世间种种,本来就没什么称呼,一切不过是后人附会,用以区分、记述、交流罢了。“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便如你自创了一门功夫,你想叫它什么,当然就可以叫它什么,只要你愿意,叫它阿猫阿狗都可以。这杯水你喝的太快,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来时如去,去时如来。既无所来,何如所去?本就无名,又何必为名呢?”甘之饴闻言,犹如雷劈当场,心道:“我就是说你起名字太随意,你倒给我装起秃驴。”恨不得上去将这装模作样的家伙狠狠揍一顿出气。但想他那能令画船于波涛汹涌之中浑然不觉的高深修为,自己多半不是对手,搞不好还反被他揍一顿,那丢脸可就丢大了。再加上自己现在在这家伙的船上做客,这家伙虽然不时脱线,为人倒是不错,至少陪自己说了说话,不然自己只好一个人待在那冷清的阁楼里面,对着墙壁发牢骚了,想想就觉得孤苦寂寥。而且这水也挺好喝的……清香甘冽,畅快舒爽。念及此处,便悻悻作罢。
甘之饴待心中平复了些许,便说道:“你要是在后面再加上一句“阿弥托福。”我觉得会更有说服力。”宋蒙微笑道:“檀越天生慧根,悟性高超,一语道破玄机,惊醒梦中愚人,果真难得,阿弥托福。难得难得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甘之饴立时起身,双掌合十,向宋蒙拜道:“大师,我悟了。”宋蒙收住笑声,说道:“在下并未剃度,不敢妄称大师。”甘之饴闻言道:“如此说来,师兄乃是带发修行的俗家弟子?”宋蒙道:“正是。”甘之饴啊哟一声,道:“这可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小可亦是带发修行,落脚处名讳上“临”下“安”,其中带发修行者数千余众,师兄可愿开坛讲法,为我等一解疑惑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两人一齐笑了出来。
笑了好一会,甘之饴口渴,拿起水壶,又倒了一杯水,向宋蒙问道:“敢问宋兄,这第四杯水,何名?”“沧海一粟。”“这倒是个不错的名字。”甘之饴仰头一口喝干,将水杯放回桌子上,向宋蒙一拱手,说道:“宋兄,方才我在湖面上施展掌法,但看涛浪卷至,宋兄的画船却轻若无物,随波上下,浑然不觉。不知是何种功夫?那古琴可是宋兄之物?莫非宋兄师承贤风谷,是七贤八俊中的人物?”“非也,”宋蒙说道:“在下并非贤风谷门下弟子,只不过是江湖上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云野鹤罢了,便如同那瀛洲海客,山水遥寄,四方而游。”“四方而游?”“正是,一叶轻舟相伴,走到哪算哪。只不过轻舟太小,我一个人坐着不太舒服,就换了艘大些的画船。”。。。。“那古琴乃是一位前辈赠予,”宋蒙接着说道:“以无用之木制成,名曰“无俗念”,与大多数古琴长三尺六寸五分不同,只有三尺两寸。”宋蒙耸了耸肩,摊手道:“但是我并不会弹,故而放在那,若是将来缘至贤风谷,倒是可以送出去做个人情,也好过在我手中一无用处。”“至于你说的功夫,”宋蒙顿了一顿,道:“其实也没什么稀奇的。”甘之饴哦了一声,好奇道:“不知此话怎讲?”
宋蒙伸手一拂,甘之饴却并未感到有劲力发出,正自纳闷,但听宋蒙道:“你看。”甘之饴目光顺着宋蒙所指之处望去,这一看不要紧,临安江竟然如镜透明,江水中的水草,鱼,虾,螃蟹,贝壳,河蚌,乌龟,树枝,衣服,垃圾,直至江底的淤泥,沉船,礁石,水蛇,极大的怪鱼,甚至不知名的东西,俱都清晰可见。动静之间,浑无所觉,鱼儿觅食,水草飘摇,乌龟懒散,水蛇把自己缠绕在沉船的桅杆上,懒洋洋的盘着,不时吐着信子,一片和谐。甘之饴嘴巴张的非常夸张,便是在此时给他塞个榴莲或者仙人掌进去,只怕他也能一口吞下。约莫过了一顿饭工夫,甘之饴渐渐的回过神来,脖子僵硬地扭动,想要回头,却又不敢回头,艰难地咽了口吐沫,似乎想说些什么,突然大吼一声,纵身而起,从左首半开的舷窗中一个猛子扎进江水中,游目四顾,上下前后左右疯狂游动,换了好几种游泳姿势。但见数千尺深的江水清澈如碧,平时绝无可能一望到底,此刻竟然犹如触手可及,抬头向上看,亦不见水波涌动,就这么直直望去,也无光线折射,两岸的树木,建筑,阁楼,凉亭,山石,草木,乃至停在江面上的各种船只,画舫,皆如亲临。甘之饴看的傻了,一时忘了换气,江水灌入鼻腔,呛的他连连咳嗽,“啵”地一声,跃出水中,停在湖面。临安江水绵延千里,但有目之所及,俱是透明如镜,鱼虾草蟒,自在恰恰。
甘之饴脸上五官扭曲的好似三观崩塌,结结巴巴的道:“这这这……这到底是什么境界……到底是什么功夫……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鬼!我日哟……”宋蒙伸手将舷窗打开,耸了耸肩,说道:“我也不知道,自从数月前我救了一个人,导致功力大损,先前所修武学已经不能再练,就换了一种新学的功法,故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境界。”甘之饴非常想表现出一种看白痴的目光,但不知道这种目光是应该看向宋蒙,还是看向自己。想来想去,甘之饴还是觉得自己比较白痴,不禁叹了一口气。不对,这分明就是宋蒙这只大尾巴狐狸老奸巨猾,把自己骗了,然后故意把自己吓个半死。想到此处,甘之饴极其憋屈,不禁暗骂自己瞎了眼,不仅如此,还上了他的贼船……直气到两个鼻孔,一般儿的出气。。。。。
宋蒙说道:“我可没有骗你,”甘之饴心下更惊,不知是否自己在心里面说的话他竟然也能听见,那自己还想过把他揍一顿。。但听宋蒙续道:“临安江虽然绵延千里,若是透如明镜,那也不过是一眼可见其方的小水潭。”甘之饴听他居然将临安江比作小水潭,直欲翻白眼。“水尤清冽,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鱼儿身在水中,却空无所依,我虽然身处船上,却似浑然,日光也不过印下我的影子,动静俱在我身,任凭外力如何汹涌澎湃,又如何加诸我身?”“我既不动而江水动,动又何动?乃是你发掌击水而动,一动而动,我随江水动而动,便如你所见之一般,画船随波逐流,上下其浮,浑然而无所觉。”甘之饴道:“随波逐流,上下其浮,浑然而无所觉,浑然而无所觉……”宋蒙道:“不错,我之前所擅长者乃是剑法,而方才这几句话,则是我新练武学之中的应气法门。”甘之饴道:“剑法?宋兄修为之高超乎凡人想象,难道竟然是剑阁剑圣门下的亲传弟子?”宋蒙摇了摇头,说道:“不是,我习剑乃是因幼时所仰慕的一位前辈,他实力与剑法之高乃是我生平仅见,更在剑圣之上。”
甘之饴五官和三观再度崩塌,表情像是被踩碎的一塌糊涂的鸡蛋,简直惨不忍睹。内心疯狂吐槽:“剑圣已经是清圣境界的绝顶高手,与三教道祖乃是一般的存在,你居然说有一人的实力与剑法更在剑圣之上?那是十二境还是十三境?这两个境界从来就没有人踏足过,虽然你看起来似乎也不比圣人境的高手弱多少,但是我TM还是在考虑你丫说的到底是不是人话……”甘之饴费了非常大的劲从内心旋涡中挣脱出来,说道:“不知这位前辈是谁?恕在下孤陋寡闻,似乎并未听说过。”宋蒙道:“这位前辈剑法造诣之高,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对手甚至连逼他回挡一招也无法做到,他在四十岁后,不再滞于外物,举手投足,动静之间无一不是剑,却又无一是剑。无声胜有声,无招胜有招。到了晚年,更是再无一人能对他动武。”“如此境界,自然远在剑圣之上。”甘之饴听的入神,喃喃道:“似此修为,的确难以想象。”若是自己也能仗剑去国,行走天下,鲜衣怒马,当真是好不快活,一时竟想的痴了。只听宋蒙的声音接着传来:“我幼时因仰慕这位前辈的绝世英姿,故而学剑。至于这位前辈不为世人所知,乃是因为……”“我知道,”甘之饴抢声说道:“一定是因为高人有高人的脾性,这位前辈既然如此厉害,凡俗之人自然不入他的眼界,他看不上我们,便隐遁山林,逍遥快活,他这么厉害,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当然就不知道了。”“你说的也对,这位前辈年轻时笑傲江湖,生平欲求一败而不可得,后来便隐于山水,再不为世人所知。”“只不过……”宋蒙顿了一顿,接着说道:“只不过这位前辈并非当世之人,他是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的,既然非是当世之人,自然不会为世人所知。”宋蒙耸了耸肩。
月上中天,云遮星影,在湖水淡淡的微光映照下,刚刚淋了雨的柳树枝条,显得晶莹通透,极是干净,挂着一颗颗圆润的水珠,像是石榴籽,混合树叶的清香,惹得一只乳燕频频飞下,伸嘴叼啄,但是水珠一碰便无,那乳燕焦急,不停扑扇着翅膀,鸣声脆脆,煞是动听。
甘之饴表情先是神往,而后变得诧异,继而平静,最后面无表情,缓缓垂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对着宋蒙说道:“我TM……忍你很久了,看招。”发掌劈出,径直击向宋蒙面门,他自知绝非宋蒙敌手,是以这一掌用上了十成力道,只求打他一掌。宋蒙微笑道:“甘兄弟,在下所言,句句是实,你又何必动气,若是切磋,出十成力未免太重了。”甘之饴喝道:“谁跟你切磋?我也不是第一次想揍你了,茶喝了这么久,活动活动筋骨对身体有好处,还请宋兄指点……卧槽。”但听“噗通”一声,自己这一掌尚未打到,脚下气劲忽然一空,竟然摔入江中,鱼虾受惊而动,四散逃逸,湖中月影无声而碎,渐渐扩成涟漪。甘之饴这一晚连连坠江,早不在意,跃出水面,正欲运功烘干衣裳,突然发觉并无凉意,伸手一摸,身上衣裳丝滑干燥,入手极为舒爽。却听宋蒙声音从画船上传来:“你当真要打?”甘之饴向画船一拱手,道:“请宋兄指点,多谢!”说着左手起势,足下丁步,右掌向后,正是《覆雨掌法》中的一招“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宋蒙并不起身,仍然坐于桌后,“虚传”碧烟凝成一线,缓缓从舷窗之中伸出,轨迹清晰可见。甘之饴一怔之下,登时明白,口中道:“得罪了。”左足跃起,左掌在上,右掌在下,如同苍松迎客,向前击去。这一掌周全礼数,并不凌厉,碧烟亦不相攻,从中一弯,意似鞠躬,正好避开来招。甘之饴右掌回返,旋身再攻,碧烟上冲,径点甘之饴手腕,甘之饴右手回缩,右腿接后,拦腰横扫,碧烟化直为削,斩向甘之饴右腿膝弯,甘之饴左手成抓,拿向碧烟腰中,右腿变横扫为顶,撞向碧烟。碧烟忽然双分,如同枝桠,正中伸长绕住甘之饴左手,上首回冲,势如一个人身背大地,右手拿住甘之饴左腕,右脚踢向甘之饴面门,甘之饴大声道:“喂喂喂,宋兄,打人不打脸啊。”那碧烟上首不再靠近,绕住甘之饴左腕的一端横着一挥,将甘之饴远远的扔了出去。甘之饴借势翻了个跟头,方才站定,本以为自己起码能和宋蒙拆上十几招,不想竟然连三招也未曾走过,不禁垂头丧气。那碧烟待他站定,便一分为二,一击“中府穴”,一击“海枕穴”,甘之饴见来势迅捷,且一前一后,掌力发出,和前方碧烟撞在一起,回身向后,双臂如扭,卷起水流,欲将劲力卸开,不料那碧烟竟然打蛇随棍上,反倒借水之力,电射而出,击中自己左腕,左臂登时一麻,同时跳环穴上一痛,立足不稳,便要栽倒,那碧烟缠住甘之饴左足,往上一提,将甘之饴倒吊起来。甘之饴大吼一声,翻身落下,双臂呈现八字,如同怀中抱着一个圆球,聚气掌中,口中喝道:“《覆雨掌法》• 羁式 • 如风举荷。”言罢双掌一翻,压向江面,江面乍起两股水柱,攻向两道碧烟。碧烟再化为三,绕成一个三角形,水柱攻来,浑然不动,而后三道碧烟分袭甘之饴胸口,咽喉,小腹。甘之饴见状,旋身转起,带起漩涡,消化攻势,而后右掌自前向后,左手外扩,一者收一者回,双掌推出,道:“《覆雨掌法》• 绽式 • 中流击水。”一道掌力发出,直欲将三道碧烟打散,却见那碧烟再分为四,尾端相连,首端打开,形如一把正在撑开的雨伞,与掌力正面一撞,一层一叠,将掌力尽纳,尾端张开,道道发散,甘之饴一掌尽数落空。甘之饴目瞪口呆,却见碧烟又增为五,再度向自己袭来,甘之饴叫道:“别别别,打不过啦。”但听嗤嗤之声不绝,甘之饴后背,前胸,颈下各俱中招。不过却是不痛,五道碧烟击在身上,也就消散了。面前忽地一花,已经回到船上,好像自己从未动过,甘之饴怔怔的看着宋蒙,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宋蒙道:“第一道碧烟你过了三招,随后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碧烟均只挡了一招,在四境之中算得中游,以此参加玄素问鼎,或能夺魁,但是想要进入大宗派修行,只怕尚还不够。”伸手倒了一杯水,问道:“喝不喝?”甘之饴伸手接过,摇了摇头,放在了桌上。宋蒙接着道:“如果你真的不想参加玄素问鼎,不如回去和令尊说个清楚,各人自性,强求无益,若得与亲人共聚天伦,我觉得更胜修行。”甘之饴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希望老爹可以放下坚持,还是让我在家舒舒服服的睡大觉吧。”“哎对了宋兄,我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是人吗?”……“砰!”“卧槽。”“哎呦”,“哎呦”……
宋蒙端着杯子,手指摩挲着杯面,轻轻的道:“哈,十年弹指,惚惚而已,天遥地远,溜达了一大圈,不如回去逛逛,只盼我那几个师弟师妹们,不要再让我做掌门了。”“真的没什么意思啊。”将杯中凉透了的“大梦初醒”倒入江中,再重新倒了一杯,慢慢喝着,画船徐徐而动,顺着临安江流,渐渐荡开涟漪,“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是真的么?”
周围立在对面,甘之饴转头看向画船,却见船桨划起,一前一后,带起水花,越来越远。江面已不再平镜,鱼虾俱无,也许是因为夜深的缘故,一眼望去,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天空又下起了小雨,甘之饴打了个寒颤。远远传来什么“无寻处”,但是声音太小,又被下雨声冲淡,便也听不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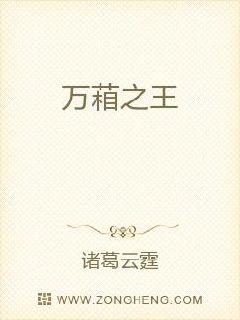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