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在途
朝有余梦,日落黄昏。
夕阳余晖照在山道之上,映出个孤单的人影。
那人是张宇初。
他已经在山道上赶了两天一夜的路,期间遇到过不少过路的旅人。他一边问,一边往北走,终于来到这里。
这里距离汀州府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如果他敢连夜翻山,并且没走错路的话,今夜便可到达。
“看样子不要半个时辰,天就黑了吧。”
夏末的白昼还算长。
张宇初忧心忡忡地捂着胸口的护符。那护符正是白鹤道长所赠,昨夜他累倒在山边,一觉睡到天亮,没想到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左思右想,发觉口袋里的清凉感觉很是舒服,拿出护符后发现护符还在发出淡淡的青光。当即他便明白了白鹤道长的好意,心底生出感激与愧疚,也将护符戴在了胸口。
此时黑夜即将来临,张宇初不确定护符还能不能保护他,故而忧心。
“该来的总会来,如果没效果,也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带着这样的思绪,趁着天还未完全黑,他再次迈出步子,沿着山道往前走。
许多方向都有炊烟升起。张宇初一路已经看到许多处村庄了,但他都没有再进去。一则他蓬头垢面,浑身破破烂烂,连鞋子都露出脚指头了,去了像是乞讨,非常晦气。
另外有了闲云观的事在前,他心底不想再连累他人。
“咕咕咕——”
他的肚子发出了一阵抗议声。但他没有理会,他就这样步履蹒跚,不急不缓地走着。
爬山丘,过小桥,远山还算青翠,近处的阔叶多是掉落。
踩在枯黄的落叶上,他的思绪越飘越远。
“你就该有这样的下场!”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杀了你!”
张宇初突然停了下来,手掌捏着脸庞,弓着腰慢慢跪下。
“如一......今后,不会相见了吧。”
他用力吸了一下鼻头,额头挤出抬头纹,茫然四顾:“这广阔天地,又该何去何从?”
山道空旷,回答他的只有风声。
良久他才平复心情,将深深的惭愧感按捺下,重新赶路。
“知——了”
“知——了”
荒凉的道路,几排树木矗立成林,在这里居然还能听到夏蝉最后的鸣叫。时过境迁,曾经让张宇初无比烦闷的声音,如今听入耳中,竟然也有几分悦耳。
至少不那么孤单......
他想走得慢一些,多感受一下那生命的鸣叫,但夕阳紧催赶路人,他终究没有在路上逗留。
晚霞中传来最后一声雁鸣。
他恰好在最后一座还算高大的山下走过。
他要绕过这座山,才看得到平整如川。
黑夜按时来临,张宇初所站的位置还算高,于是他的眼前是落日沉沦,身后是夜幕直追。回望天涯,他发现自己已经走出很远很远了,而前路仍然遥遥无期。
他着实有些累了,饥饿感与劳累感互相杂糅,让他的精神无比疲惫。他本想再走一段路,但远处传来的野兽吼叫声让他不得不止步,停下来思索哪里适合过夜。
这一片看不见人烟,最近的村庄已经被他绕在后头,再折返显然不可能。加急赶路的话,前边是大片平原,若是碰到野兽,未必跑得过。
想来想去,张宇初便停在了山里,他四处找寻了一会,刚好看到不远处有几棵叶子没落干净的树凑在一起,枝叶交错,树干还算粗,勉强够睡。
就那了。
张宇初借着余晖,冲了过去,然后手脚麻利地爬上树,在离地丈二高的位置盘膝而坐。
树皮粗糙,枝干不整齐,都没有影响他的入定的状态。在过去的旬日里,他早习惯了白天赶路,晚上练功的作息习惯。
赶路赶的自然是去龙虎山的路,练功则是意外得来的饮魔功残卷!
人活着,还是要有希望!
张宇初暗叹,若非得到饮魔功,这几百里山路走来,他可能已经放弃了。
但现在,他开始学会慢慢静心,双手下方,结与丹田之前,调整呼吸。
渐渐地,他的呼吸平缓下来,越来越慢,他的人也平静,仿佛身长在这颗树上一样。天地已远,万物寂灭,只剩他一人一息,由外自内,循环不息。他就这样枯坐着,慢慢将饮魔功入门吐纳篇运转周天,虽然只有单脉单向可循,但也值得庆幸。
唯独有一点他不知道的是,一直缠绕在他身上的黑气,至今未消。他人修道,汲取的是日月风华,而他却是将依附在周身的黑气引入体内,在携带废气而出,在不知不觉中用黑气将五脏六腑敲打了一遍,像是给虚弱的脏器镀上一层薄膜似的。
他还不能淬炼肺腑,更别提丹田聚气,开拓心源。但这也未必是坏事,他根本不知道那黑气是什么,也不知道这黑气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他的想法很简单,练功便是了,左右不会比以前更差。
何况在过去的旬日里,他除了开始的几天会腰酸背痛腿抽筋,外加伤口隐隐作痛,之后每练一晚上饮魔功,气息就绵长一些,肺腑也更能抗累。甚至于一连走几十里山路,也只是筋疲力尽,休息一晚便又生龙活虎了。对比从前,自从爷爷离开后,他不仅坐吃山空,浪荡汀县,还体虚气弱,不堪重任。此时整个人精干许多已是不得了的进步。
这给了他底气,也让他在经历过生死之后,格外专注地练着。他想了很多,现在最希望的便是变强,他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夜晚悄然过去,晨曦暗淡,照常升起。
这个时间天地之间,气息较为浑浊,张宇初眉头微动,“啪嗒”一滴露水顺着叶子的脉络滑下,滴在他的脸上。觉得入定的状态受到了影响,他睁开了眼。
他简单活动了下肢体,双腿仍会麻木,但休息一会便能活动如常。
他便将注意力转到查探四周上。
这些天天气不见得很好,时长阴沉下雨,偶尔出太阳也不太温暖。所以山间的动物一般出来得少,离山道越近的东西也更难看见猎物。
但张宇初饿了。
他的精神还好,但身体已经一天未曾进食。他离辟谷的境界还早的很,这会急需食物。可搜了一圈,他也没发现什么可以吃得活物。不由得叹息一声,思考着去哪里摘点野果果腹。
然而这里离平原太近了,地势渐渐变缓,路上见到的几棵低矮出的果树早就被其他人摘掉,连带着青涩的都没留。
目光平静,张宇初抓住树枝站起身,找了个合适的角度,往下爬,到离地不足一丈的时候,直接抱着树干滑了下去。
脚掌踩到地面时,张宇初觉得步子有点虚,稍微适应一下,便提着包袱往山上走。
夏日即将结束,秋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许多果树都开始结果,但此时能吃得不过三五种。
张宇初知道这一片地带,只有一种很小个的棕色野梨子能吃。
他在山上转了一圈才找到一株,这种梨树不高大,果实差不多拇指和食指圈起来那么大,吃起来干干的,水分不多,甜中带涩,口感不是很好。
但张宇初不嫌弃,他当初带的干粮早都吃完了,一路上半生不熟的兔子,去掉内脏和鳞片的鱼虾和未成熟的野果都吃过,此时根本不挑,他把包袱摊开,开始摇树!
之所以摇树,是因为最熟的果子会刚好被摇下来,这种可以当天食用。剩下的则要爬上去甄别一下,差不多快成熟的包起来,放个几天,就会成熟一些。
“呼呼——”
张宇初大力摇晃着果树,果子一颗颗掉下,他也不洗,捡起来便往嘴里塞,吃过几个之后,便把能塞的全都塞进包袱里,心满意足地继续上路。
他重新回到山道上,朝着北方走。
这一天,从清晨道晌午,他赶了将近三十里路,终于路越走越宽,他看了一片梯田,看田里稀稀拉拉成片倒下的庄稼,张宇初大喜。这附近肯定有人,虽然这片田似乎缺少打理,但前面肯定有人居住。
他便提起干劲,加快速度赶路,又走了几里路,绕过一片矮丘,他看到了几座茅屋。
茅屋统共三间,居中的大,左右两间或方或长拼接在一起。茅屋外边是片小院子,种了些蔬果。
张宇初无意乞讨与借宿,他早几日问过路,到了今天已经好久没见到人了,生怕走错了路。便稍稍整理了下自己褴褛的衣裳,把渐长未束冠的头发撩开,撇到两边,让自己还算清秀的脸露出来。
做完这些,他深呼一口气,朝茅屋走去。
茅屋是开着的,主人应该在家,张宇初刚走进院子,“汪、汪、汪——”
突然从一口水井后面跳出来一只黄狗,龇牙咧嘴地朝他狂吠!
张宇初放慢了脚步,口中发出:“啄,啄——”的声音,这在怀远县,是“狗子乖”的特殊安抚音。
但这里已经出了怀远县,黄狗好像听不懂外地口音,仍然不停歇地狂吠着,张宇初靠近一点,它便后退一点,如临大敌,好不安静。
“啪!”
茅屋的木门突然关上了,一个中年妇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谁?”
张宇初有些奇怪,前些日子看到的乡人也不见得这么怕生,这会怎么还没看到人先吃一个闭门羹。
但他心态还好,礼貌地朗声道:
“大娘莫慌,小子是过路的旅人,独行到这里,想问个路!”
屋里的人听到张宇初说的话,噢了一声,许是觉得张宇初的声音很真诚,不像是作伪。便将门缝拉开一些,从里面往外看。
张宇初见对方观察自己,便双手摊开,露出一个还算阳光的微笑。
门缝又拉开了一些,露出那妇人的半边身子。
“汪汪汪。”
黄狗还在叫,那妇人出声呵斥道:
“锉,大黄安静点,不要吓到客人!”
黄狗呜咽一声,尾巴摇了几下,跑到主人脚边撒了个娇,不过仍旧恶狠狠地注视着张宇初的一举一动。
妇人虽然露了半边脸,但也还是很戒备,有意无意地露出了手上握着的菜刀。但语气已经缓和了许多:
“郎郭,没吓着吧?”
张宇初本就不想进去,既然这狗没扑上来,那他也乐得保持一点距离。他便站在原地,笑道:
“没事的,大娘别担心,我急着去龙虎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大娘能不能给我指个路?。”
那妇人点点头,没邀请张宇初靠近的意思,回道:“龙虎山啊,那可还远着呢,从这里往北走,过了府城还得半月的路程才到。”
看来是没走错。
张宇初心里安定不少,继续问道:“大娘你说的府城,莫非是汀州府城?还是昌南府城?”
这话倒是把妇人逗笑了:
“傻郞郭,这里还在汀州境内,当然是汀州府城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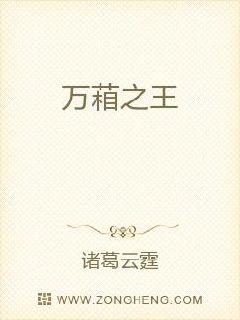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