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故人来
十九当然不知道身后北邙山上发生的小插曲,兀自走在青石小巷里。
整个南山村其实就只有这一条巷子,长不过两百余步,两旁都是低矮的院落,长年荒废无人打理的缘故,入眼都是一片萧条破落的景象。
荒草从残破不堪的土墙边、无人问津的门窗里、陈旧腐朽的屋檐上冒出来,爬满了整个村落。屋檐下筑满大大小小的燕巢,这个时节,大部分还是去年的旧巢,新巢在更靠外面一些的地方。
十九知道,要是他愿意,朝阳那些檐角下,他应该还能找出几个蜂窝来。
纵然十年前的涨潮没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活物,不过区区十年,自然还是以其不可抗拒的伟力抹平了几乎所有的痕迹。
十九走到小巷尽头一个没有草的院子前站住,这院子显然有人打理,低矮的土墙虽然粗糙但也还算完整,甚至土墙上还爬了几株干巴巴的葡萄,院口是两根一人多高的柱子夹着两扇低矮的篱笆,权且就算做门了。
推开门后的院子不大,入眼处是座一进一出的茅草小屋,左右不过十几步宽,左边屋前左右都摆满了木架,左边晾满了风干的猎获,右边晒着一垛柴火和一些大概是貂或者狐之类的皮草。十九把黄羊往地上一扔,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一卷袖子,开始处理起这只在雪地里躺了两天才等到的猎获。
南山村原本物产丰饶,这十年来山上的猎物虽然越来越少,但是这一片就十九一个猎人,养活他自然绰绰有余。
不过猎物终归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比打猎更好的事情,当然是北邙山上的灵药。
可惜的是,十九找到的最后一株灵药是三年前他在火猴林摘下的一颗快要长成的火云果,那之后灵药似乎就在偌大的北邙山中绝迹了——至少十九再也没见过它们。
所以十九现在很有危机感,天知道万一哪天北邙山里连猎都没得打了呢?
虽然他也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十九还是决定趁现在努力攒下每一分银子。
把弄回来的黄羊处理好,十九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时已近暮,夕阳斜斜的挂在北邙上山上一尺来高的地方,阳光暗晦,看起来有气无力的。
他擦了擦手,肚子咕咕作响,这才想起自己这两天粒米未进,腾出手来准备弄点吃的。
初春的落日不比盛夏,只是在先吃后腿还是前腿的问题上稍微纠结了一下,大半个太阳已近掉进北邙山里,模模糊糊的雾气从山林间升了起来,本就厚重的北邙山显得更加迟缓老迈。
十九带着半只羊腿推开茅草屋的房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具之外几乎别无他物,房间主人显然不是个太有生活情趣的人。
房间正中是一个黑色的浅坑,上面架着一个沾满油灰的铁架子,十九把火升起来,变魔术般的掏出一堆香料,专心烤起羊腿来。
专注或者说执着是十九的一大特点,十九感觉自己仿佛被某种强大的本能所驭使,他做的事情,一旦开始,似乎眼里就只剩下那件事情,完成之前根本停不下来。
不过也说不上来这就一定是个好品质。
他确实可以在雪地里蹲上几天几夜等待一只猎物,但也曾在十四岁的时候因为追一只雪兔一头扎进了豺狗的地盘,那次执着留下的记号至今还留在左手臂上。
但是怎么说呢,就像人们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这世界上总有些蠢货要撞了南墙才会回头。
当然,还有更蠢的,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
他们会一直撞,要么头破血流的撞过去,要么头破血流的撞死在墙上。
十九显然属于后面那种更蠢的,这点从他十五岁为了一只不足五斤的兔子就和山北六个老猎手死杠也能看得出来。
那些人本来以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随便吓唬一下,就会把手里的猎物拱手相让——毕竟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孩子自然也很清楚打起来没有胜算。却没想到不管是恐吓还是殴打,那孩子只是团成一团,抱紧那只兔子死不松手,不过不管那些人怎么拳打脚踢,那孩子在地上翻来覆去都只重复一句话:“这是我先打到的兔子。”
后来可能是那群人觉得为了一只不足五斤的兔子打这么久实在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力气,丢下他扬长而去。十九一瘸一拐的从山上下来,在邙山城的正阳斋里躺了半个月,花了七两二钱四分银子——差不多是当时他的的全部积蓄,让他肉痛了一整年。
七两二钱四分——兔子保卫战的代价。
这种二笔品质是好是坏暂且撇开不论。
有一点十九可以拍着胸脯保证,至少用专心烤出来的黄羊腿味道绝不会差。
他满意的看着眼前烤好的羊腿,金灿灿,油汪汪,猛的吸了一下鼻子,嗯哼,色香味俱全,完美。
一阵风卷残云之后,十九用刀把羊腿骨缝里的肉一点点挑出来吃掉,这是多年来在邙山生活下来的习惯,每一分食物都应该得到充分利用。
最后十九把十个手指全都啜了一遍,往兽皮衣上一抹,在火堆旁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开始思考白天的事情。
这也是十九的习惯,杀羊的时候他想的都是杀羊,但是一旦停下来,他就会想些别的事情。
他坚持相信,不忙的时候多思考可以让他少忙些。
比如他兽皮衣服里面的《狩猎宝典》——他自己编的,上面精确的记录了从他打猎到现在遇见每一种猎物的位置和时间,他把它们都按季节,种类,标在了北邙山的地图上。
所以不过区区两年,他现在已经是北邙山最出色的猎人。
十九自认对脚下的这片土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北邙山上寒冷的冬天里机敏的黄羊会去哪里觅食,也知道下山路上什么样的岩缝里住着狡猾的豺狗;他知道哪片崖璧上长着珍稀的云根石,也可以轻而易举的从白水河边几百种草木中分辨出哪种是能活筋生血的红花草、哪种是一小片就能要了人命的飞燕草。
但是关于会飞,还能拼成字的树叶。
十九一无所知。
这种一无所知的感觉让他不大舒服,那树叶拼成的“是”字”时不时闯入他的脑海,十九隐约间觉得这大概是某种预示?
某种——会有更多的未知闯入他生活的预示?
他自己也并不确定,甩了甩头,试图把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甩出自己的脑海。
说不定这就是老水井憋太久了,随便开口应付他一句呢?
给自己下了这个安慰性质远大于实际意义的结论,十九暂时轻松了些,他拾起一块柴火,朝火堆里丢去,又拱了拱柴火,让火烧的更旺些。
十九环抱膝盖,在火堆前坐下来,把下巴放到膝盖上,眼底映射出眼前跳跃的火焰,偶尔一声清脆的爆裂声溅起一团飞舞的火星,他的目光就追着那些火星游移,那些会写字的树叶逐渐淡出他的脑海。
火越烧越旺,寒冷逐渐离他远去,温暖将他包围,十九的脑海变得一片空白。
他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完全黑了,正下着雪,映着屋里的火,纷纷扬扬的。
十九叹了口气。
北邙山的春天就这样,说变就变,他推开门,准备去把晾在院子里的东西都收回来。
雪不大,但是地上也已经有浅浅的一层。
十九先把皮草抱进屋子,转过身准备去收腌好的腊味时候,他突然停住了,看向院子口。
漆黑的夜里,虽然只是屋里的一炉火光,影影绰绰,看不太真切,但是毫无疑问的——门口有一个人。
那或许是个访客?
如果是的话,那他就是十年来这个院子唯一的一个访客。
十九从火堆里抽出一块烧的正旺的柴火,拔出腰间的短剑,朝院子口的小柴门走去。
走的近了些,十九已经能看清那是一个带着斗笠的男人,斗笠遮住了他小半张脸,依旧露出了下半张胡子拉碴的坚毅脸庞,穿着一身蓑衣,看起来像白水河上的垂钓人。
十九站在三步开外把火把朝前伸了伸:“你是?”
来人抖了抖蓑衣上的雪花,把斗笠抬得高了些,露出他那张刀削斧凿的脸庞,好让十九看清楚他的脸,眼里如有星辰流转,声音低沉略带嘶哑:“我能进来么,外面也挺冷的。”
十九看见那张脸,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僵硬了。
那绝对是他这辈子印象最深刻的一张脸。
十年前他还不过是一个六岁的孩子,缩在老水井下的水桶里瑟瑟发抖着等待命运到来的时候,井口突然被掀开,和井口的阳光一起出现在他眼里的,还有一张如刀削斧凿的脸。
十九到现在还常常梦起那时的场景,那张刀削斧凿的脸在井口略带嘲笑的朝他吆喝:“嘿,小鬼,是不是吓得尿裤子了?”
他涨红了脸的反驳:“没!没有!”
泡在井水里,是不是真的尿了裤子十九其实自己也不知道。
那张脸显然也并没有真的在意这个问题,朝他伸出手哈哈一笑:“不错,小男子汉挺勇敢。”
他仿佛被清风托起,缓缓朝井口飞去。
但他几乎忘记了飞翔的喜悦, 他眼里只有那张脸,和那双眼睛——那双装着浩瀚星河的眼睛。
然后才是四面八方赶来的赶潮人,他们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棕色的斗笠,青色的劲装,漆黑如墨的大氅上绣着金色的苍梧树。
他们如鬼魅般突兀的出现在空气里,在他身边的男人面前单膝跪地,单手扶着斗笠,点头致意,又一个个突兀的消失不见。
那个男人也扶起斗笠,微微点头,算是回礼。
那个男人低头看着刚从井里捞出来如水老鼠般瑟瑟发抖的孩子,右手扶起斗笠,微微点头一笑道:“小家伙,捡回来的命好好珍惜,我们还会再见的。”
十九还没来得及问再见的那天是哪天。
那个男人就飘散在风里。
从出现到消失,前前后后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仿佛从来没存在过。
他一个人呆呆的坐在井沿上,额角伤口流出的鲜血涂满了他小半张脸庞,不知过了多久,北邙城里赶来的医官给他清洗包扎,他甚至都感觉不到一丝疼痛,甚至连恐惧都忘记了。
脑海里只有那张脸和那句话在荡来荡去。
“小家伙,捡回来的命好好珍惜,我们还会再见的。”
十年来,十九反反复复的梦到这句话。
年复一年,有时候他甚至怀疑,这只是一场梦境。
那个男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也永远不会再回来。
而现在,这张脸又出现在他面前。
虽然多了些胡渣,看起来有些憔悴,鬓角生出些白发。
但是毫无疑问,这就是那张脸!这就是那双星河流转的眼睛!
斗笠男子看着发呆的十九,淡淡一笑:“有什么问题么?”
十九猛然从僵硬中缓过来,尴尬的摆手道:“没有没有,我就是走了一下神。快进来快进来!大——”话音到这里十九的话戛然而止。
他才突然醒悟过来,他既不知道眼前旧人的名字,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看鬓角的白发,大概应该叫大叔,面相看起来又是三十来许的年纪,大概叫大哥也行?
斗笠男子晒然一笑,看破他心中所想:“不要叫什么恩公之类的,太俗,叫大叔,我也不年轻了。”
十九连忙把斗笠男子让进院子里。
斗笠男子扫了一眼院子,可怜的院子十年来都没招呼过客人,自然是寒酸无比。斗笠男子的目光最后终于落在缺了一只后腿的黄羊身上,停住脚步。
十九也赶紧跟着停住脚步,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斗笠男子皱了皱浓密的剑眉,咳嗽了一声,捉黠道:“一般这种时候,你不是应该问我吃了没有……我要是说吃过了,你就得接着问我要不要再吃点之类的么,我要是说那多不好意思,你就告诉我没关系没关系,就加双筷子的事…….”
少年幡然醒悟,抽出腰间的短剑,寒光闪闪,露出一脸热情的微笑:“那个,大叔吃了没?要不要在……”
斗笠男子并没有按套路出牌的意思,干脆利落的打断他的话:“没有,我可是赶了好远的路。”
“唰”的一声,可怜的黄羊一天之内又少了一条腿。
茅草屋内,少年又抱了些柴火进来,让屋里的火烧的更旺盛些。
到了屋里的火焰旁这张梦中的脸庞才终于变得清晰起来。坚硬脸庞每一划都像是斧钺劈出来的,绝不带多余的棱角,古铜色的皮肤和两鬓的斑白诉说着这张脸经过的风霜雪雨,眼角细密的鱼尾纹里,每一道都仿佛刻着一个故事。
但显然,故事的主人看起来不像是个爱讲故事的人。
少年在一旁看着斗笠男子狼吞虎咽,找了个机会弱弱的开口道:“大叔,你…….”
斗笠男子又是干脆利落的打断他的话:“我知道小家伙你现在有很多问号,忍住!不要问,等我吃完再说!”
少年咽了一口口水,把剩下的话硬生生的吞回去。
约莫小半盏茶的功夫,斗笠男子满意的放下手中的羊腿骨,饶有兴味的看着十九:“没看出来,你这小子,脑瓜子不太好使,手艺倒是还可以,唔,你现在可以问了,问吧,我为什么到这里来。”
少年呆了一下,想起来刚才要问什么:“那个,大叔,我刚才是想问下你,羊腿一个够不够吃,要不要再烤一个…….”
斗笠男子气结:“你刚才怎么不早说?”
“大叔你刚才不让我说……..”
……
斗笠男子叹了口气:“你这脑瓜真是,算了算了,看在你手艺的份上,不和你计较。”无奈的挥了挥手:”快去快去。”
又是一条羊腿下肚,斗笠男子打了个饱嗝,看着十九道:“怎么,不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条?”
十九嘿嘿一笑,尴尬的挠挠头:“不用不用,大叔你吃饱了。人吃没吃饱,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吃不饱的时候可难受了。”
斗笠男子一怔,看了家徒四壁的茅草房,才意识到当年他丢在井口旁那个小鬼,这么多年多半就是一个人在这儿这么过来的。一个六岁就没有父母的小孩儿,自己刚才居然和他开了个父母和人客套的玩笑话。
想到这里,男人心里觉得有些歉意,尽量让语气柔和些,迟疑道:“这些年,你都是一个人在这儿?”
十九哪里知道就这么一个瞬间斗笠男子心里就这么多百转千回,连忙应道:“嗯!”
虽然问题有些残忍,但斗笠男子还是止不住好奇:“我记得你当时应该也就六七岁的样子吧,你一个这么点儿大的娃娃,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活下来的?”
十九哈哈一笑,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颇为自豪,神色突然变得生动起来。
“其实也不难,像我这种孤儿,能一直在北邙城荒政司领抚恤到十二岁,虽然一年只有五两银子,但是北邙山上有草药可以挖,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碰到灵药,这些都可以去北邙城里的正阳斋里换钱,一开始我是分不清楚,老被收药的张老头骂,后来就简单多啦,现在他们正阳斋里的人都没我认识的药草多!我还可以自己打猎,大叔你不知道,现在去外面提起我十九的名头,整个北邙山的猎户那都是要叫一声好汉的!”
少年看着斗笠男子饶了饶头,想起刚才可能骄傲了些,有点不好意思,接着道:“大叔你不是说过我要好好活着嘛,虽然我现在会的都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肯定和大叔你没法比,但是其实我也没怎么偷懒,哈哈。”少年憨憨一笑。
斗笠男子有点意外:“所以就因为我当时说我们还会再见,你就一直呆在这儿?”
“也不是啦,涨潮之后,村子里大概是留了味道之类的,除了虫子啊什么之类的,灵光一点的像是虎豹豺狼什么的,根本都不敢往这边来,人就更不往这儿来了,其实这里挺安全的,而且,我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这里房子还多,随便挑!我想来想去,还是呆在这里最好!”
只是寥寥数语,以男人的心智,如何听不出其中的艰难。
然而眼前的少年只是纯粹的骄傲于他所取得的成就
毫无疑问,对眼前的这个男人来说,所谓“正阳斋鉴药小能手”“北邙山猎户扛把子”这一类的成就和他足以载入史册的传奇经历相比显然不足一提。
但某些方面他们取得的成就是一样的——他们都活了下来,都是幸存者。
男人看着眉飞色舞的少年,想找出一丝掩藏的悲伤。
他失败了,他满意的笑了。
他愈发肯定自己这一趟回来是正确的。
他向来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心中计议已定,便直接开口说出少年心里埋藏了十年的那个疑问:“十年前我就觉得我差个徒弟,不过那时候还不太肯定。今天我确定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还差个人继承我这身手艺,你有兴趣没?”
少年略微有些迟疑:“是哪方面的手艺?”
“害,也不是些什么了不起的手艺,大概就是怎么和人打架之类的,当然你要是偶尔要抓两只魔来烤着吃的时候也用得着,我烧烤的手艺肯定比不上你,但是关于怎么抓怎么打这件事情,我手艺还算不错。”
少年只是短暂的失神之后,马上反应过来,倒头便拜:“师——”
男子扶住他,笑着止住了他拜师的举动:“先别急,年轻人下结论太轻率可不是个好习惯。”
十九没吃过猪肉好歹见过猪跑,这才反应过来拜师也是一件大事,连忙问道:“是要挑个日子么?我要准备些什么?”
男子笑着摇了摇头:“年轻人口比心快,你今天说的都不作数,不用挑日子,也不用准备什么,七天后你再给我答案,只要你愿意,我就可以当你师傅了,另——外,不管我教不教你,师傅这两个字都太拗口了,你还是叫我大叔,明白了么?”
“好吧,师——大叔,那我这几天该干嘛?”
“这几天嘛,你得先补补课。”
“大叔要给我上课么?”
斗笠男子扭头看向窗外深沉的夜色沉吟道:“不是我,会有很多人来给你上课的。”说完便不再言语
十九没有听懂,如坠云雾。
斗笠男子也不打算解释,摆摆手:“今天也不早了,睡吧,明天再说。”
“哦,大叔你等下,我去弄张床来。”
所谓的“弄张床”,其实也不过就是在火堆的旁边又加了一张兽皮,十九又多垫了两张,尽量弄得舒服些——大部分时候他都睡在北邙山里。
勉强折腾出一张床,十九把火灭了,躺了下来。
今天这一天对他来说情绪实在是太过丰富了些,他的脑袋到现在还有点混乱,在他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终于想起自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问。
他脱口而出:“大叔,你——叫什么名字?”
男子这才想起这样自己好多年都没用到的东西。
眼中风雪骤起。
男人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更加沙哑
“陆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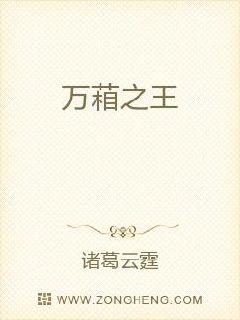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