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神居山(下)
等到白天华钟离下山过湖,循印象一直东去。真个是脚不沾地,两袖清风,缓步行迟,欲以人情体天心。
三秋风浸,满地黄叶无枝依;九霄云乱,几行征雁乘风急。日中原尚谧,筌散水更凄。桥残数石拢,草没一地梨。谁道果辛不堪食,留于鸟兽过冬至。正因那放纵无涯,水没城洼。野径寻旧路,拂尘掸牌幕。道上历历何所有,街边行行植白榆。
华钟离在路上,过了犹有三尺水深的废城,眼见一川相隔,新区已近。前面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看见一座混凝土大坝,南北四十里,又上前,已建了二十米高,还在不停增加中。
那坝前空地停了一路排的吊车、起重机,足有几百台,密密麻麻的脚手架上,攒簇了上万工人,搅拌机嗡嗡作响,打桩机隆隆刺耳,挖掘机刨土破石,土方车鱼贯出入。
有一处断口,尚未合拢,一条水泥路穿壁而过,被压得是坑坑洼洼,走得是颠颠簸簸,浑水坑,断头路,碎渣遍地,寸草不生,说不出的脏乱差,吃不完的灰土尘。
他七弯八拐、东闪西躲,来到跟前。那些工人见了他,一个个惊讶诧异,把他细打量,就像看到鬼。
华钟离醒悟了,“哦!我这身道装,难怪人家吃惊。只是众目睽睽,不好变回。算了吧,天下无奇不有,又何须在意古今。”
他深深唱了个肥喏,诌道:“福生无量天尊,列位安康,贫道这厢有礼了。”又故意打了一个稽首。
工人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后来一个老师傅说:“炼师哪里来?”
华钟离笑道:“我弟子云游四海,方外之人,无来处,暂于湖西歇脚。”
再问:“这条路早就不通,荒无人烟,小师父怎么来的?”
华钟离叹口气,说,“唉!贫道无能,观赏风光,迷入草荡,涉水而过。”
众人啧啧称奇,又问:“这下可别再往回了,那你打算去哪里?”
“我有亲戚在市里,多年没走动,想去看看,跟你们借个路。”
还问:“好说好说,下班有船,一同过去,小伙子你是真道士吗?”
华钟离哈哈一笑,“那还有假不成,”反问道:“这枯水不兴,滩上还有好大一块空地,离湖也远,不清理旧城,怎么去建新坝,要知道百年一遇的洪灾,也淹不到这里。”
老人说:“也是奇怪呢,虽说前些天发大水,老堤垮了,不晓得为什么,只扩建新区,把老城圈了,另给别的管。公家也大方,每家光补偿就二十万,新房子包分配,你说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干的这叫以工代赈,每天五十块,低是低了点,本来种田,也是一样。”
华钟离心虚地问:“老师傅,发大水死的人多吗?”
“咳!还好,受伤的几千人,要说死的人,报道上讲,二三十个。”
换班铃声响了,在工人好心的带领下,华钟离顶着许许多多的视线,于大坝另一侧的码头上船,渡过东漕河。他十分感谢,长揖一下,别了老师傅,五味杂成,径往城市之中。过了关口,转下大坡,立于街市之上。此时金乌西垂,对他而言,新城其实不熟悉。
譬如老树发新干,焕发着涅盘的生机。他从未看过家乡这么井井有条,这么崭新,街道整齐而漂亮,摊位干净而秩序。空气中再无浓烟废气,小河水清澈见底。
天空明净,是一片苍茫深邃的湛蓝,只可惜风太大,都无纤翳。太阳失去了云霞点缀,显得低矮且孤寂,过一会再抬头,红日已不知所踪,许是坠入蒙谷,或者再浴于咸池,更没有留下一丝余辉。
新城更热闹,似乎每个人都面带笑容或安详,没有被愁苦和烦闷所困扰。人潮自动将他分开,犹如滚滚长江中的一块礁石,格外醒目的道装就这样突兀地立着。
华钟离停下脚步,随即就发现,人们见怪不怪,与自己迎面而过,保持着礼貌的距离,几乎未做停顿,既没有目不斜视,也没有目不转睛,就那么自然而然地一扫而过,走向殊途,或者,他们眼里只有未来,对传统不感兴趣。
华钟离忽然觉得,大概自己的心结有些过于执拗了。
他信马由缰,走走停停,在车流人海中穿梭,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把从前忽略无视的事物又恢复印象,放眼望去,四顾何茫然,不免心生感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想当年,自己曾对所谓的流俗和成见不屑一顾,读书考试所为何来?工作家庭又有甚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不过是逝水流年,冷暖自知罢了。
老君有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从修真的极端走到凡世的极端,他无备而来。事实上,灯红酒绿的街巷,五彩斑斓的招牌,光怪陆离的门面,声色犬马的男女,并不能令他的道心迷失。
这样总而言之的现代生活,审视得太过于聚焦,反倒不容易降噪。不管美丽还是丑陋,一经单纯的对比便会失真。
凡是入世游戏红尘、了结俗缘的,常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抱持悲天悯人的胸怀,善则善矣,未免迂腐落伍过了头,个个都道人间遇合无偶然,因缘果报皆定数。
眼见中叶以来,正以道化凌迟,礼教大坏,权谋机变如过江之鲫,正心实诚则二三子而已,江河日下,日甚一日。
久而久之,道德人心尽化于功利,趋炎附势,淳朴之质变浇薄之风,背信弃义。欲以教化普度,坚信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而难之,吃力不讨好,反被磨蚀了本性。或是性恶论,力征定规矩,成一时之功而毁誉参半。
过不一会,一个蹦蹦跳跳、穿校服背书包的小男孩跑过来,也停下了脚步。满脸好奇,不加掩饰地观察他,靠近拉拉衣角、拽拽袖子,围着打转,一时间恍然大悟,指着他老气横秋地说:“大哥哥,你在玩角色扮演吗,这样打扮很逊唉,都不如……”
就这样,路灯下只有一大一小的对话,和谐地融入这个城市,并没有机锋相参而迸发一星半点的火花。
和小朋友拍掌告别,华钟离踱进一个市民广场。广播的扩音器一直在朗读郡府的公告,包括重建和资助的项目。他路经一个书报亭,掏钱买了份晚报。头版用大字黑体标题写着,扶木集团斥资二十亿在秦邮郡新建高科技产业园一期。这等俗事本来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下面的配图吸引了华钟离的注意,当中握手言笑的两人背后,分明站着三仙岛弟子休英。
无怪乎自己回珠湖,也是原因之一。对真相一无所知的人们,只不过是一群混混沌沌的羊。倘若一场事后交易能弥补亏欠,那他也没有拒绝的权力。
不管三仙岛还是广洋王,让他留守中土,都是别有用心。他可以等待,等全部的头绪沉淀下来后,因为他已经答应了。这一点算得了什么——何况他的内心还将得到报偿。
有片刻工夫他想起了昔日的秦城,他的家乡已经逝去,早已不见。
可是,仅仅过了六个半月……思想远非言语所能表达。他现在正踏上陌生的故土,而使世道人心更迭,潜移默化的改变已在悄然进行中。
他弯着身子坐在广场的休闲长椅上,注意到对面树下的一处地摊,主要是一些简单的旅行用品,浏览的人寥寥无几,卖家百无聊赖地听着音乐,抬头朝华钟离瞥了一眼,又继续冷漠地低下去,既不叫卖展示的货物,也不拉拢路过的客户。
华钟离对一捆拐杖比较好奇,“你好,”他说:“这些多少钱?”
摊主当他只问其一,随口道:“十块钱,不还价。”
华钟离弹出两张百元币,“老板,我包了,有多少我都要。”
“便宜算给你了,”摊主没好气地说,“那该死的袋子是哪一个?”他的三轮卡停在马路牙子上,堆满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一会儿拉开一个袋子,一会儿又翻个儿;忽而呛得直咳嗽,忽而又挥手拭汗。
最后硬从一摞折叠帐篷底下抽出大大的蛇皮袋子来。当他把里面更多的拐杖展示给华钟离看时,脸上不由露出得意的笑容。“承惠五百块,不能退货。”
“五百,一张不少,给你,”华钟离说,同时朝对方笑了笑。“桑木做的吧!”
摊主皱起眉,一副不爽的样子,以为华钟离要惹事。但华钟离露出一种奇特的笑容,像是安抚,又像是命令,打消了他的气焰。然后才红着脸,强词夺理地说,“是又怎么样,保证你能用就行。钱货两讫,大家痛快人,任你选个搭头好了。”
“我没别的意思,就想问一下,”华钟离一只手轻而易举地拎起袋子,摊主愕然张大嘴巴,目瞪口呆,“这树材你哪儿弄得,不是家种的吧?”
“老家在乡下樊集,门口荒了的田长了一些野桑树,老地方邪性,以前不管种什么粮食都绝收,就这几颗能活。上半年不是发大水吗,地整给淹了,我寻思干脆把田改堰,做鱼塘得了,这些树就放了,也不知道能做点儿啥好,村头老疯子跟我怄气,不许动,我就连夜锯成几段,稍微加工了下,当拐杖买。”摊主老老实实地说。
“你应该信他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华钟离不客气地说,“算你命大,穷乡僻壤地气灵,老桑阴甚鬼欢喜,半夜来了丧门星,勾魂夺魄要你命。”他朝摊主转过身来。“你说搭头任我选,一点也不吃亏,”他以天眼视之,说:“把车后座下的旅行袋拿来。”
摊主一头雾水,糊里糊涂照他话做了。华钟离打开拉链,把一个圆疙瘩捡出来,又把旅行袋还给摊主。“行了,互不相欠,各取所需。回去给老人送点酒,以后多看顾些。”
“喂,你要这个树瘤干嘛?”摊主对华钟离的背影喊道:“这玩意又不值钱,枫树的,不是花梨木,我有更好的,海南黄花梨,要不要,价钱都好商量!”
华钟离摆摆手,到了暗处,趁机将东西收入袖里。心有所感,拨打了一年难得一回的号码,连通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母亲听到他的声音,惊喜交加。先吩咐他不许再失联,然后挂断通话改用视频。
他找了家最近的网吧——立即引起里面所有人的注视。吧台的小姑娘不但马上替他开了单间,而且还自告奋勇要手把手教授使用流程。华钟离礼貌但不失坚决地拒绝了她的好意,惹得小姑娘好一阵沮丧。言归正传,他改头换面,按照吩咐拨通了视频地址。
华母看来把一家子人都叫齐了,他的父母与一弟一妹。她说,听到儿子在洪水中失踪的噩耗,亲人们心都碎了,多少个晚上夜不能寐。
“阿离,老这样子下去行吗?”她兴师问罪道:“我的意思是,你必须面对现实!我和你爸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你也不是小孩子,生活是一塌糊涂,过得越来越糟糕,脾气越来越大,脑子越来越不清楚,我们对你越来越失望。你看你穿的一身,我简直不敢说有多荒唐,我的心脏也经不起回国受你的气了。”
“唉,儿子,别怨你妈啰嗦,不要活在虚幻的世界了,你呢,想想我们,给我们个盼头,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知道你消息来得多不是时候,耽误你妈多少事吗!我们找了你整整半年,一个月前刚飞回来,虽然你妈不许我说。不过……”他用手指戳了戳板着脸的华母。“现在知道你没事我们还是很欣慰,更希望你把话听进去。”
“嗨,哥,好久不见……”弟弟妹妹与他打招呼,脸上充满了惊异而又开心的表情。
华母几下没甩开华父安慰着拍打肩膀的手,索性不理了,弟弟妹妹每人揽住母亲的一只胳膊,配合爸爸的动作。华钟离看了这个来得很自然的亲人互动,一下觉得伤感。历劫而不磨损的道心却有些摇摆了,他怅惘地倒在椅背上。
“听着,亲爱的儿子,尽管你简直是发了疯,可是看到你还活着我比什么都高兴,”华母说,“今天的情况好多了,你终于又回来了——我保证是最后一次。我跟你打赌说,不会再把你丢掉,才不会呢。你给我乖乖呆在秦邮,哪里都不许去,等我把手头忙完了,我尽量快点,就去接你。你把我吓死了,这是确定无疑的。”
“妈,我可以听你的话,但不想去美国。”
“没问题,一切好商量。过去几个月,我后悔死了。想到这么多年来,没照顾好你,确实是爸爸妈妈的错,但你自己责任也不轻。别打算逃避了,至少听一回话。”
“我想会在秦邮过上一阵子,”华钟离哄到,“随便找个什么工作,你们就甭操心了,然后有机会坐飞机去看你们。我遇到一些同行,以后介绍你们认识。”
“还是异想天开!你在说些什么?同行!想也是假的,世界上没有神仙!”
为了避免不欢而散,华钟离还是勉强暂时屈服了,哪怕只是表面文章,也属他第一次表现出屈从的态度,华母龙心大悦,皆大欢喜的结果也令场面变得融洽。
他们又絮絮叨叨聊了好一会,最后华母嘱咐他一定要去拜访吴兆松,华钟离的表哥,当初在寻找失踪的他时出力颇多,华家回国也是吴兆松接待的。
第二天一早,华钟离来到新城的另一部分。这里,一条条街都是两三层高的花园洋房,建造的特别漂亮。吴兆松是做灯具生意的,看起来过得非常不错。
他家是附近占地最大、最气派的别墅,典型的欧陆古典式住宅。入口是一个雕琢得很考究的双叶铁门,通向大屋前绿茵茵的小花园,当中有一个正迸出水花的喷泉。很遗憾主人偏偏不在,门房说吴家七口人去南方度假了,过完年才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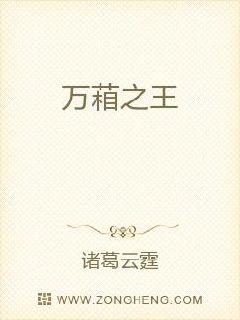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