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奇门遁甲
《易》有三大秘术,其为奇门、六壬、太乙,奇门遁甲即为奇门。奇为乙、 丙、丁三奇;门为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遁即隐藏;甲指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甲,其包含六十种天干地支的组合。
此乃用九宫八卦融入天地造化,利用日月星辰、江河山川之力变化空间方位、命途吉凶的奇异法术。其中奥秘使用起来出神入化、精妙非凡,但这种法术晦涩难懂,需常年累计学识,花费许多精力方能运用自如,非天赋异禀之人难以掌握。耗时耗神之太过,使之许多人穷尽一生也无甚造化,因此学习这种秘术之人越来越少,几乎成为失传之秘学。
众人站在桃林之中,不敢妄自行动。奇门遁甲并非他们所熟悉的法术,而且如此变化莫测、诡异无常,他们暂且还无法破解这个桃花阵。
江自流沉默了一会,道:“苏姑娘,你们天师道应该学过奇门里的一些法术,不妨给我们破解这奇门遁甲的法阵?”
苏槿棠似乎想到了什么,她点头道:“我的确有看过奇门遁甲的一些书籍,不过我也只记得一些简单的知识。时间来看……现下是夏至下旬,乙巳时,按此遁局来说,值使门是死门。布阵之人之所以昨天没有动手,是因夜色太晚,驱使之阵法还不足以发挥足够的威力,他想要等到我们次日清晨出门。我进入桃林之时恰逢是值使的伤门,所以才不幸受了重伤。”
南宫徽震惊,道:“这是什么深仇大恨,居然还想要我们死吗?我可没记得有过什么仇家呀。”
“若你进来之处是伤门,那我们现下该去往何处?”江心石问道。
“八门随着时间飞转,即便我们来时走进的是伤门,现在肯定就不是了。”苏槿棠埋头思考了一阵,道:“若要避开死门,就要避开北方的坎水位,但……”
话还没说完,突然一道白芒极速飞过,朝着苏槿棠的胸膛冲去。江自流眼光一闪,那白芒从他眼角闪过,他青袖中飞出一股气流,将这道白芒挡在苏槿棠胸前。那白影受到气流的冲撞,立刻往远处的桃树中弹去,却没有落在地上,竟直接消失在花瓣之中。
苏槿棠半张着嘴站在那里,惊魂未定,若不是江自流出手相救,那道白芒肯定会刺穿她的胸膛。她心里到底有些不甘,自问自己在天师道的同辈中的资质也算上乘,在这个遁甲阵中居然防不胜防,差点两次中招。
可是,她最在意的还是江自流,明明自己要杀他,现在反倒他救了自己,心里总有种奇怪的感觉。
忽然,江自流提高声音道:“大家小心!”
话刚未落,四面的桃瓣忽然被一阵强风刮起,花蕊中飞出数十道光芒,正朝四人逼来。苏槿棠迅速抽出长剑,江心石也从腰间抽出短刃,三人相背对,准备与这数十道白芒横面交锋。
南宫徽也提起那把青铜小刀提防戒备,但他自知这种场面自己也派不上用场,何况还有三个高手挡着,所以他只需要挪到三人中间,虽然偶尔从间隙中飞出两道白芒,但他的身手也足以抵挡了。
苏槿棠一跃而起,主动出击,在她看来总比等着别人放冷箭要好办得多。灵力注入剑体,光芒大盛,一下子就击退好几十道白影,顺势撂倒了身旁的两三棵桃树。
江心石迅猛的身手亦不容小觑,虽然是带病之身,也没有江自流那样超然卓绝,但毕竟作为江自流的弟弟,多少能学到一点绝学。他几乎没有使用过任何法术,只提起短刀迅速左右挥动,“哐啷”地竟然响起兵刃撞击的声音,白芒又向四周弹开。
可是过了一会儿,花瓣中又重新汇聚光芒,朝众人射来。
南宫徽大惊,这些白芒居然是之前的两倍之多!速度也加快了不少,就算是从三人间隙里飞来的白影,他都快要架招不住了。
江自流霍然急速跃起,一袭青衣吹得猎猎作响,几近透明的青色流光在他的轮廓上迂回流转,他双袖微举,流光似乎就势定格下来。接着他在半空起风旋转,流光化作剑锋状,向四周散开。流光和白芒交织在一起,发出连续不断的闷响,白芒渐渐消退,然后在半空消失了。
江自流从空中落下,双袖飞舞,飘逸如神。
桃林再次恢复平静,只有桃花瓣被余风吹得漫天飞舞。众人放下兵器,重重地呼了一口气。苏槿棠倒是深深吸了一口气,她感觉自己差点是窒息了。方才在抵抗之余,不止一次偷偷观察过江自流,这些攻击对他来说仿佛就像拍打苍蝇般简单,仅一招就可接下所有攻击,如果换作她自己那又会怎样?会不会也像昨晚那么狼狈?这样的差距实在是太远了。
她想,以江自流如此实力,竟然也走不出这片桃林,看来她该是好好修习一下奇门遁甲术。
待风停后,一切彻底安静下来,南宫徽走到一棵桃树前,轻轻摘下一枝桃花。忽然,几片花瓣晃落,化作几道极速飞行的白光。他忽然惊叫了一声,手一松,空枝落在地上,却没有消失。跟着几滴鲜血沿着南宫徽修长的手指滑落。
江自流脸色一变,道:“南宫,切莫擅自乱动。这些都是幻像,更切确的说,是幻化成桃花瓣的法术机关。”
南宫徽扯下一块布,包扎住手上的伤口,一边道:“我看这些光总是往桃花树里去,又在那里飞出来,我就觉得有奇怪……”
苏槿棠道:“这也是我刚刚正想说的,虽然判断出奇门方位不算太难,但是如果这个人也懂得使用幻术,那要准确判断破阵的方位,就太难了。”
江自流轻笑道:“这么说,我们还是得靠苏姑娘对奇门的学识,才可逃过一劫了。那便烦请姑娘出手相救。”
苏槿棠闭上眼想了一下,道:“好,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请讲。”
“我……还没想到。带出去以后你们再还我这个人情吧!”
南宫徽不屑挑眉,低声道:“希望你不要耍什么手段才好……”
江自流拍拍南宫徽的肩膀,示意他不要扰事生非,才对苏槿棠道:“好。”
苏槿棠道:“天师道虽然也研究易中得法术,但若非专究此道,也只是学习剑术道法而已。不过,还好我还曾翻阅过这些书籍,我看来这就是奇门中的‘八门遁甲了’。”
江心石似乎听得很有兴趣:“何为‘八门遁甲’。”
“就是八卦中对应八个方位而分的八门,即是开、休、生、伤、杜、景、惊、死八门,它是堪舆与阴阳术的一种。我们现在桃花林中,这里的一事一物都再敌人的掌控之中,这种情况下最容易迷失方向。但八门可辨吉凶,只要知道我们的时间方位,就可以找到出路……”
南宫徽一悟,道:“所以他要赶在天黑之前杀人灭口,因为随着时间转移,阵法的能量强弱会随之改变。”
苏槿棠点头道:“不错。现在最先避开的是伤、惊、死三个凶门,现在是在坤、兌、坎宫。所以,西方北方都不能走。”
南宫徽道:“但是我们正是要往西走。”
“那你还要不要命了?不管要去哪里,那也得活着走出这里再说吧!。”
江自流:“苏姑娘,方才我们恰恰遇到凶险,这里大概便是伤门,或是惊门了吧。”
苏槿棠思量一下,道:“就算不是也应该近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往回走?依我看,布阵之人应藏身死门,他肯定会用尽方法引我们到那里去。我们还是东南方去吧,那里比较安全。”
江自流伸手示意且慢,道:“等我们去到,估计这人盘就已经再次转换了。我们不如直接去北边的死门。”
南宫徽不解地笑了一声:“小江你疯了?虽然我不懂这什么奇门遁甲,但这死门我也知道是最凶险的,你还朝那边去?”
江自流一笑,摇头道:“不是说布阵者藏匿在死门吗?不去找他,怎么破阵?”
苏槿棠点头:“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但是,我们身处法阵之中,就算你身手比他好,你也未必不会吃亏。”
“没关系,这阵法有些熟悉,我想见见这布阵之人。”
江心石道:“大哥,你跟他认识吗?”
江自流摇头:“不知道,找到了便会知晓。”
一行人大约向着北面走了将近半个时辰,却还不见一个人影,想不到这片桃林大成这样,或者是,这一切都是幻觉?
南宫徽开始有些担心,道:“小江,我们会不会走错了?还是他又用幻术引我们去别的地方?”
江自流摇头道:“不清楚。但我觉得可能甚微,若想借用死门之力杀我们,应尽快在一定时间内让我们靠近死门才是。又或许,他只是在玩弄我们?”
接着已经到了河边上,再无去路。可是对岸仍然长满桃花,好像没有止境。四人停下脚步,不知所措,也开始四周张望有没有桥或者小舟。
南宫徽感觉到身上的衣服无风而动,他侧头看见江自流,他身上正泛着淡淡的光芒。想道,此时他祭出法术,难道这里便是施法者的藏身之地?
苏槿棠和江心石也感觉到有不同寻常的气息,正要拔出武器防范未然。
“我们到了,凝神。”江自流道,慢慢地往前两步。
“小心。”南宫徽轻声道。
江自流伸手探向前方的空气,他的指尖仿佛正触碰着
须臾之间,南宫徽觉得一阵眩晕,非常突然,那瞬间脸上的惊讶仿佛是对死亡的恐惧。他矍然望着眼前那转瞬即逝,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桃花树在扭曲,河流在扭曲,站在身边的苏槿棠和江心石的身影也在扭曲,但依稀能看到两人的身躯也在摇晃。他瞟了江自流的身影,似乎也就只有他依旧屹立着。
他不敢再多看几眼,不然都要恶心到吐出来。
忽而一阵劲风逼来,白光四起,正朝着这边射来。南宫徽头皮发麻,这些不就是刚才熟悉的那些白芒,难不成刚到死门就真的要死了?虽说不甘心,但已然晕得连手都感知不到了,这身体怕是要被扎成蜂窝了。
但这些光芒在逼近之时,似乎有法术在他们身边形成气壁,将白芒向四周弹开。他显然听到身旁传来江自流的声音:“奇门遁甲果真是名不虚传,如果是这么做呢?”
话罢,南宫徽他们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那种眩晕感又增加不少,感到天翻地覆,气血乱撞,几乎要晕厥过去了。眼前一切快速模糊,本来看得扭曲的江自流干脆截开两半,最后扭曲得什么都不是了。脑袋中嗡嗡作响,除了他们自己的喘息外,什么都听不见,四周就是一片混沌,越是认真辨别寻找,胸中那股闷气越是往上冲。
隐约间,出现的兵器气流碰撞的声音,还有风声,喘息声,祭出法术的声音。南宫徽干脆放弃挣扎,五感反而越来越清晰,他听出来这是打斗的声音。不知道江自流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才破了这死门的法阵,逼得对方现身。
那些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激烈,还发出两个人声,除了江自流的,似乎还有一个男子的声音。南宫徽现在视觉还未完全恢复,无论他怎么干着急,也只能认真听着周围的动静,来辨别他们的状况。
不远处发出一声低吟,有人受伤了,但不知道是谁。
“小江……”南宫徽极力撑起身体,试图寻找江自流的去向。
突然,一切幻像消失。刚站起来的南宫徽,气血回转,喉咙一哽,一口鲜血涌了出来,一个踉跄又无力地跪倒在地上。
“南宫……你怎么了?”江心石也伏在地上,他跟苏槿棠正要爬过来扶起南宫徽,两人除了脸色苍白了一些,看上去怎么都比南宫徽好多了。
而眼前的一切都让互相寒暄的三人马上收住了声。
江自流依旧安静地站在那儿,但是一行鲜血已经在嘴角流了下来。
面前,正跪着一个男子,大约跟南宫徽相仿的年纪。他单膝跪着,一只手紧紧捂住胸口,似乎受了内伤。他的伤势,倒是这里所有人里面伤得最重的一个。
而此刻,他眼中泛着怒火,慢慢抬起头,射向江自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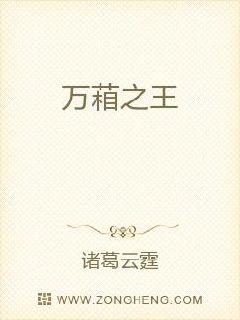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