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礼轻意重
这边九叔神神秘秘,关正心越是问他,他的嘴越像是封了蜡一样,半个字也不吐不露,只是微笑,愈加引起关正心的好奇,但既知他什么也不会说,便也不再问。
两人行走在关府之内,移步而景换:碎石铺就勤为径,玉白竹节垂帛林;群葩齐放衡吴院,日升月落观法亭。一步一景,让对这地方并不熟悉的关山闵看得欣喜,忍不住赞道:“真不愧是大柱国府,啧啧啧,气派。”
七弯八绕,终是抵到了马厩。老关家,以马闻名,马厩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其中有骏马,分三六九等。次些的马住在半面透风的木棚底下,下铺茅草。中置长食槽,饮水、干草等等悉储其中。且这些马都是被拴住的,横竖走不了多远,且十匹二十匹地挤在一起,可怜得就好似住在虾蟆陵中的一众百姓。只不过弹丸之地的两层楼间,便挤上数十人,腾挪闪转都不方便,更何况每日还要洗衣做饭。虽无缰绳拴之,又有何异?
稍好一些的,四五匹马挤在砖石砌成的马厩之中。这些马都算是上等的好马了,什么汗血马、赤影马,乌骓马什么的。这些马倒没那么凄惨,虽然戴着马辔,但所幸没有被栓死,盖因这些马都被关家好手训得差不多了,再没有桀骜的野性。如此一来,自然放心他们。比之最次的马,它们每匹马都有独立的饮水槽,除干草之外也能时不时吃些细糠,日子过得可算是有滋有味。
而那最最上等的,所住之处,鹅绒马床,独立洗浴,西域奇瓜异果。诸如此类,终难尽述。它们生活的豪贵,又岂是其他马能想敢想的?上等马中,包括那关正心的踏雪乌骓,灵性十足。那上屋一跃的功力,若非天赋异禀,又怎能及?
关正心路过自个儿的马厩时,唤道:“追云追云。”追云自是那匹踏雪乌骓的名字。
刹那风声鹤唳,又如浊浪击空。马厩帘子被奔风所卷,呼啦啦作响,那匹乌骓身影闪现如电,如一堵墙般朝两人压了过来。关山闵心中一恶,忙道:“侄儿当心!”正欲探手将他拉到一边,忽然万风顿止,乌骓堪堪停在了关正心身前,刚好够它伸出脖子,在主人脸上轻轻一舔。
关山闵但觉天地霎时安静下来,只听到己心扑扑狂跳的声音,半晌说不出话来。但见侄子伸出手轻轻抚了抚乌骓的马鬃:“乖追云,好追云,我就是路过这里,想到了你。没什么别的事儿,你就先回吧。”紧接着又是一阵风,追云眨眼间便消失不见,唯余帘子依旧波动不止。
关山闵长吁了一口气,暗羡关正心福气,心道自己的驯马之术是决计不如他的,刚才这下可真显得自个儿太没见识了。岔开来,往前一指:“马上就到了,咱们快学走罢。”
关正心搓搓手,咧嘴开怀:“是什么好吃的呢?”
一方斗室之中,竟摆满了三个红木金漆大箱子。关正心看得都傻了眼:“这么多!”
关山闵道:“你先别急,待我一个个打开给你看看。”
第一个箱子打开,里面全都是稻谷子。第二个箱子打开,竟也都是稻谷子。看到这里,关正心大为失望,不由地问道:“咋都是这些啊?九叔,你也忒没诚意了吧。”
九叔嘿嘿一笑:“你自己去扒拉扒拉,看看里面都是些啥再来呛你九叔。”
关正心点点头,手伸进一片灿黄之中。叮的一下,他的手忽然摸到了什么硬邦邦,滑溜溜的物事。眉头一皱,遂伸手探进去。拿出来,金黄色的稻谷子簌簌落下,手中抓着一个圆肚窄喉红塞子的瓷瓶。打开瓷瓶一闻,猛地一咳:“就是,这是什么酒啊?”
九叔刚从第三个箱子里拿出一个皮制酒囊,还有一个油皮纸包。闻声转了过来:“哪一个,让我闻闻。”说着,放下手中的物事,赶了过来,拿起酒瓶,放在鼻子边使劲嗅了嗅:“哦,这个啊。小子着实见得少,这个是著名的贵州茅台,没听说过?”
关正心挠挠头:“贵州茅台?听说是听说过,从来没尝过。”
“你要不要尝一尝?”九叔说着,递给了侄子一个专喝烧酒的小杯子,琉璃剔透,纯色的茅台倒进去,清冽可见,也是赏眼。
关正心本拟说:不不不,这么烈的酒,我还是不喝为好。但渐渐习惯了茅台的气味,竟在其中觉察到了些五谷的香气,不自觉地舔舔嘴唇,轻抿一口,随即剧烈地吐了起来:“呕,这酒怎么是这个味道啊,太难喝了吧。”
“哈哈哈,小侄子还是嫩了些。”九叔说着,接过那杯酒,脖子一仰,喝了个干净:“淡的和水一样。”
关正心嘟嘟嘴,没有接话。九叔把刚刚翻出来的那酒囊递了过来。酒囊也不知是用什么动物的皮革制成,摸上去糙糙的。月牙形状,握在手中,倒好似握着一把弯刀。皮革上只淡淡几笔,便勾勒出了明月天山,苍茫云海。虽只几笔,却也看得关正心心旷神怡,喃喃道:“要是我也能去辄边塞就好了。”
拔开塞子,但闻一阵比方才更刺鼻的酒香。可关正心闻到了,却不逃避。连酒杯都不要,“咕咚”就是一大口下去,顿时感觉身子已在那遥遥的西北戈壁,黄沙漫漫,驼铃阵阵,耳畔呼啸而过的猎猎西风仿佛还夹杂着幽怨的胡笳,悲凉的羌笛。神游大漠,梦回千古;似幻似真,如痴如醉。
忽听九叔道:“嘿嘿,瞧把你给醉的。”瞬间把关正心从神游之中拉了回来,眼见自己身处斗室之中,顿感枷锁俯身,不由生出一阵落寞之感。
九叔接着道:“瞧你的脸红的哟,像什么一样。”关正心闻言,忙去摸自己的脸颊,果然滚烫似火。
九叔一只手接过关正心手中的酒囊,一只手把油纸包递给他:“喏,喝这酒当配肉干,乃是一绝。”
油纸包打开,里面的肉干呈条状,深褐颜色,极少处有一些或白或黄的油脂。关正心问道:“这是什么肉啊?”九叔答道:“这是西域的野马肉。”
听到此处,关正心“啊”的一声惊叫:“马肉?马儿是我们的好朋友,怎么可以吃马肉?”眼中隐隐流露出悲愤,好像马上就要忿然离席。
关山闵白了他一眼:“不吃就不吃,还摆那么多臭规矩。鸡鸭鹅,牛羊鱼,哪一个不是咱们的好朋友,还不是该吃照吃?湘西那边还吃狗肉火锅哩,说到这个,啊,我又要流口水咯。湘西真是个好地方,风景美,好吃的多,姑娘也好看,没事的时候我还要再去一趟。”
关正心愈听愈怒,脱口道:“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但见九叔也不管他,抓起一条肉干就往嘴里塞,嚼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关正心见状,索性将头扭了过去,不去看他。但听九叔嘴吃得“吧唧吧唧”响,实在忍不住,还是偷偷侧目,手指在桌子上不住叩击。
九叔嘴中嚼着马肉,一指桌子上的那些肉干:“吃呗,我是你九叔,又不会笑话你。”
关正心听了,咽咽口水,终不管那么多,抓起一条,撕开,随后塞进嘴中。他吃在嘴里,但见两腮不住鼓动,太阳穴上下起伏。忽然,双目瞪大,拼命点头,竖起大拇指:“好吃好吃,吃出野味来了。”
九叔笑道:“对嘛,骑的马是骑的马,吃的马是吃的马,一马归一马,哪有那么多这不行那不行的?我们当年......”说到一半,忽地又不说下去了。
关正心接着问道:“九叔,你们当年怎么样啊?”
九叔嚼着马肉的嘴忽地停了下来,喃喃道:“吃腊马肉,当配这西风烈。”另一只手拇指轻弹,“叭”地打开瓶塞,那股塞外黄沙的气息登时扑面而来。
关正心见九叔话说一半不说完,则愈是着急,急吼吼道:“九叔,你们当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九叔竟浑似没听见他讲话似的,拎起酒囊,咕嘟一大口灌下去。袖子一抹嘴,双眼泛红,泪光晶莹,忽地站起,朗声念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念罢也不做下,只是两颗豆大的泪珠滚滚滑落,让侄儿看得分外揪心,遂不敢再问,只是默默低下头,玩弄着手指。
忽听得前厅又传来打斗声,关正心一皱眉:“爹爹又是在和谁打?”关府之中,关山敬时常邀人前来切磋,是以正理正心两兄弟早已习惯了。
此刻关山闵也从西风烈的悲怆中抽离了出来,迷离的双眼也骤然变得清亮狡黠,拍拍侄子的肩头:“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待得叔侄二人奔至前厅,见了院中场景,不自觉相望一眼,哈哈大笑。
场中争斗的两人听到突如其来笑声,收手扭头,也望了过来。场边一个已年过三十的女子,凤眼柳眉,贝齿朱唇,见了两人,忙走来:“九哥,正心,你们好啊!”原来是关正心的小姑姑,“哟,才半年没见就长高了这么多。”
这边正心与小姑互相道好,那边九叔一下拍了拍方才正与关山敬打斗的人:“包大侠,你好啊。”包大侠笑着回道:“九哥你好。”
小姑拉住关山闵的手臂,摇道:“九哥你看,三哥也忒不讲理,我们一进来他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便和阿靖动上了手。您给评评理,这哥哥是怎么当的?”
关山闵笑道:“哈哈哈,婷儿你别急,我一进来他也是这般要试我武功,还不是被我......”瞧见哥哥炽怒的眼神,不由地吞吞口水,没说出下文。
一众人分别互道安好。小姑关婷儿拉过关正心的手:“来,也快二十了。小姑送你一样好东西。”
关正心心中一震。方才九叔也送自己礼物,现下小姑也送自己礼物。他心念闪动:今日到底是什么日子?离自己的二十生辰分明还有一个多月的光景呀。
正想着,手中便多了一个红木制方盒子,盒上雕着一棵大树。乍一看,却是一棵平平无奇的大树。可是稍微细心些许便会发觉,这颗树竟有两只树根。根起之处,两树主干竟交错连结在了一块儿,盘旋而上。其上树枝更是互相纠葛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冠处叶盛,张开似孔雀的屏尾,赏心悦目。
盒盖揭开,竟是一只精美的银簪。簪头的鸟双翼高展,将欲飞起。鸟颈处伸出两根脖子,也像盒盖上的连理树一般,相互盘旋缠绕在一块儿,直至头部。头部两只鸟喙紧紧贴合在一起。
连理枝、比翼鸟,这些意象关正心也都识得。他抬起头,朝姑姑皱了皱眉头。关婷儿嘴角微扬,笑道:“二十了,若遇上了相中的姑娘。喏,这簪子,你是聪明娃子,自理会得姑姑的意思。”
关正心脸“刷”地一下涨得通红,缓缓低下头,却还是难掩那抹青涩的春笑。只觉日光灿烂,照在身上,暖酥酥的,格外舒服。
忽然,指节上长满老茧的大手伸了过来,轻轻盖上了盒子。关正心还没觉过味过来,盒子便从手中被抽走。他微一惊愕,顺着那手望了过去,目光正撞见自己父亲微笑的面庞。可那微笑,却似挂上去的一样,眼角与嘴角边挤出了千沟万壑的深纹。却见他转向幺妹,笑道:“婷儿你可真是胡闹。正心他还小,这礼物便由我先替他保管着罢。”
关婷儿小脸一板,眉宇间有怒意上攀,轻叱道:“我那是送给正心的礼物,至于收不收,看他自己罢。”嘴上说得客气,身形闪动,却已伸长皓臂,便要从兄长手上夺来木盒。
关山敬也不客气,身形微侧,拿着木盒的那只臂膀高举起来,手一松,那盒子便顺着自己的小臂,轻轻滑落入自己的宽袖之中,叫关婷儿再夺不到了。他望着面前怒目圆瞪,气得双腮绯红的妹妹,咬咬嘴唇,仍是没摘下那挂上去的微笑:“小妹啊,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是再清楚没有的。只是,婚嫁之事,可不是孩子他一个人的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要讲个门当户对的。都不说风尘女子了,若是孩儿他找了个整日价刀尖儿舔血的草莽女子,你说,岂不是太丢我们老关家的颜面了?”
听了此话,关婷儿鼻息愈发粗重,拳头之间的咯咯暴响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关正心以前也从父辈之间不投机的话锋之中稍听出些玄机,可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让兄妹之间动辄翻脸,他却是一概不知。倒也试过从九叔那儿探出些口风,但言及此间,九叔每次都会垂下头,低声说句:“父辈的事儿是父辈的事儿,你莫操心。”
见两人剑拔弩张,关正心心中害怕,悄悄隐到关山闵身后,以观其变,心仍是止不住地砰砰狂跳。
忽听场边那人发话:“好了,婷妹,过来罢。”原来是那关山闵呼之为包大侠,而关婷儿呼之为阿靖的包靖,剑眉星眼,阔口方腮。一身腱子肉,生得雄浑非常。听到包靖的话,方才还激愤得几已跳起的关婷儿,忽地就变成了一只温驯的小猫崽,蹿到包靖身边,轻轻倚在他怀中。
包靖的大手轻柔搭上关婷儿的肩膀:“好啦婷妹,三哥确是长我们不少,历事自是比我们多,听听他的定有好处。再者了,长兄为父,撇开事情对错不谈,我们待他礼节上可不能有失。”温文尔雅,有礼有节,很难让人将的谈吐与健硕伟岸的身子联系在一起。
关正心见势头稍缓,偷偷瞅向父亲,见他脸上紧绷着的假笑终是缓了许些,自己的心头也一道放松了下来。
忽有家仆朝庭院中奔走而来,直直来到关山敬面前,跪而抱拳:“大人,客人来了。”
关山敬一听,笑逐颜开:“起来罢,跟我迎客人去。”遂挥挥袖子,大步朝大门口的方向走去。
关正心见父亲背向大伙儿,这才敢走出,来到关婷儿身边,悄声道:“没事儿的,姑姑,礼物被收走了,您的心意我却收到啦。”
关婷儿斜了眼三哥离去的背影,压低声音道:“别听你爹爹说的什么门当户对,都是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看到钟意的姑娘尽管放开去追便是,莫管那些条条框框。”
关正心舔舔嘴唇,没有应答。关婷儿忽然感到包靖拉了拉自己的衣袖,对上眼色。夫妻并辔多年,二人之间几已无需言语便可畅通无阻地交流,心意相通,羡煞旁人。是以一见他的眼色,便知他示意自己不要再说下去。关婷儿既心领神会,旋即缄口。
即便如此,关山敬也已听见了关婷儿说与正心的话儿,停下脚步,回身招手:“来,正心,和姑姑呆在一起的机会有的是,咱们先去看看有哪些客人罢。”
关正心不敢拂逆其意,望了一眼姑姑,见她翻了个白眼,便也吐吐舌头,转身向父亲小跑坠去。
不知何时,关山闵已然来到了婷儿身侧,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关婷儿也跟着叹了一口气:“咱们这位三哥啊,当上大柱国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好怀念以前的那个三哥啊。”
关山闵喃喃道:“其实他向来如此,只是以前较疼你,而你却不知罢了。”
见幺妹朝自己疑惑地眨了眨眼睛,关山闵摇摇头,叹道:“若非如此,他又是如何当上大柱国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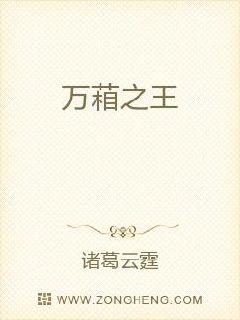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