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少女退避,信笺显危机
季明昭瞧着田闯的背影微微紧了紧眉,自顾自地说道:“这个田闯,怕是命不久矣了。”
施阆闻言急凑上前问道:“季兄何出此言?”
季明昭身形微侧,缓缓说道:“众所周知盛莽的‘滚雷杖法’功力奇强,除非是武功修为高的人迎战,否则只能是以卵击石。咱们显然能看见田闯与盛莽的实力悬殊,但他并未在当场被击成重伤。我适才仔细观察了盛莽的出招,他用杖只使了蛮力,所以田闯轻易的招架住了他的虚招,实招则是在他们兵器相搏的刹那,盛莽震了内功传入了田闯的体内,击伤了他的五脏六腑。若我没有猜错,田闯已经受了很重的内伤,如无良医,恐怕活不了几日。”
“哈哈哈...”少女拍手笑道:“季公子真是分析的头头是道。我起初以为,什么‘南季北江’都是不要脸的富家公子给自己起的不要脸的名号呢,没想到,你还真有几分本事。”
季明昭也不怒,微微颔首,“多谢姑娘夸奖。”他又两眼一疑,问道:“只是在下不解,既然姑娘想要他死,为何不当场打死他,而是要他受尽苦痛而亡呢?”
少女现出一副无辜的模样,疑道:“谁想要他死?我?可不是我在和他打。”她转身蹙着眉,却一副幸灾乐祸的神情问向盛莽:“盛老四,季公子问你呢。”
盛莽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说道:“姑奶奶,这可是您说要我杀了他,但也是您先前和我们说不要杀人惹麻烦,这...我才用这招的啊。是他武功不济,若真死了,我也没有法子。”
少女脸色一变,大眼瞪着盛莽,似乎他说了不该说的话。突然盛莽的胳膊被重击了一下,传来了蒙徙的声音:“蠢东西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盛莽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想要讨好少女,季明昭的笑声却响了起来:“原来姑娘还怕惹祸上身呢?看来是我高估你了。”
少女转头温和地看着季明昭,说着:“我不杀他们,是因为他们不配被我杀。但季公子就不一样了,若我杀了你,说不定江湖上也给我安个什么名号,我岂不也是威震武林之辈了。”少女话音一落,脸上的悦色霎时没了踪影,她右手迅速甩起,一粒红枣就飞了出去,速度奇快。
季明昭瞧着疾来的物体,右手一出,孰料在季明昭出手之前飞来了一根银针,连着红枣一同插入了树干里。
东方翊觉得眼前闪过了什么东西,以为是错觉的他摇摇头揉了揉眼睛,看到眼前的几人仍然是一副吃惊的神情,他才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只见树干上留下了一个貌似极深的小窟窿,尽管他没有瞧出个所以然,但也知道来者是一个武功极高的人。
少女痴痴地看着那个窟窿,此时天空漫出了一道低沉的声音:“你还要玩到什么时候?”
“传音大法?”施阆惊呼出声。
“传音大法是什么?”东方翊悄声问道。
“传音大法可以将自己的声音传到数里乃至数十里之外,一般使这门功夫的的人,武功修为都是极高的。”施阆给他解释着。
东方翊点着头,还想再听,声音却再也没有传来。
蒙徙看着少女的表情有了一丝忌惮,便凑到她耳边问道:“姑奶奶,怎么办?”
少女回神,又露出了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撇了撇嘴,说道:“拿着东西,咱们走。”说完还不屑地瞥了一眼季明昭一行人。
少女一走,季明昭便缓缓迈到了那棵树面前,手指掠过了那个窟窿眼,若有所思着。施阆看着他仿佛思索的模样,问道:“季兄在想什么?”
季明昭回神道:“我在想,什么样的人可以让‘贺兰五绝’唯命是从。又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让‘贺兰五绝’唯命是从的人唯命是从。”
施阆也陷入了深思,这时一直没有作声的呼先扬开了口:“弱者依附强者,强者依附更强者,这本就是这个江湖的生存法则,公子不必放在心上。”
季明昭点点头,呼先扬又揪着下巴的一小撮胡子说道:“不过...我想我能猜到他们的身份。”
“哦?”季明昭疑惑,恭敬地拱手问道:“明昭愿闻其详。”
呼先扬说着:“咱们有目共睹了那名少女有着不俗的武功,那神秘人的传音大法和他使暗器的功力,也证明了他武功修为不弱,由此可见他们的武功应当在伯仲之间,且那名少女听见传音的神情还有那神秘人的言语和语气,都能瞧出他们的地位应当是相当的。”
季明昭肃然起敬,频频点头以示赞同。呼先扬一笑,却听他问道:“不知公子可有瞧见那根银针的模样?”
季明昭点头,言语却不是那么的有底气:“瞧是瞧见了,觉得很眼熟,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暗器。”
“那是独步春。”呼先扬蓦地严肃了起来。
“独步春?!”施阆惊道,“危月宫的独步春么?”
呼先扬点头道:“独步春只是一根细小银针,和天狼帮的‘穿杨箭’,近水阁的‘水漫青山’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就连和异蛇派的‘灵骨刺’比较,都逊色不少。若说特别之处,据说是因为它极其美观,在不到两寸之地精雕细刻了十数朵不同品种的梅花,且均是人工雕刻,耗时耗力,产量稀少,还不实用。不过它肉眼难见,若非眼疾手快或内力深厚之人,倒还真辩不出它的踪迹。”
季明昭听完这番话,又瞄了一眼树干上的窟窿,悠悠说着:“危月宫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
施阆勾住他的肩膀拍了拍,说道:“危月宫的势力遍布武林,行事作风颇为古怪,季兄别太多想。”
呼先扬顿了顿,又继续说道:“‘独步春’美而无用,却成为了危月宫的‘暗器之首’,全因它是现危月宫少主月惜迟所创,据说那月惜迟极其奢靡,喜欢华而不实的东西。再加上那暗器做工繁琐,产量极少,所以能用上那暗器的人,便屈指可数。危月宫少主用的东西,试问普通的门人怎么会用到?那名男子武功修为高,又能使‘独步春’,细想下来,只有‘修罗鬼魅’了。”
季明昭心头一紧,都没发现自己握紧了拳头,“修罗鬼魅”是危月宫的四大高手,神出鬼没武功高强,从不在江湖中露面。施阆在一旁惊问道:“那依照呼先生之前所猜测的话,那名少女,是...魅吟?”
呼先扬摇头道:“不尽然,危月宫的武功高强的女子不在少数,我也并未见过他们的人,不好猜测,我能断出那名男子是‘修罗鬼魅’里的三兄弟之一已经是用尽头脑了。”
呼先扬说着便笑了出来,缓和了他们如临大敌的气氛。季明昭也跟着笑了起来,他对呼先扬颇具恭敬地颔首拱手道:“呼大哥见识颇多,心思缜密,明昭真是内外感佩。”
呼先扬摆摆手道:“公子哪里话,我只不过比你多活了十来个年头,多走了十来年路,若要拿公子如今与我当年比,我才是望尘莫及啊。”说完之后又正言道:“危月宫行踪诡秘,作风怪异。咱们还是小心为好。即便咱们与他们有‘些许交情’,但时过境迁,咱们也不得不防。”
季明昭看着呼先扬难得的严肃的模样,知道他意有所指,于是也郑重地点头回应。
一道响雷落下,施阆瞧着缓和的气氛又凝固了起来,他看了看天色,便对季明昭说:“瞧着要落雨了,此地不宜久留,我和东方老弟打算去方府,季兄可要一起?”
“我们还有要事在身,下回再去叨扰方老爷罢。”季明昭婉拒道。
“好,那咱们后会有期。”四人互相行了礼便分道而行。
方府。施阆和东方翊相继踏进了门槛。
方府管家喜出望外跑进去通报:“老爷,东方公子和施公子来了!”
“快快快,快请进来。”
“拜见方世伯。”“拜见方伯父。”两人同时俯首作揖道。
“哈哈哈,好好好,都好。”方浔高兴得快语无伦次,“我前几日才收到你们父亲传过来的书信,正念着你们呢,这就来了,快叫人上茶,再吩咐膳房做些点心上来。”他吩咐着管家。
“不,不用了方世伯,我们在松鹤楼吃过了。”东方翊急忙摆手。
“松鹤楼?你们去松鹤楼了?”方浔疑惑道。
施阆生怕方浔多想,急忙圆道:“是我听闻方伯父的松鹤楼内的姑苏卤鸭乃江南一绝,一时垂涎,就急不可耐先去品尝了下,倒一时忘了来拜见。”
“哈哈,不打紧的,你们若喜欢,我每日命人做几道菜从松鹤楼送过来,你们就在这多待些时日。”方家世代从商,方浔虽说每日酒池肉林,可却不像普通商贾人士一样脑满肥肠,举手投足间也尽显儒雅。
“父亲。是施阆哥哥来了么?”这时一名少女轻跑进来。她明眸皓齿,皎若秋月,模样虽谈不上倾国倾城,却也是难得的美人。浅绿色的长裙,袖口用银丝勾出了几朵牡丹,艳而不俗,头发松松的绾了一个半髻,斜插着一只和田玉雕的芙蓉花钗。胸前是淡黄色锦缎裹胸,薄唇用樱色唇脂点缀,倒略显俏皮,在灯影摇晃下更显楚楚动人。
东方翊望着她,只觉美人如斯,不由心生悸动。
“过来,这是你东方世伯家的公子,你们幼时还是玩伴呢。”方浔向女儿介绍着。
方珩顿时没了适才的活泼,微微福身向东方翊行了个礼。她自然知道眼前这人是从小与她定亲的男子,不过对他的印象也止步于孩童时期,想到这,不由得心中一紧,她还不想嫁人,更不想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
东方翊也回了个礼,时隔多年后再见面,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施阆见气氛微妙,便开口道:“我们的方小姐真乃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上回见你,还饮啖兼人,怎么现在却堪比飞燕了。”
“上次见施阆哥哥就怪会打趣人,几年不见,功夫有没有长进不知道,嘴上功夫倒是精进不少。”方珩虽然反驳着,可是脸却不自觉得红了起来。
“珩儿,不许无礼。”方浔见状急忙出来制止。方珩从小养尊处优,虽然脾气刁钻,但平常也算得上知书达礼,可一见到施阆,两个人就如水火不容般,非得争个你高我低才肯罢休。方浔自然知道其中的缘由,却也不说破,毕竟方家和东方家有姻亲,即便日后为了爱女可以出尔反尔,但是琼楼和南宫家也有姻亲,自己家与南宫家也有些许利益往来,施阆终究不是上乘人选。
东方翊看着眼前这一幕,胸口有种道不明的情绪,便不想久留,说道:“方世伯,这段时间赶路赶得急,现下有些累了。”方浔看出了他的窘态,也没有多说,吩咐了下人带他到早已备好的厢房。
东方翊在厢房放好了行李准备睡下,突然看见了临走时父亲叮嘱他交给方浔的信。本想明日再送去,但是想到父亲严肃地叮嘱他亲自送到方浔手上,想必是很重要的事情,且施阆也在府上,虽然他们二人一同长大,情谊深厚,东方家和琼楼生意上也有不少来往,但琼楼楼主施中谷却是老谋深算,表里不一之人,武林中更有很多事情都是他暗箱操作,这一切也是东方翊从父亲口中无意得知的。想到这些,决定起身去方浔的房间。
“叩叩叩”,“方世伯,睡下了么?”
“东方贤侄?进来罢。”
“晚辈深夜前来,不知可扰世伯清梦?”
“无妨,我暂未睡下,不知贤侄前来,是有何要事么?”
“父亲交予我一封信,说要我亲自送到世伯手上。”
方浔拿过信,越往下读眉头越紧,看完之后迟迟没有合上,眉头仍然深锁。随后,走到书案旁,取下了雁足灯罩,将其付之一炬。
“世伯,可是发生了什么事?”东方翊疑惑道。
“没什么大事,就是提起了你和珩儿的婚事,还有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方浔若无其事地说道。
显然不是。东方翊心想,瞧他骤然严肃的模样定不是婚约这般易事,可方浔没有说,便是不想告知他,既然如此,也不好再问。
“那世伯若无其他事,我便回去睡了。”说罢就要往门口走去。
“贤侄。”方浔叫住了他。
东方翊回身疑惑地看着他。
“既然你这次来了,就多待些时日,正好和我多说说话,顺便也陪陪珩儿,她母亲离世早,没有其他手足,我陪她的时间也不多,她终归也是要嫁与你的,你们好好相处,我也早些放下心来。”方浔直截了当地说道。
东方翊被方浔这么一说,更是笃定信上所言是十分要紧的事情,他不敢多问,只能强扯出个微笑,“是,世伯。”
回到厢房的东方翊,虽然舟车劳顿,却一夜未眠。同样,另一端辗转未眠的方珩也心事重重。十年前方家与东方家结下媒妁之约,东方家承诺待独子成人便迎娶方家之女,那时候方家之女也年芳十八,正是适婚年龄。可今日前来,父亲和东方翊都没有提起迎娶之事,也许父亲暂不想让她出嫁,又或者东方家有变故,想着想着,方珩定了定神,没半晌就沉沉睡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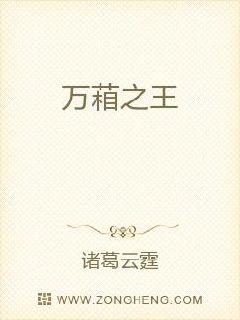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