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魔剑
望着断桥对面、手持巨剑的半裸少女,安生不由得沉默下来。
冷凌霜经过刚才一番恶战,早已手足酸软,已经提不起力气再战,只能软软倚着廊桥雕柱;低头一瞧,桥底下那名巨汉的面孔,不知何时已不再狰狞,空洞的眼瞳终于又是黑多于白,只是随着口鼻中不断溢出的鲜血,视焦逐渐散在虚空中。
“你叫阿傻,是不是?”她俯下桥面断口,扬声叫道。名唤“阿傻”的巨汉颤抖着仰起脸,小眼珠转了几转,被雨打湿的粗糙皮肤显得灰白。
“二…二掌院…”一阵抽搐,终于斜斜垂颈,再无声息,显然已经死了。
冷凌霜忽有些鼻酸,看着对岸怪物一般的秋月,喃喃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来…像是被附身了似的。”安生突然开口。
“附身?”冷凌霜微眯杏眼,似是十分迷惘。
安生指着那把巨间。“好像拿了那把巨剑,就会变成力气很大的怪物。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目前看起来似乎就是这样。”
“是么?”
“我也不知道。”安生微一沉吟:“但凡事皆有因果,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抬头见断桥对面的秋月正缓缓后退,心念一动,赶紧转头问:“二掌院,你还能走动么?依我看,此地不宜久留。”
冷凌霜暗提真气,拄着寒霜剑缓缓起身,微微踉跄些个,旋又站稳。她在百花轩第四代弟子中号称武魁,代师传艺多年,内力根基极为深厚,又有天生的臂力,便只这么休养半刻,已然恢复行动能力。
“还可以。”她对安生说:“我们先回岸上去,凉榭那厢已无舟艇,暂无危险。待与我掌门师姊从长计议,再做……”话说到一半,突然愣住。
对面的断桥之上,只见一个小小黑点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显露出一个小小身影,扛着一把铁链巨剑。
冷凌霜“呀”的一声轻呼,突然被横抱起来,安生头也不回,径直向岸上狂奔!
“二掌院得罪啦!事出突然,还请见谅!”
冷凌霜不及责他唐突,就着颈窝向后一瞧,秋月已奔至断口,一跃而起,巨剑往湖间桥基一撑,连人带剑越了过来!廊桥尽头,秋兰身子未恢复,还在慢慢行走,眨眼间安生已至,只听怀里冷凌霜急道:“快……快放我下来!你带着秋兰先逃走!”
安生登时醒悟,连忙将她放下,一把抄起秋兰就背在背上。
那把巨剑寄生到秋月身上之后,似乎又撷取了秋月身轻如燕的优点,一反巨汉行动迟缓的缺点,动作不知快了多少倍,越过断桥后仅仅几个起落,距安生等已不足十丈。
冷凌霜指着身后小山头上层层迭迭的建筑,对秋兰叫道:“带这位兄弟去掌门闭关处避难!沿途遇着其他人,也都一并带去。”
秋兰点了点头伏在安生背上点了点头。
安生却未跟随,只问:“二掌院你呢?”
冷凌霜微微一笑:“我将她引开,少时便至。”又见他不肯舍己离去,心中一动,又道:“我轻功远胜我师妹,要逃不难。有你们在,反而累赘。”
安生这才放了心,负着秋兰离去。
冷凌霜存了舍生之念,心中暗祷:“秋月,你知道师姊一向疼你。你虽被妖邪附了身,愿你良善体贴的心肠莫尽舍去,师姊一定不伤害你。”双手握紧寒霜剑,摆开架势、一力当关,被雨打湿的红衫在风中猎猎飘扬,果不负“血染秋霜”的豪气与美名。
小秋月扛着巨剑,飞步疾奔而来,冷凌霜觑准来势,咬牙挥剑迎上,谁知秋月却一跃而起,倏地越过她的头顶,径往山头的屋舍处奔去!
“师……师姊!”秋兰惊慌的语声透雨传至,风中听来倍觉凄厉:“她…她一直追我们!一直…一直在追我们啦!”
冷凌霜一击失的,差点失去平衡,好不容易稳住身子,却见秋月一路衔尾,安生背着秋兰,始终离秋月有三五丈的距离。倒是沿途有许多躲在屋舍里的女弟子们闻声出来观视,秋月巨剑随意一挥,雨帘间鲜血四溅,不知杀伤多少、又死了几个,庄院里一片娇声哀唤。
冷凌霜急着大叫:“都进屋去!都进屋去!”忽觉侥幸:“这少年…好厉害的脚力!”
她见安生年纪轻轻,料他撑持不久,一咬牙拔下头上发钗,“飕!”朝秋月背心射去!还怕下手重了,特地留力五成;谁知秋月好似背后生眼,身子一让,轻松避过。
冷凌霜接连出手,俱都无功。秋月速度不减,倒是秋兰,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惹得她惊叫连连。
安生回见一路三三两两倒着女弟子们,个个死活不知,心想不是办法,对秋兰叫道:“我们不去山头了,到外厅去!”
秋兰吓得魂飞魄散:“你…你疯啦?我不要,我不要!”无奈安生力气大得惊人,身不由己,被他背着掉头,贴着一幢屋角转了大弯。
秋月动作虽快,却似乎不会转弯,径直追出十丈余,这才歪歪倒倒转了个方向。一消一长间,安生携二姝奔下小丘,与迎面追来的冷凌霜会合。
“怎不听我的话?”冷凌霜继续奔跑,语带责备:“若教那……教秋月追上,这可怎么办才好!”
秋兰缓过气来,哇哇大叫:“霜姊,不是我,是他!”
安生背着秋兰,与冷凌霜并肩齐奔,突然开口:“二掌院,那位秋月姑娘一直追着我们,若然引至贵派弟子聚集之处,死伤必惨。我们还是逃到外头去好了,先离此地,再找安全之处避难。”
秋兰恼他带自己犯险,嘴上不饶:“上哪里去?你家么?”
安生认真想了片刻,居然大点其头:“本城主上是封爵王侯,无双城内有五千精甲驻扎,城下又离江南道护军府甚近,倒是个避难的好地方。”
秋兰哼哼冷笑,一想这人呆得生趣,居然连抬杠也分不出,想着想着忍不住一声噗哧,这回倒是真心笑了出来。
冷凌霜听他说得有理,暗骂自己胡涂,又想:“这少年根基不恶,不知是谁的门下?于奔行之间犹能开口说话,殊不简单。”
四人来至停客的外厅,安生随手拉倒桌椅,形成路障,一面径往内进狂奔。冷凌霜蹙眉道:“你要到哪儿去?”
安生不答,带着她转了几转,来到后进灶房外,赫见一辆篷顶马车停在空地上,车辕套了匹瘦马还未解下,车座上一大片深褐血渍,里外却不见人影。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车?”冷凌霜不禁起疑。
安生面皮一红,直抓后脑勺:“我在前厅等候时,听见这个方向有马嘶的声音,其实也不确定有没有车,算是运气好蒙中的。”
冷凌霜想起他曾在雨瀑中听见远处的尖叫声,犹在自己之前,暗暗纳罕。
四人上了车,冷凌霜手握缰绳,驾着马车往大门外急驶。忽听哗啦一声,秋月砍开前厅七横八竖的桌椅路障,飞身追了上来。
冷凌霜驾驭之术极精,操控车辆左弯右绕,在曲折的内院里如屡平地,便是京城守卫的羽林骁骑亲来,亦不外如是。
然而那车原是拉炭之用,马匹羸瘦,慢慢拉着炭薪一路晃来堪堪可用,竞速却是不能。
冷凌霜自幼在马厩里长成,熟知马性,一眼就看出这匹杂毛老马挨不得鞭子,只得尽力催行,忽听篷里秋兰一迭声惊叫:“霜姊!她…她来啦!她追上来啦!”
冷凌霜被车篷挡住,看不见后头情形,料想秋月已至,不觉骇然:“就算被所谓的魔剑附身,血肉之躯自有局限,武功根基更是无法说变就变。秋月武艺平平,那巨剑少说怕也有百斤重,怎能有这样的轻功造诣?”
情急之下,冷凌霜不自觉抽了两鞭,檀口中“驾、驾”出声。
那羸马一吃痛,竟不放蹄,腿筋一软,篷车几乎翻覆,速度不增反减!冷凌霜稳住车缰,急忙回头:“都没事罢…”
轰的一响,无数细碎木片刮面而来!秋兰惊叫着,缩头拼命往车前挤。冷凌霜定睛一瞧,后半截篷车早已空空如也,官道上拖开无数狼籍破片,半塌的遮篷碎布迎风乱飘,宛如叫化子的百结鹑衣。
就在方才的一瞬间,秋月抢入两丈范围内,单手提起巨剑一挥,半辆篷车便化做齑粉!
那车的后轮轴幅全毁,四轮车只剩前轴两轮,所幸炭车的车板结实,没有立即解体,但残余的部分随路面不住颠簸,分裂只是早晚的事。情况危急,冷凌霜尽力稳住车体,见安生爬上车座,逆风大喊:“快些坐好!这车快撑不住啦,莫要乱动!”
安生大声应答:“距离拉开啦!能不能再快些?”原来车体一分为二,重量大减,速度反而快上许多,间距顿时拉到四丈余。
冷凌霜摇头:“不成啦!这是匹老马,至多再跑一刻,便要坏腿。”
安生瞇眼眺望,急道:“二掌院!这是往市集的方向,再出得里许,便要入城外镇集啦!”
先前忙不择路,冷凌霜此刻方警醒过来,一咬银牙:“莫要牵连无辜,我们走小路!人都压向左边!”提缰一振,车辆倏然右转,左半车身翻翘起来,几乎倾覆。
篷车轰然转入官道旁的小径,秋月转弯依旧不甚灵便,冲出数丈才又回头。
安生紧抓着车辕,身体被路面颠得一抛一抛,探头回目,只见一点小小身影不断逼近,纤腰如柳,两条纤细白皙的裸腿飞快交错,似乎永不知疲累。曲线柔媚的大小腿,根本没有足以支持这种爆发力的肌肉线条,白得酥滑耀眼,他看得入神,又不禁有些迷惘:“世上,真的有魔剑附身么?一旦被附了身子,还能不能…还能不能再变回人?”
……
冷凌霜等一行弯入小径,转眼已奔逃数刻。
夜色渐浓,周围几乎黑不视物,沿着官道走时,犹能借着湖面映射些许微光,勉强辨别前路;转入小径后,距离湖面越来越远,车上又无提灯火把之类的物事,抬眼只见一片幽蓝蓝的靛青色,前方黑呼呼地横着无数胧影,或是石块,或是树枝,更可能是一处洼陷或水坑,根本无从辨别。
黑夜驰马,本就是最最愚蠢之举,许多白日里司空见惯的地景地物,一到夜里便成催命阎罗。
朝廷八百里加急的文书,纵使沿途享有金字牌的特权,各地邮驿一见旗号便即备马,信使无须落地,一路接力急驰,但也仅止于白天;为防发生差池,入夜后也是绝不赶路的。
冷凌霜握着马缰,口中荷荷有声,一双翦水明眸盯着黑夜里的虚空处,那匹又老又瘦的羸马总能适时跨腿闪身,避开路上的索命障碍,一路放蹄狂奔,速度丝毫不减。
安生知这非是侥幸,而是极高明的驾车御马之术,佩服之余,又禁不住想:“二掌院一个女子,从何处学来如此高明的马术?”但这些疑问也只能埋在肚里,不敢随意惊扰,只是紧攀着车缘,眯眼细看前路。
雨停片刻,朦胧的月光破云而出,安生辨别周围地景,逆着风叫道:“这里是清风林!往前再出数里,便至铸剑山地界啦!”
冷凌霜点了点头,精神大振,侧头微微一笑,顿如百合绽放,雪靥生春。安生看得一怔,心想:“原来二掌院笑起来,这般好看!”连忙别过头去,不敢多瞧。
忽闻车后一声惊叫,他赶紧低头钻进残破不堪的车篷里,见夏荷指着车后,尖叫道:“她……她还在!要追……追上来啦!”咬牙闭目,粉颈一斜,又晕死在秋兰怀里,胆子小成这般也是没谁了。
就着月光一看,车后约莫三丈外,娇小的秋月拖着巨刀,两条粉砌似的的笔直细腿飞快交错,嫩如新剥笋尖的足趾沾地即起,连泥水都没带起几滴。
雨中视线不佳,安生一度失去她的踪影,还以为已经摆脱。
大雨一停,月光复明,谁知她又追了上来,这回少了夜雨掩护,越追越近,不多时已拉至两丈之内,安生不敢稍离,攀着半毁的车篷紧密监控。
透过月光望去,秋月双腿修长,身薄腰小,腹间线条起伏、柔肌紧束,丝毫没有筋肉发达的刚硬扎眼,按理说本不该这般耐力惊人的。
安生只觉得奇怪,不由得多看了两眼:秋月雪腻的肌肤上,几滴汗珠滑过,说不出的玉雪可爱,但要知道僵尸死物是不会流汗的,只有活物才会;既然会流汗排热,肌肉筋骨自然会有疲倦的时候。
安生心念电转,一瞬之间,心中已转过无数念头。
秋兰喃喃自语道:“她怎么…怎么变成了这样的妖怪?”面色白惨,微颤的声音里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清冷。
安生摇头:“她是人,不是妖怪。”返身钻回前头车座。
冷凌霜大声问:“秋月追来了么?”
安生点点头,忽道:“二掌院,我猜秋月姑娘的轻功应该不错。”
冷凌霜一怔:“他怎么知道?”微微侧脸避风,大声道:“秋月轻功很好!便是算上了我大师姊、三师妹,她都能排得上第四第五!这孩子旁的不行,于此倒是别有天分。”
安生沉默点头,片刻才说:“二掌院,依照秋月姑娘的速度,少时便要追上,我想向你借寒霜剑一用。”
篷车几近半毁,自不会在车上相斗。冷凌霜急道:“万万不可!我…我绝不会抛下你,让你独自面对!”
安生仓促间不知如何解释,想了一下,才说:“我打不过那巨剑,但可能赢得了秋月姑娘。”
冷凌霜闻言蹙眉:“这是什么意思?”
安生说:“依我看,就算拿了那妖邪似的巨剑,阿傻是阿傻,秋月姑娘仍是秋月姑娘。阿傻若有秋月姑娘的轻功,刚才在桥上,我们就死定了;秋月姑娘若有阿傻的力气,那一刀决计不止砸坏半辆篷车。”
冷凌霜微微一怔,登时醒悟,不禁对这少年的洞察力颇感佩服,暗忖:“逃亡之中,连我都不免凄惶,他却见我所未见,想我所未想。”但仍是摇头:“我师妹向来力弱,却能毫不费力的挥舞那把巨石刃,这又怎么解释?”
安生摇头:“我不知道,要多些线索才好推测。请二掌院先借剑一用。”
“不行!那妖邪似的兵刃奇异,鬼神难测!我若让你下了车,与亲手杀你有什么分别?形势未至绝望时,岂能轻言牺牲!”
她说得急了,双手紧握马缰,檀口咬着几络乱发,雪靥微微涨红:“听明白了没?”
安生无言以对,想想也不是非剑不可,危机却须臾便至,随手折下一段残辕,在车座上屈起腰腿,作势要跳。
冷凌霜正全神驾车,眼角余光瞥见,忙伸手去揪他衣领。谁知安生动作极快,猛地低头,竟然闪过;突然车轮碾过地面一处窟窿,左边高高弹起,两人一下子失去平衡,顿时撞成一团。
冷凌霜不避男女之嫌,乘机一把揪住,斥责道:“少不更事!小小年纪,学人家逞什么英雄?你很想死么?”单手执缰,忙将车身稳住。
安生个头不高,被高挑苗条的冷凌霜张臂一挟,倒像姊姊教训调皮捣蛋的幼弟似的,偎着她曲线玲珑的温软娇躯,闻着襟怀里透出的微汗幽香,不禁有些发窘,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
争执之间,篷车又驰出里许,前方忽见一座黑黝黝的物事突出树林,形似磨坊,又有些像塔楼。冷凌霜正自狐疑,忽听安生大叫:“是烽火台!那是本城的烽火台!台中驻有哨队,一班多则十来名弟兄,都是全副武装。
“二掌院……”话没说完,“轰”的一声巨响,身下倏空!安生一阵天旋地转,不知翻了几翻,直到背门撞上硬地,才知自己是在疾驰间被抛了出去。
他抱头连滚几匝,化去冲击的力道,一跃而起,见三丈外一处巨坑,坑里木片狼籍,依稀辨出辕轭轴辐的模样,原来是秋月追了上来,一击将仅剩的半辆篷车砸了个粉碎!
那匹羸马后腿受到重创,倒地不起,昂首嘶嘶哀鸣。距陷坑不远处,一抹窈窕的衣影拄剑而起。
冷凌霜簪带迸散,披落一头如瀑长发,掩着半张如雪玉靥;周身衣衫被尖利木屑划破,血染如枫,破孔里露出欺霜赛雪的晶莹肌肤,分外凄艳。
她勉强站起,拖着左腿走前几步,从破烂的篷布底下拉出秋兰。秋兰似无大碍,抱着小脑袋连摇几回,神情茫然,身上却没见什么皮外伤。
安生抓起一根碗口粗的辕木,四下急望。
一阵寒风吹来,左右树冠沙沙摇动,天边乌云被刮得漫卷而来,月华越来越稀、越来越淡,视界里又比想象中更加浓暗,就像有人在吹着灯焰玩儿……
凭着一股莫可名状的直觉,安生拖着辕木朝前方走去。
冷凌霜拄着寒霜剑,与秋兰一同迎面走过来,秀丽的脸上满是关怀之色:“安兄弟!你还好……”
安生心中一动,大吼:“小心!”抡木往一旁的树影扫去,砰的一声,整条辕木应声爆裂,一条纤细苗条的俪影闪了出来,几株粗木四散倒落,铁链声中,拖出一把狰狞的巨剑!
“快走!”他回头大叫:“往烽火台去!”
冷凌霜微一迟疑,将寒霜剑扔了过去。
安生一把接住,心中暗祷:“阿叔!阿生今日将性命,交到你亲手所铸的剑器里了!”连剑带鞘扫向敌人!铁石交轰之下,寒霜剑鞘迸碎,暗铜色的剑身却连晃都不晃;巨剑簌簌几声,剑身上剑痕宛然,犹如新刻。
安生大喜,也不用什么招数,双手握着寒霜剑的奇长剑柄,回身又是一斫!他自知武功低微,所恃者不过天生的臂力,因此一昧猛砍,每一下都抢在秋月之前,不待她体势用老,转头又是一剑;对击十余合后,秋月身子轻盈,越转越快,手中巨剑却变缓,与其说是舞剑,不如说是以巨剑为盾,撞击的动作还多过了砍劈,人兵渐渐分离。
虽是如此,巨剑毕竟有千钧之重,再加上寒霜乃极刚之剑,剑身硬实、不具韧性,每回交锋,挥出的力道倒有三成由剑身反馈回来,震得他双手虎口迸裂,两臂酸软,边打边退,不意一脚踏空,竟然摔入一处大坑里。
“不好!”他举剑护住头脸,但巨剑连地面都能硬生生劈出三尺深坑,居高临下,岂能被轻易格住?正要闭目等死,谁知秋月忽然停步,在坑边踌躇起来,似乎想后退跳将过去,如在断桥时一般,但又隐约知道敌人不在对面,一双雪腻的细直长腿在坑缘前前后后探着,沾尘的赤裸足趾显得十分娇妍。
他无心细看,忙环视四周:坑深约七尺,足有一丈见方,沿坑似乎砌有砖石,如今倾坯大半。
此地离无双城的烽火台甚近,可能是昔日屯兵卫所挖掘的贮水池。
“难道……她爬不下坑壑?”
忽然想起阿傻掉落断桥时,动作更加呆板,半晌都爬不上桥墩,似乎是妖邪巨剑附身的弱点。秋月下不了池坑,气得尖声嚎叫,抓着铁链,猛将巨剑往坑里一掼!掼破池底铺石,安生避无可避,攀着坑洼的巨剑表面往上一蹬,乘机跃出池坑。
秋月随即用力扯回铁链,力道却差了分许;巨剑稍动即沉,第二下才又拉了上去。
安生见此心想:“果然如此!妖邪巨剑纵使神异,但所附身的人力毕竟有穷。”觑准时机,一剑刺中秋月的右大腿!
秋月一跤坐倒,巨剑当胸一抡,将安生平挥出去。安生直摔到池坑对面,落地滚出两丈有余,一口鲜血全呕在地上。
他起身一抹唇际,提剑缓缓退走,对面秋月坐在地上,不住挣扎站起,右腿却无法施力,又圆又大的眼中射出熊熊恨火,口中荷荷低咆,宛若困兽。
安生盯着她,沉声道:“你若再要追来……下一回,我会取你性命。”妖邪巨剑似通人语,秋月仰天尖嚎,挣扎得越发激烈。
一妖一人四只眼睛隔空对峙,安生直退出十丈外,才转身往烽火台奔去。他一路借由月光辨别地貌,认出此地名为“狮驼峪”,算是铸剑山的北方支脉,峡谷不甚高,却层迭成狮身驼背状,故尔得名。烽火台应沿峡顶而建,再往前去,便是一片低崖。
奔跑一阵,听见前方有刀剑交击声,暗自心惊:“莫非烽火台出了什么意外?”急急穿出树林,却见台前的空地之上,一片青芒夹着霭霭红雾,其间一条人影交旋闪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趋避直如鬼魅;再揉眼睛,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战团中心,冷凌霜手持一柄酒红弯刀,那丝丝红雾正是由刀身上窜出。她左腿有伤,索性坐在地上,背门靠着台前石狮,径以弯刀应敌,夜里看不清她的神情,从舞刀的动作判断,体力似已不支。
来人占尽上风,却迟迟未下杀手。安生正要上前,忽听秋兰叫唤:“安生!快去帮霜姊的忙!”
转头望去,只见她远远坐在空地另一侧,身边除了趴卧的夏荷之外,还有一名容貌清癯的高瘦老者闭目盘膝,脸色青得吓人。
冷凌霜一听他来,手底骤软,似乎气力已尽;那手持青芒的敌人也不屈膝弯腿,足尖一点,便要倒退开来。
冷凌霜急道:“安兄弟!快,快拦住此人……”忽然粉颈一歪,软软瘫倒,胸脯剧烈起伏,挺直的琼鼻却喷出两道淡淡粉烟,恍若胭脂悄染。
安生这才明白;原来非是击退来敌,恰恰是要将他留下!急迫间不及细问,抡起寒霜剑一扫,将来人的退路尽数封住!那人转身格挡,照面一瞧,才发现他周身、头脸均缠满绷带,持了柄绿光闪闪的阔剑,剑锋形如兰瓣,极为罕见。
安生微微一怔,认出是狼叔的冶炼铸房为心剑宫承制的兵器,开锋研磨时他还曾经在一旁观看,脱口道:“你是心剑宫的赵三侠!”
那人不发一语,随手化去来势,正想夺下寒霜剑,岂料安生一缩手竟避了开来,嘴角露出一丝欣慰,也不见他如何出手,安生胁下微疼,整个人倏忽倒地,半边身子酸麻难当,动弹不得。
那人缓缓走过他眼前,一颗血珠蓦地坠地;第二步尚未跨出,血珠又复滴落,第二颗、第三颗……直如檐前雨漏。
“他受伤了?”安生心下骇然:“以他的身手,若施全力,怕连二掌院也难以抵挡……此人,究竟所为何来?”
那人平举兰锋阔剑,跨步而来,一步快过一步,越走越急;蓦地身形微晃,飞也似的刺向闭目盘膝的白衣老人!秋兰吓得惊叫起来,谁知剑锋着体的瞬间,老人倏然睁眼,反手将兰锋剑卷入袖中,一掌击在那人胸口!那人胸口刀创爆裂,鲜血如提酒酾空,溅成一片贯日长虹,身子一弓,拔剑倒退;两个起落间已滑出四五丈远,双膝跪地,深浓的血浆鼓溢而出。
老人面色灰败,这一击似乎用尽了他仅剩不多的余力,同样站不起来,撑地剧咳一阵,冷笑道:“弄了半天,原来……原来你是来杀我的。想……想灭口么,妖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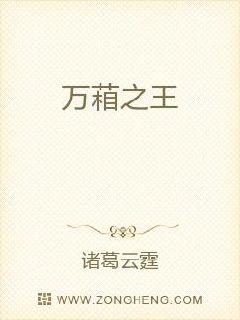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