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装神弄鬼
老妇人:“大官人还有何吩咐?”。
南宫月又露出了那令人讨厌至极的笑:“大侄子还没有吃过叔叔的花生呢,吃了再走也不迟。”
老妇人脸上已因激动而红得发紫:“大官人这花生,老身母俩可吃不起!”。
南宫月:“在下请客,无妨。”
老妇人:“适才四条人命都换不到大官人的花生,现在大官人要白送?”。
南宫月:“只要你说出这笔生意的幕后大老板,花生可以随便吃,人也可以随便走。”
老妇人:“那老身可不可以不吃?”。
南宫月:“只不过,在下请吃的花生,别人不吃也不行!”。
老妇人:“大官人好生霸道,那老身母俩恭敬不如从命了。”
小孩已经不哭,正在妇人怀里蠕动。
老妇人正抱着孩子,慢慢地捧过来,捧到南宫月眼前。
就在这一瞬间,寒光一闪,一把匕首从妇人怀里突然刺出,急划南宫月咽喉之处。
谁也没料到会有这么一着,匕首竟是从孩子的手里刺出,孩子竟然是个侏儒。
南宫月就算防着这个老妇人,也不会防着这孩子。
又有谁会去提防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呢?
在这电光石火中,南宫月忽然向后一折,整个身体翻仰向后,匕首堪堪从南宫月鼻梁上划过去,只差半寸。
这时老妇人已双腿连发,急扫南宫月下盘。
这一着实在太出乎人意料,南宫月就算没有被匕首划中,下盘也必被攻破,只要南宫月一倒下去,很有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再站起来。
这一配合简直天衣无缝,在这么近的距离,这么快的出手,几乎已没有任何人能闪避,更何况他们这一出手本已排练过很多次,从无失手过。
只可惜,南宫月并不是任何人,世上也只有一个南宫月。
他早已经从无数次的暗算、恶战中练就了极度灵敏的本能,才成就了今天第一神捕的名声。
南宫月双足在地上一点一提一蹬,把两条腿平伸出去,身子横在半空中,整个人就像横着躺在半空中一样,匕首堪堪从鼻梁上划过,老妇人一腿扫空,就在这当口,南宫月已双手急点,右手点老妇人脚上涌泉穴,左手点侏儒腰间志室穴。
南宫月早就算准了这一出手就算不能点中,至少也能逼退对方。
但,世事难料。
天下间有很多事情都是无法计算得到的。
侏儒没有借势翻开,却突然伸过双手揽住南宫月左手扯住不放。
老妇人也没有退后,一条腿硬生生踢了上来。
这一突变更令南宫月震惊不已。
只听“噹”的一声,南宫月已点上了老妇人腿上。
那感觉却像是点在一张铁皮上,双指立时有些发麻。
身上穿着铁甲的江湖人并不少,这不足为怪,但脚上包着铁皮的人实在不多,更要命的是,这时南宫月的另一条手臂也已经被翻身缠上的侏儒抱住。
情况万分危急。
“嘭”的一声。
只一声,三人几乎在同一瞬间摔在地上。
地上一片狼藉,残败。
茶馆内外鸦雀无声,众人都在等着他们站起来。
良久,终于有人慢慢站了起来。
站起来的人是南宫月。
南宫月能再站起来的时候,别人通常都已经倒下去,永远的倒下去。
他再站起来的时候,只淡淡的说了一句:“现在你知道红辣椒和小二哥是怎么倒下去了么?”。
没有人回答,倒在地上的人已不能回答。
或许此刻他们都已经知道答案,但也没有机会再回答了。
此时日已偏西,秋风正萧瑟。
茶棚外的汗血宝马正在拴柱旁踢踏着闲步。
天外云去。
落日慢悠悠的。
天底下已有炊烟在飘渺。
表示这一日的光阴已经不多了。
劳累了一整天,大部分人都已经回到家里,享受着黄昏前的那一刻清闲。
一个遛鸟的老人却正提着一个条形很密的毛竹制成的笼子,在长街上慢慢踱着闲步。
老人的身形消瘦,轻凊,也正如炊烟般飘渺。
老人们一旦变得越老,似乎就越是不肯停下来休息,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竹笼子里的百灵鸟在鸣唱,却失去了往日的韵味。
或许它早已失去了高飞的勇气,就像这暮色下的老人一样,也已经渐渐习惯了慢慢悠悠的脚步。
老人生命中的乐趣已然不多,太烈的酒已喝不下,太腻的饭菜也早已不合胃口,笼子里那仅有的一点点生命力,几乎已是他生命的全部。
他每天提着这一点点微薄的生命力,迎着夕阳下不停地踱着步,似是想要把握住那每一次虽灿烂美妙却已微薄得可怜的余晖。
平凡又苦闷的日子就这样子被他一步又一步地踱掉。
柳长歌一边踱着闲步,一边用手袖轻轻地擦拭着长笛。
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老人这笼子里的鸟,也已没有了高飞的勇气。
他生命中的乐趣也不太多,这管长笛或许已算是他生命中为数不多的一屡生气了。
但这一屡生气却已是他生命的全部。
此刻他忽然觉得自己也已经变老。
真正的衰老正是从内心开始的。
当你觉得自己已经老了的时候,你就真的已经老了。
这也正是人类最大的悲哀之一。
柳长歌一边擦拭着长笛,脸上的表情淡淡的,就像是这傍晚的薄云,淡而无味。
“你是说,我们就在这里等人?”。
欧阳菲菲一边拔着琴弦,一边缓缓道:“是”。
“等什么人?”。
“等一个可以带我们去参加晚宴的人!”。
“这个人是不是一定会从这里经过?”。
“一定!”。
“可是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该来的时候总会来的。”
该来的终究会来,该走的是不是一定会走?
秋风瑟瑟,送走了一地落叶,却送不走漫天的寂寞。
欧阳菲菲仍在抚琴,琴声如落叶般萧瑟,远而不绝,恨而不休。
像在诉说着故国残梦。
她抚着琴,一面浅声吟唱: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花。
没有月,也没有沙,但漫天飘渺的烟云已然将长街笼罩。
柳长歌的眼神已然飘渺,这一刻,他也已朦胧。
最近这一段时日,欧阳菲菲总是反复的弹唱着这首曲子。
南陈后主的这首曲子也同秋风般萧瑟,她每弹一回,柳长歌的心就为她揪紧一次。
夜已近,人正停泊异乡,此处虽非秦淮,却也有酒家。
酒家就远在长街迷雾中。
迷雾中已挂起一盏灯笼,灯笼上一个斗大的“酒”字,在秋风中招摇,似在呼唤浪迹天涯的游子共谋一醉。
是不是喝醉了,便可以驱散这漫天的寂寞?
是不是喝醉了,便可以忘却亡国恨?还有那醉人的**花?
柳长歌的眼神已飘摇,摇到陌路天涯。
若是这秋煞能醉人,柳长歌宁愿酣醉。
不管是**花还是天涯陌,花开花谢终有时,天色渐暮的时候,海棠花也已失去了颜色。
凤凰正在园子里给海棠花浇着水,浇得比以往都多,比以往都满。
她这双手握刀的时日远比浇花的时间多得多。
这双手握起战刀的时候,也曾经令无数的敌人胆寒。
可是谁又能想到她这双手浇起花来却是那么细致,那么温婉。
她往海棠花里不停的浇着水,暮色下的海棠花却已暗淡,空洞。
那泛起的水花仿佛就浇灌在她空洞无神的眼神上,一直要灌满她的心里为止。
她浇得那样专注,仿佛浇完了这一次,就不知什么时候能再浇了一样。
“小姐小姐,马车来了!”。
蝶儿牵着马车,车马已到了大门外。
饱战的骏马已略苍老,深邃的马眼正漠视着黄昏。
那曾经踩踏过无数敌人尸身的铁蹄此刻却在这黄昏下有一茬没一茬地闲踩着碎步。
“我们为什么不在家里等着老爷,老爷都快要回来了不是么?”。
蝶儿一手拿着把用猪鬃编成的刷子在老马的脖子上来回刷拭着,就像在刷拭着自己的辫子一样仔细,疼惜。
她忽一抬头,甩了甩头上扎的两条马辫子,满眼欢喜地道:“不就是老爷要请客吃饭,我们为什么非要去不可……”。
凤凰喃喃道:“但这顿饭却并不好吃!”。
“不好吃的饭,老爷为何要吃?”。
“老爷若是不好好的吃这顿饭,只怕以后的饭也很难好好地吃了。”
“什么样的饭这么打紧?”。
“若是有人在你吃饭的时候,给你送来一口棺材,你还吃得下这口饭么……”。
“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给咱们老爷送来一口棺材?”。
“我也很想知道!”
“报信的没有说清楚么?”。
“恐怕连老爷都不是很清楚!”
“哦?”
“但我们可以去问。”
“找谁问去?”
“当然是吃饭的人!”。
“我们究竟是去问话,还是去吃饭?”。
“话要问,饭当然也得吃。”
蝶儿手上的刷子忽然慢了下来:“只可惜,有些饭只怕是吃不得的……”
凤凰:“人活着,就得吃饭。”
蝶儿:“人若死了呢?”。
凤凰:“你若是怕得打紧,还是不要随我去的好。”
“有小姐和老将军在,蝶儿不怕!”她忽然也紧握起双拳来,眼里也已充满精光。
此时暮色已深,很多人世间的美好也已在暮色中渐渐模糊。
蝶儿望着迷蒙的暮色,又轻轻叹了口气:“只怕咱们去到那里,也已经太晚了……”
天还不算晚,至少不算很晚,就算给海棠花再多浇几桶水,也还来得及。
但,车马已启程,有些事是等不得的。
车马走入长风镇的时候,暮色虽然已经很深了,却仍可分辨出长街上一地流离的落叶。
落叶深处,有琴声。
琴声凄迷,仿佛在讲诉着人间的大不幸。
不幸的曲子很多,偏偏此时的曲子却是异样的苍凉,比一地的落叶更凉。
凤凰忽然觉得这琴声竟似有些熟悉。
琴声中还夹杂着一屡笛音。
琴声虽熟悉,但笛音却似从未听闻。
琴声凄迷低沉,笛音也沉,但仔细听来却显然意味不同。
凄迷的琴声略嫌急促,低沉中满是愤恨,在秋风中带着萧杀之气。
笛音虽也低沉,但节奏却缓慢,有如徐徐微动的枯叶,虽萧瑟却隐含归属之感。
车马走入长街时,风很轻,满街的落叶正在寻找着归宿,马儿也不自觉地放俏了脚步。
凤凰从车窗里瞟出去,朦胧中依稀可见一袭白衣女子正坐在道旁的茶僚外抚琴,旁边一蓝衣男子却背立在晚风中吹着笛子。
就算是同一首曲子,不同的人弹起来也不尽相同,但此刻琴声听来很是熟悉,却是因这弹琴人的节奏与力度。
这种节奏与力度竟似与凤凰平时所弹非常相似。
笛音起初节奏缓慢,一丝一屡有如月下幽泉潺潺流淌,流入心中,淌满心底的一方故里,仿佛要带着迷途天涯的浪子落叶归根。
忽然间秋风骤急。
琴声也突的变了。
变得愈加急促。
秋风萧杀中,凤凰忽然发现地上的落叶越积越多,满天的落叶竟似被这琴声所摧残,擦得地面簌簌的响。
从指尖弹发出来的力度显示弹琴人的内力显然不俗。
原先缓慢的笛音此刻竟似不由自主的跟着急躁起来。
凤凰忽然发现这笛音中竟也生出了屡屡杀气。
就像战马忽临城门,战士忽然拔刀。
虽未砍伤一人,却足以令人感受到死亡逼临的气息。
萧杀的傍晚,两个萧杀的江湖人,满地的落叶,漫天的杀气。
凤凰忽然觉得空气很闷。
拉车的马本是一匹战马,此刻突的马首一仰,伸出那踏过无数疆场的铁蹄在满街的枯叶上来回踩着碎步,不肯向前。
“小姐,小姐,天都要黑了,我们怎么越走越慢了呀?”。
凤凰轻叹了声:“只因咱们的马受了惊,不肯走了。”
蝶儿伸头探出车窗一望,长街昏沉,道上空荡荡的,只有一地的落叶在簌簌的响。
道旁茶僚外只有两人,一站一坐,一吹笛,一抚琴。
琴声随着晚风掠过,蝶儿心里不由得隐隐感到丝丝凉意。
“咱们的马跟着小姐上阵杀敌都不怕,难道还怕鬼不成?”。
“你说对了,就是怕鬼!”。
“哪里有鬼,奴婢怎么见不到?”。
“你是自然见不到的,只因这鬼在人身上……”。
“鬼在人身上?什么人在装神弄鬼?”。
“我也正想问问。”
“只是这人倘若心中有鬼,又怎么能问得到?”。
“这就得看你问话的学问了……”
“问话也有学问?”。
“当然是有讲究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问法。”
蝶儿伸长了脖子问道:“天底下不同的人那么多,若是一个个地问,小姐不是忙死了?”。
“对本小姐来说,世上只分两种人”。
“男人和女人?”
“活人和死人!”。
“死人还能问出话?”
“死人的话倒是容量问得多……”。
“这却是为何?”。
“只因活人会说谎,死人却不会!”。
“只怕这活人的话也不好问!”。
“活人也分两种!”。
“哪两种?”。
“敌人和自己人!”。
“这俩人是敌人?”。
“至少还不算是自己人。”
“小姐通常是怎么给敌人问话的……”。
“跟敌人问话,就得用对付敌人的法子!”。
“小姐平时是怎么对付敌人的?”。
“对付敌人,最好的法子就是用刀!”。
“可是小姐的刀呢?”。
凤凰久已不用刀。
她手里那柄弯如明月的长刀久已被海棠与长琴所替代。
只见她忽然起身,下了马车。
她一下马车,立刻就恢复了上阵杀敌的样子。
晚风中,她的身形飒爽挺拔,眼神忽然间也变得犀利。
那个迷茫的浇花女子此刻已然不见了。
她虽没带刀,此刻却以臂代刀,忽的凌空跃起,以一招“力劈华山”之势,突然向晚风中吹笛的男子劈了下去。
柳长歌正在吹笛,笛声随着琴声正渐入苦境,秋风声里却忽闻衣袂破风之声,似是从空中直奔背上袭来,风声甚急。
柳长歌一惊之下,立即身形急转。
一转过身,他立刻就发现一人正从半空中扬臂劈下,其势甚猛。
出于本能反应,柳长歌立刻扬笛挥出。
长笛一挥,在秋煞中带着凌厉的杀气,划出一阵破风之声,迎着来人斜划上去。
但他立刻又发现这人下劈之势虽急,招式间却似乎缺少了那种令人胆寒的气息。
来人这下击之势看似力度不小,但招式间却似乎缺少杀气。
身形虽破风,但手势似在犹豫,隐隐有后收的意味,所击也并非要害之处。
似乎并没有想要一击必杀的意味。
柳长歌这长笛上划间忽然一变,变为一扫,横扫来人下坠的双足,再把笛尖一挑,连抖出三四个“棍花”。
来人双足上的几处穴位均已被“棍花”笼罩。
这长笛一划上去的杀气也立刻被他横着收了起来,来人若不攻下来,完全可以在横笛之上借势弹开,他在空中连抖的三四个棍花也只是点到为止。
这一挑,抖得那么轻灵,在晚风中挥洒出一阵绵柔这气,极具诗意。
昔年公孙大娘从诗中悟剑,何等洒脱,柳长歌这长笛一挥一抖,却也正是他从诗词当中自行悟出的招式。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这一横一扫间,凤凰本被封死的退路立刻就被铺展开来,她在长笛上双足一点,翻身退落。
长笛却只在身后抖了几朵棍花,并没有追击而来的意思。
那抖动的“花影”随着晚风轻送,如暮下的海棠花在招手,虽寂寥却令人怜惜。
凤凰心头忽然一紧,竟停下了身形。
琴声此时忽也停歇。
琴声一停,弹琴人便立刻抬起头来。
弹琴的人却正是欧阳菲菲。
欧阳菲菲忽然抬头一笑道:“姐姐,姐姐,凤凰姐姐,别来这一向可好?”。
欧阳菲菲一面欢笑一面连声呼唤起来。
柳长歌竟似完全没有料到欧阳菲菲竟忽然会生出这种样子。
她笑得这么欢喜,这么爽朗,仿佛和刚才那个满身怨气,琴声中充满杀气的弹琴人竟已完全两样。
柳长歌忽然怔住。
欧阳菲菲却笑得愈加亲切了。
“姐姐在发什么怔,姐姐难道不记得欧阳妹妹了么?”
她一连几声个“姐姐”,声音不但欢喜、亲切,甚至饱含深情。
柳长歌紧握长笛的手已渐渐松开。
“妹妹适才弹的这首曲子还是姐姐两年前亲手所教的呢……”。
凤凰还未来得及反应,欧阳菲菲已拔开双腿,小跑过来。
她一路跑过来,一路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凤凰的手,似乎就要热泪盈眶。
“两年不见,妹妹可是想刹姐姐了,姐姐这一向可安好……”。
姐妹重逢,他乡遇故知,这本应是非常值得令人高兴的事情。
但凤凰却开心不起来,特别是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
她不像欧阳菲菲,她还不能一下子就马上转变自己的情绪。
凤凰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一别两年,妹妹还是从前的样子,只是姐姐……”。
“姐姐有心事?”。
“自然是有事,其实真是一言难尽。”
“其实姐姐的心事妹妹或许也能猜到一二……”。
“哦?”。
“妹妹也正是特地在此等候姐姐的!”。
“等我做什么?”。
“跟着姐姐去蹭饭吃呗!”。
“妹妹怎知姐姐要去吃饭?”
“这么特别的‘饭局’,妹妹岂能不知!”
欧阳菲菲:“这么轰动的消息,只怕早已传遍天下,只怕已是无人不知了……”。
凤凰:“莫非妹妹也正是为这消息而来?”。
欧阳菲菲:“正是,妹妹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想着要来看看。”
凤凰:“只可惜这种事并没什么好看的……”。
蝶儿:“不但不好看,而且危险的紧……”。
欧阳菲菲:“正因为危险,所以妹妹更应该要去!”。
“哦?”。
“姐姐的亲人对妹妹来说,也像是亲人一样。”
欧阳菲菲不等凤凰回答又接着道:“亲人有了危险,妹妹怎能无动于衷?”。
“只是,只是……”,凤凰面现疑惑之色,竟忽然一时语塞。
欧阳菲菲:“姐姐莫非不放心妹妹?”。
“这倒不是”,凤凰忽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不经意中却撇了柳长歌一眼。
欧阳菲菲:“这位柳先生与妹妹情同兄妹,姐姐大可放心!”。
柳长歌的手又忽然握紧。
“这位柳先生也一定能帮上姐姐的忙!”,欧阳菲菲说着话,却偷偷瞟了柳长歌一眼。
蝶儿:“这位柳先生一手笛子使得好生得意,奴婢也很想多瞧瞧呢……”。
欧阳菲菲:“柳大哥使笛子好不好看?”。
蝶儿:“好看极了!”。
欧阳菲菲:“那你可就有眼福了……”。
凤凰:“再好看的笛子也同样危险得紧……”。
“所有更应该多看看了”。蝶儿竟忽然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
凤凰忽然觉得,蝶儿心里也有鬼。
鬼精灵。
若真有人装神弄鬼,会是什么样的人?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胆敢在大将军面前装神弄鬼,只怕已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没有谁愿意用性命去开这种玩笑。
无论是谁,若想跟大将军开玩笑,这人若不是疯了,只怕就是已经不想活了。
晚风已变缓,凤凰却只想车马再快些。
将军从不信鬼,也不拜神。
将军拜的是太阳,只有天上至高无上的炎炎烈日才配做将军心目中的神。
此刻天已经很黒了,烈日也早已被黒暗吞没,正是百鬼出没的时候。
长亭外秋风习习,点点星光下有树影飘摇。
将军就坐在长亭上。
树影流动,将军却稳如泰山,稳坐在一方光滑亮堂的长形大理石上。
他的身形也正如大理石般坚固,厚重。
长亭里灯火阑珊,两排绿的红的大灯笼将长亭熏染得异常灿烂。
将军身上银甲亮堂,宽阔而厚重的身影在灯火中同样灿烂异常。
他的手臂很粗很长,几乎已和他的***一样长,此刻他却没有握刀,一双手却正按在长桌上。
他目光炯炯,俯瞰长桌,面上的表情充满自信,那神情就好像手里已经按下了无数的城池一样,一双手不但稳定而且充满了力量,仿佛能压倒一切。
长桌很长,大约有十来丈那么长。
那么长的长桌却只坐着六个人。
六个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人物。
其中既有少林的渡难禅师,也有魔教的长老曲值,更有武圣人的胞弟问天雄,以及神医谷的管家毒阎王,另外还有关外武林盟主的少主谢小天。
最后一位虽非江湖中人,但在江湖上也早已是声名赫赫。
他便是天下第一神捕,当朝国舅爷南宫月。
长桌上有酒,却没有人举杯,有菜,却也没有人动筷子。
将军的酒自然是好酒,其中既有天子赏赐的来自波斯朝贡的葡萄美酒,也有从民间秘酿出来的各种小酌,桌上的菜肴更是精妙无比,不仅有草原上那种又粗又硬的马肉,也有关外的不满周岁的小羊羔肉,各种飞禽走兽当真尽藏其间,尤其日间刚捕获的一头梅花鹿,也已被军营中的伙头用火炭熏烤了一整天,此刻就摆在长桌中间。
能够坐在这样一张桌子旁吃饭,实在是人世间最美妙的享受。
但此刻却既没有人喝酒,也没有人吃菜。
每个人都在望着大将军,大将军就坐在长桌尽头,仿佛离这个世界很遥远。
他孤零零的坐着那里,就像一个已被世界冷落已久的遗孤,那么孤寂、无助。
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此刻在众人眼中看来竟似已有些苍老。
但其实他既不苍老,也不无助。
他正值壮年,如日中天。
虽然此时已是夜间,这里里外外看来仍是静悄悄的,看不出什么动静。
但谁也不知道这长亭外,芳草间,藏有多少凶悍无比的兵士,只要他振臂一呼,随时都可能将这片芳草夷为平地。
通常他没有举杯的时候,别的人最好也莫要举起杯子来。
他没有开始吃菜的时候,别人也最好莫要去动筷子。
这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从来也没有人能够破坏这种习惯。
如若有人硬是要破坏这个习惯,除非那人已经活得不耐烦了。
世上活得不耐烦的人毕竟还不太多。
不多,但也不能说没有。
此刻就有人已经开始动了。
动的是谢小天。
谢小天忽然拿起桌上放着用来切肉的一柄小刀。
大将军最不缺的就是刀,各种各样的刀都有,且大多都是大刀,但这柄刀却很短,很小。
刀虽小,却削铁如泥,锋利无比。
这样子的刀无论切在什么东西上面,都必将无往不利,用来切肉自然是非常合适。
更何况这桌上的梅花鹿早已被焱焱炭火熏得熟透,若是用刀的人力量够足,哪怕是坚韧如铁的鹿骨只怕要切下来也不算是什么难事。
这么样的一柄刀,若是切上那面大理石上面,是不是也同样能切出一个大洞来?
谢小天已举起刀。
刀口向外,滴着寒光,正如他的眼神一样,充满锋锐。
他的人也正像这柄短刀,精悍、锐利。
他举着刀,冷冷的开口说道:“早已听闻这中原的鹿肉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美味,各位可不要辜负了主人家的一翻美意才好!”。
久已沉默的大将军忽然双目一射,冷冷道:“谢少侠若想争食中原鹿,却不知可有逐鹿中原的本事?”。
谢小天:“若论这逐鹿中原的本事,又有谁能及得上老将军,只不过……”。
大将军:“不过什么?”。
谢小天:“只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以后这种苦差事还是交给年青人来做比较好。”
他一边冷笑一边接着道“外头风雨飘摇,老将军劳苦半生,可莫要累坏了身子骨!”。
他拿着小刀,轻轻地转动,却迟迟没有切下去,但是握刀的手背上却已透出青筋,显然握得更紧,更用力。
大将军:“谢少侠认为本将已老?已吃不得中原这块鹿肉了么……”。
谢小天:“每个人都难免会老,这种事既然无可避免,做人何不知趣些?老将军又何苦懊丧……”。
谢小天嘴上说着安慰的话,但脸上那种孤傲的冽笑却一点安慰的意思都没有,他盯着手中的小刀,刀泛寒光,仿佛随时都会切下去。
少林渡难却正在掐着挂在胸前的一长串佛珠。
佛珠又圆又滑,又黑又亮。
这尘世间的人,尘世间的事,岂不也正如这佛珠一样,又圆又滑?有时暗黑,有时亮堂?
他掐着佛珠,就像在掐着自己的俗尘往事一样,好像总也掐不完,此刻他却忽然一笑,笑道:“不管是中原鹿也好,关外羊也罢,终究也免不得要被世人摆在餐桌上,供世人分食……”。
他掐着佛珠不停地转,目光也随着在餐桌上转个不停:“众位施主又何苦执着于这鹿由谁来逐?这肉由谁来分?善哉善哉……”。
谢小天忽然话锋一转:“中原的出家人莫非也食肉?”,他挥动着手中的小刀,冰凉的目光却已射向渡难。
渡难笑道:“阿弥陀佛,吃即不吃,不吃即吃,谢小施主又何必执迷不悟……”。
谢小天:“既如此,大师何不动手……”。
渡难:“谢小施主如此心急要动手,只怕是吃不得这鹿肉的……”。
谢小天:“哦?”。
渡难:“这烤肉讲究的是火候,吃肉也是讲究时机的。”
谢小天目光一挑,冷冷道:“大师莫非认为在下火候不足,难成气候?”。
渡难:“这鹿肉未免已太老,肉汁也太浓,谢施主这小身子骨却未免嫩生了些,只怕是经受不起!”。
谢小天:“这肉若嫌老,便只能配老人么?如此说来,这鹿肉可是更合大师的胃口?”。
渡难不过也才四十出头,若说这样也算是老人,这未免也太过牵强了些。
只不过出家人四大皆空,当然是不用理会这种稚幼的嘲讽之言。
却不想此话一出,渡难脸上顿时没了笑容。
渡难眼里强行露出冷笑道:“小施主常年在关外牧犬放羊,莫非家风向来如此,难怪行事也如犬羊一样浪荡不拘……”
他嘴上虽说的是“浪荡不拘”,实则是在暗讽谢小天如犬羊一样,不懂礼数。
谢小天眼里却已有火花闪现,环顾四周一遍才冷冷道:“有真本事的人自是值得令人佩服,只不过这里既没有令人佩服的人,在下又何需假意奉承……”。
他挥手轻轻将刀口一翻,已对着渡难,刀口下的寒光正映射在闪闪的佛珠上。
“更何况,在下面对的只不过是一头被少林赶下山的秃驴,又臭又硬的秃驴!与一头秃驴又何需讲什礼数……”。
他的目光忽然变得更冷,更锐利,他的人也如这把刀一样,充满了威胁性。
渡难的脸色忽然憋红,一双眼却已瞪得鼓鼓的,手上更是用力地掐着佛珠,就像要把它掐碎一样。
谢小天却又接着道:“在下平日里不仅牧羊,闲暇时也训驴,特别是中原那些又臭又硬的秃驴!”。
渡难:“贫僧时常也渡化世人,像小施主这样的宵小之辈,贫僧倒也是非常乐意超度得很……”。
他嘴上说着要超度别人,众人只道他就要出手了。
少林乃武林泰斗,渡难更是辈分极高,他若出手,放眼江湖,很少有人能招架得住。
但不知关外武林盟主的少公子又如何?
众人都在瞅着谢小天。
渡难瞪圆着双眼,“啾”地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脸上立刻现出了杀机。
谢小天:“你让我先出手?”。
渡难:“区区黄毛小儿,贫僧便让三先又何妨……”
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没有哪一个江湖人能够忍受这种轻视。
谢小天已咬起了牙,从牙缝里蹦出:“没有人能让我三招”。
话音未落,“咻”地一声,手中小刀忽然挥出。
只听“噹”的一声,刀光一闪而没。
灯影交错中,谢小天却退后一步,脸色已有些发白。
渡难却仍坐在原地不动,只是脸上的表情却已变了,变得双眉紧皱,嘴唇也已绷紧。
谢小天这一刀挥出,速度本极快,别人还没有来得及看见他是怎么出的手,刀背已击在佛珠上。
他本不愿占人便宜,所以出手前转以刀背击出,出手时又留了两分气力。
未曾想这大和尚的功力却是如此深厚,顷刻之间竟被震退一步,当下脸色发白,竟不由感到有些后悔没有用尽全力。
渡难原本正在盘转着佛珠,忽见寒光一闪,刀已逼至胸口,急促间竟来不及闪避,只得将手中佛珠随手迎上。
只听“噹”的一声,佛珠正好磕上刀背上。
幸好渡难手指上早已贯满内力,将内力灌注在佛珠上,这才堪堪将刀震开。
渡难这一惊却更是非同小可,他虽未曾退后一步,但这一着却已略显慌乱,面容上也已蒙上了一层寒霜。
他神情尴尬的坐在那里,胸前起伏,一口闷气还未排出,便冷冷道:“还有两招!”。
他刚说完这句话,挂在胸前的一长串佛珠上忽然有一颗佛珠裂开,掉落地上。
他脸上,额头上忽然开始渗出汗来。
谢小天冷冷的盯着渡难:“还有两招?”。
渡难呐呐地道:“说好三招,贫僧岂能食言。”
谢小天不再说话,却轻轻地将手上的小刀放在了长桌上,握上了一直佩戴在左手边腰上的一把长剑。
剑,才是他的随身兵器,从七岁开始,这柄剑就从没离开过他的身边,剑长三尺四,比普通大多数的剑要多突出一寸,剑柄上缠着黑丝,此刻也已与黑暗融为一体。
他在这柄剑上曾下过的苦功比起大多数同龄人要多得多,甚至比大多数比他年长的剑客更要多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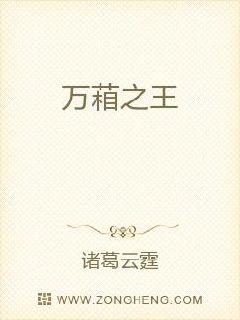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