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最要命的事情
“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顺着台阶爬向我,灯光照在他脸上,莫名觉得很亲近,一下子刻进我心里。他的眉毛比较粗重,眼窝深深陷进去,那双眼睛像磁铁一样,敦厚的耳垂很有安全感,脸庞轮廓刚毅,满脸络腮胡,嘴角挂着血,身高与郑师傅相仿,虽然没有他魁梧,但依然很结实,只不过伤痕累累,从头到脚一副落难的硬汉模样,实在难以抵挡。”
“哇!爸爸这么帅,妈妈一定非常喜欢啦!”
“岂止是喜欢,我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切。”
“可他已经跑了,什么也没留下。”
“不,他还在。”我妈按着自己心脏的位置,“在这里,留下了人间最美好的事。”
“那是什么?”
“爱情,永恒的爱情。”
“独独妈妈有吗?我会有吗?每个人都会有吗?”
“人人都奢望永恒的爱情,就像花朵奢望永恒的春天,流星奢望永恒的黑夜。奈何此事可遇不可求,人的生命却不能永恒,人会老去,人的心会老去,心里的冲动会老去,越老越胆小,越胆小越挑剔,越挑剔越妥协,总有人中途放弃,将奢望埋藏心底,卖身给无爱的婚姻,甘当半生傀儡,也总有人至死不渝,哪怕一世伶仃。”
“呃……不懂。”
“你只要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懂得自重,懂得尊重女性,不要丧失勇气,上天就不会亏待你。”
我将我妈的话一一记下,接着问:“你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
“就那么在一起了啊。”
“妈妈不兴敷衍,我有权利知道。”
“你哪来的权利?”
我昂首挺胸叉起腰,亮出一派理直气壮的架势,说:“因为我是妈妈在世上最亲的人,我绝不会丢下妈妈一个人不管,我是妈妈的监护人!”
我妈噗地笑出声,说:“你还知道监护人呢,监护人是你这样用的吗?”
“这算什么,我知道的可多呢!”
“你还知道什么呀?”
“我还知道,你们生我的时候都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难道不应当把你们的故事告诉我当作补偿吗?”
我妈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人小鬼大,满嘴歪理。”
我吐出舌头,两根食指扯下眼皮,冲我妈扮起鬼脸,我们笑作一团。
下了飞仙桥,来到擒龙口,这是个三岔口,与飞仙桥连起来像一只反着的凤爪,凤爪摁着诞龙江,由此得名。左边那条路经落羽长廊左段上山,右边稍高那条经长廊右段上山,稍低那条沿江绕到翥山另一面。
我们走了左边。
走廊上游人稀疏,山间松柏恬淡,凤凰惜嗓,脚边江水如龙,掠身而去,好一派动静相宜。我们一路无话,悠然信步,约莫小半钟头,直到左段长廊的尽处,山路就此大转,蜿蜒而上。
“那个坏医生叫方怀,他说他们家族都信佛,取个慈悲为怀的意思。”我妈说。
“可他一点慈悲心也没有。”我说。
“说起我和你爸的事情,后面还亏了他帮忙。”
我诧异得一时语塞。
“他一肚子坏水,两头打算盘,却反而成全了我和你爸。”
一名女子对一个男人动了心,无论多么身陷囹圄,到决定对这个男人托付一生,总还要有个过程。这过程可以很长,或一生一世阴差阳错,也可以很短,或遭逢一场即海誓山盟。
十一年前那团朗朗的冬夜,滑腻的月色仿佛被人间的情思粘滞,迟迟不舍得换出太阳来收割幻梦。
将那个名叫梁方的男人抢救过来之后,无论我妈做什么,走到哪,面对什么人,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他的样子,连她上完厕所照镜子时,胸牌上都若隐若现着那张迷人的脸,怎么也甩不掉,好似业已生根。我妈觉得这个男人早不受伤晚不受伤,偏偏赶上自己值夜才受伤,自己又偏偏一眼就看上了他,冥冥之中恍惚自有安排。
心动必生心怯,刚猛如我妈亦不例外,何况梁方身份可疑,越加让她想打退堂鼓。谁敢轻易将一生赌在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身上,要知道,那块枪伤足以将这个人与世间任何罪恶扯上关系。
枪伤是个大麻烦,凭我妈在医院的位置,能够遮掩一时已经殊为幸运,要想真正瞒天过海无异于痴人说梦。尽管她在病历上做足手脚,把枪伤写成钢筋刺伤,且亲自领着梁方混过了重症监护室的收治检查,可重症科里那帮人岂是吃素的?搞不好第一次换药时伤口就会露馅,那样一切都将完蛋,毕竟没有谁会为了个疑是罪犯的陌生人陪我妈冒险。
我妈在急救科里彻夜徘徊,苦思到破晓时分,脚底板磨起了泡,愁得太阳穴直发胀,才终于想出个不得已的法子,只怕也是唯一的法子。
她决计兵行险招,谎称梁方是自己的丈夫,从外地回来出了意外,如此一来,她就可以顺理成章请假陪护,加上人是她抢救的,她熟知伤情,有了这些条件,请重症科开个绿灯想必不难。
医生平时大都累死累活,难得有位知根知底的同事主动分担子,谁不乐意呢?况且这种特殊情况必定要签责任书,确保万一出了事也是家属全责。好在那时我妈一个人住在外面,一贯独来独往,要是住在医院宿舍,这一招怕是连小屁孩都糊弄不了。
此计刻不容缓,我妈当即找到重症监护室的值班医生,明面上搬出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自己不想因私废公影响医院正常工作,所以才未第一时间表明家属身份。严格说来,即使是医院内部人员,作为家属签责任书也要先验明身份,可在翥山镇这样偏僻的小地方,规定往往不及人情管用,这种事在翥山医院早就见怪不怪了。
签完责任书,我妈马不停蹄去门口超市采办日用品,只顾得要买哪些,根本不选款式,拿起就往篮子里丢,像抢大减价似的。回来时也同样火急火燎,不料脚下打滑,在门口的台阶上栽了个大跟头,手脚摔出几处淤青,最后摇身一变,以梁方未婚妻兼主管医生的双重身份坐进了重症监护室。
人世间最要命的事情是什么,是那个人什么都没做,你就已为那个人走火入魔。
梁方睡了整整两天两夜,期间,我妈除了自身吃喝拉撒以外寸步不离,随时关注着他身体各项数据,比监护室里的仪器还要敬业。尤其是头一天,我妈愣是撑过了二十四小时,熬得满眼血丝,脑袋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才敢进值班室趴桌子,为防梁方夜里醒来,还特意叮嘱值班医生每两个小时叫醒她一次,像个反复起夜给孩子喂奶的新妈妈。
直到第三天早上梁方才醒过来,喂过水后,我妈示意梁方小声说话,虽然重症监护室的隔音极好,仍要以防万一,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出不得半点差池。
“我是你的主管医生。”我妈小声道,”现在……也是你的妻子。”
梁方脸上非但不见一丝诧异,反而会心一笑,像早已提前知晓似的,盯着我妈一动不动。
倒是我妈先不好意思,避开梁方的视线,接着说:“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你至少要一个月才能痊愈,从现在起你要叫我‘老婆’,人前人后都得这么叫,好形成习惯,以免露馅。”
我妈见梁方愣住不回话,道:“哑巴了?再看小心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寻常人动了这么大个手术之后,刚醒来时必定有气无力,可梁方真不一般,尽管压低了声音,却仍透着中气十足:“那……你该叫我什么?”
“梁方。”
“既是丈夫,直呼姓名不妥吧?”
“称呼不重要,语气才容易出卖两个人的关系。”
“那我也直呼,敢问恩公尊姓大名?”
“要你叫什么就叫什么,难道还委屈了你不成?”我妈说。
“不,我是怕委屈了你。”梁方一对眸子定格在我妈脸上,“老婆,谢谢。”
尽管已经预想过很多遍了,可真当梁方将那两个字叫出口时,我妈仍觉得很不习惯,一阵发懵。
“谢……什么?”
“你救了我一命啊。”
“救人是医生的天职。”
“那……谢谢你帮我隐瞒,大恩大……”
“慢!”我妈抬手打断道,“伤怎么来的,为什么不让报案?”
“取出的东西你丢哪了,那是特制的,要是被曝光,我这条命你算白救了。”
“我丢进医院后门的枯井里了,那口井枯了十几年,不会有人知道。”我妈说。
“我的衣服和兜里的东西呢?”
我妈拿出个透明密封袋,放到我爸床头,里面有一块圆形的白色玉佩、一张银行卡、一支录音笔以及少量现金。
“衣服全是血,烧了。”我妈说。
“别的丢了没关系,只是这玉佩不能丢,玉在人在。”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还有,那个东西上面的印记有什么特殊含义?”
不料梁方立即转过头去,不看我妈,说:“别问了,我不想连累你,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不是坏人。”
“我安排你进这里,就为避开外人,方便说话,既不是坏人,有什么不能说的,你不告诉我来由,同事们要是问起,我怎么应付,我总不能连自己丈夫怎么受的伤都不知道吧?”
“愿意的话,麻烦你编个好故事,否则就去报案,反正我的命是你救的,你随时可以拿走,被你拿去我死而无憾。”
“不识好歹,我欠你的吗?找死的人不配活着!”
我妈气得扭头便走。
“你当然欠我的!”梁方急忙说道,“你偷走了我的发动机,在你去报案之前请先还给我,好让我到时能落个全尸。”
“胡扯,什么发动机,我没偷过。”我妈回头道。
“这。”梁方摁着自己心脏的位置说,“你要是走了,我会原地报废,再也起不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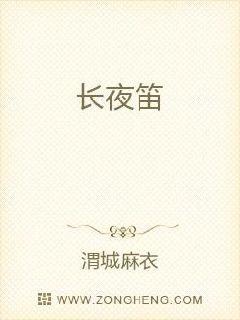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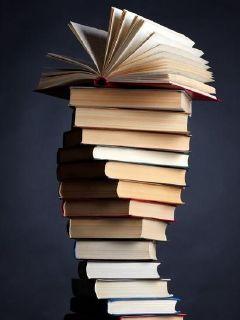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