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鏖战沙海(4)
李同自顾自脱光了跳进耙子湖,晨光里湖水冰凉,他用力搓洗着,里里外外梳洗干净了,顿时感到异常的舒爽,里里外外的衣服也洗的干干净净,晾在沙滩上。李同爬上岸,把莫博德拖到水边,皱着眉头道:“老莫,你这家伙太臭了,熏得我想吐。”
阳光刺破昏暗,洒下光和热,静谧的荒漠深处,洗干净的李同站在不深的湖水里,莫博德脱光了仰面躺在湖边,李同正在认真给他洗头发,他发现洗干净了的莫博德其实很耐看,年纪也不是很大,一打听才知道,这家伙今年还不到二十岁,比自己就大三岁,这家伙留着络腮胡子,两个人站在一起,乍一看倒像是差了一个辈。
“谢谢你!李同,我欠你两条命了。”莫博德突然冒出一句。
李同停下手上的动作,盯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老莫,你记住,如果你当我是兄弟,这样的话以后就不要说了。”
“行!反正我这条命卖给你了,今后我就跟着你。你打算怎么办?回汉军吗?”莫博德问。
李同想了想,说道:“我还没想好,说实话,我现在不想回汉军,想独自闯荡一下。你不知道,我这人是最受不得约束的。成为罪囚这半年多来,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想为自己活着。我打算继续前行,先去伊吾卢吧,走一步看一步吧,跟你说实话,我想在西域打下一片自己的天地,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你要不要跟着我?”
“呵呵”,莫博德露出笑容,无所谓的耸耸肩说,“当然,我没有问题,反正我现在是你的仆人,主人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反正匈奴那边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对了,我见你的武艺高强,而且识文断字。应该来历不凡吧。”
李同神色黯然,悠悠地说道:“家祖出自陇西李氏,我的先祖是飞将军李广,呵呵,不过我的老祖宗李广比较倒霉,打了一辈子的仗也没有封侯。我的曾祖父李敢运气也不好,稀里糊涂被霍去病杀了,虽然汉武皇帝补偿了李氏,但这于事无补。我的祖父因为是个奴婢生的妾生子,没有地位。李敢死后我祖父就被逐出了家门,开始以行医为生。没出事前,我家在大汉也只是个平头老百姓。”
“飞将军的后裔,难怪你这么厉害,我说一个汉军的小兵怎么会这么厉害。“莫博德听完眼睛都瞪大了,他有些激动地说道:”果然出生名门,你不知道吧,李兄弟还是坚昆王的族人哪。”
“坚昆王?”李同有些迷惑,猛然又想起,“哦,你说的是李陵吧,他已经死了吧。”
莫博德点点头,说:“是啊,李陵将军的确早就不在了,他娶了匈奴的公主当上了坚昆王,他的子孙后代还在。呼衍王曾经三番五次邀请现在的坚昆王进攻大汉,可坚昆王李陵留下了家训:坚昆绝不与大汉为敌。这事才作罢。”
李同听了点点头,叹了口气,没有继续刚才的话题。
俩人洗干净后躺在胡杨树荫下,云开日出,温暖的光照耀着赤条条的俩人。战马在湖边的湿地上甩着尾巴吃草。李同抬头,恰见一只雄鹰飞向天际,低头又见一只蝼蚁爬过了湖畔的小沙堆。
到了中午,李同从湖里捞起鱼篓。几条鱼在里面跳着,他冲莫博德晃了晃鱼篓,得意的笑了。衣服一会儿干了,俩人换上干净衣服,点了胡杨枝烤鱼吃。李同拿过最大的那条鱼,掰掉鱼头扔了,大口啃鱼肚子上的肉。可能是饿的很了,莫博德吃得非常的香甜,他吃完自己那份,又捡起李同扔掉的几个鱼头吃了还意犹未尽。
吃完鱼,李同起身割来香茅草剁碎了放进木碗里,用剑柄舂成糊,先敷了自己满是血泡的脚掌,又在莫博德左腿的伤口上敷了点,又采摘了一些鱼腥草,用刁斗煮好了让莫博德喝下去。
这一日过得慢,俩人总算是歇出了点元气。长日将尽时,李同用芦苇编出一张席子铺在莫博德身下。到了晚上莫博德发起了烧。李同心里很清楚,这家伙伤口发炎引发了并发症,可是他也无能为力,李同虽然医术高明,但这里根本找不到对症的药材,连最常见蒲公英也没找到。只能让这家伙的靠身体扛了,扛过去就扛过去了,扛不过去就只能够等死。
沙漠夜风中,李同用芦苇席子把莫博德紧紧裹起来,烧旺了篝火。到了子时,莫博德从昏睡中醒了过来,他蜷在芦苇席子里冷得磕巴,身上却烫的厉害。李同指着他的左腿,对他说:“老莫,得把这块烂肉割掉。否则这伤好不了。”莫博德脸色惨白地点点头。
李同拔剑出鞘,说,“我也没把握,这里找不到合适的药。割了这块烂肉伤口更大,能不能好很难说,你禁不住再流血了……”
“别说了,生死由命。“莫博德打断了李同的话,”你动手吧,这么拖下去也是个死。”
李同把剑放在火里烤,无奈地说道:“待会我多捣点香茅草糊糊,割掉烂肉就敷上,不知管不管用。兄弟,你一定要撑住啊!”
莫博德望着火里的剑,自言自语的说道:“我以前老想,自己应该会战死沙场……”
“闭嘴!死在沙子里有什么出息?“李同不耐烦的打断了他的话,安慰道,”老莫,除了打仗,这世界还有很多活着的方法。你是没见过我的本事,我告诉你啊,只要有了我能够做主的地方,我会让你过上你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你还别不信,你们匈奴人不会过日子啊!守着这么肥沃的大草原,只能够靠天吃饭,自己遭了灾就去抢劫,说白了,你们就是一伙马匪,如果是我手中有块那么好的地方,就会搞一个综合牧场,畜牧业和综合养殖业一起发展……”
莫博德微笑着听李同吹嘘,只觉得这家伙今天说话特别有趣。李同嘴里面絮絮叨叨,手上捣药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等李同做好了准备工作,莫博德掀开裹在身上的芦苇席子,拿过篝火边的一截胡杨枝,横在嘴里咬紧,冲李同点了点头。
李同上前解开了绷带,露出了已经发黑的伤口。他从火里取出剑,先慢慢提起整块被狼咬耷拉的肉,胡乱凝在一起的伤口重新撕开,里面的脓血涌出,莫博德死死盯着伤口,整个过程无一丝呻吟。李同提溜起整块坏死的肉,将剑锋对准根部唯一连接的一小块筋肉,猛一割,滋一声青烟冒起,烂肉离身。他扔了剑,先用刁斗里准备好的盐开水清洗几次以后,再拿过木碗,将事先捣好的香茅糊糊敷在鲜血涌出的伤口上。
李同的清洗和敷药的过程耗时很长,莫博德痛得目眦尽裂,浑身已被冷汗湿透,却狠狠吐了嘴里的胡杨枝,强忍着不出一声。李同望着地上那一大块烂肉不禁打了个寒战,看着那恐怖的伤口实在有些恶心,借故说道:“我去看看鱼篓子,你没晕就得接着熬,等会儿喝点鱼汤补补力气。”
到了半夜,莫博德开始上吐下泻,李同起来喂了他几次鱼腥草熬的水,发现他整个人都是烫的,正在发高烧。李同很担心这家伙熬不过去,尤其是怕他转为败血症,但此刻的他束手无策,只能打湿麻布给他物理降温。
沙漠里九死一生后,莫博德总觉得口渴,明明喝了一肚子水,还是不停想喝水。到了未时他失去了意识,裹在芦苇席子里失了禁。李同在现有条件下能用的办法都用到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这一夜,他找来了很多的胡扬树枯枝,又在他身旁又加了堆篝火取暖,然后静静的坐在旁边,仰望的星空发愣,一夜无眠。
暗夜无边,风声鹤唳。
第八天,南呼衍王麾下曾经的第一勇士,草原上有名的射雕手莫博德已经变得枯槁如鬼,他快死了!大小便失禁,浑身的尿味。李同也神情憔悴,他不眠不休的守了一夜,这家伙的病况依旧没有好转,这让他怒火中烧,又有些悲伤。他在这个世界实在太孤独了,他不想失去朋友!哪怕莫博德这家伙是个匈奴人。
烈日烘烤着这方小小的绿洲,李同掀开芦苇席子,捂着鼻子扒掉了大小便失禁莫博德的老羊皮袍和里衣里裤,他用碗盛来水,骂骂咧咧地为莫博德擦洗干净,又割了香茅草捣成糊给莫博德换了药。忙完这些,李同去湖里抓鱼了,留下莫博德全身赤裸着,伤痕累累地仰面躺在太阳下。
中午莫博德醒来一会儿,太阳明晃晃照得他睁不开眼,他伸手挡住阳光,转头望去,见李同正站在不远处的浅滩里收拾鱼篓。阳光下湖面水光潋滟,莫博德盯着波光中的万点金鳞,神情恍惚地问:“阿妈,这里就是陇右吗?我们的家乡真的好美啊……”他的脸上露出婴儿般的表情,独自在那里自言自语,仿佛是回到了童年。
正在这时,李同从水里抱起一篓子鱼爬上岸,“老莫,有口福了!我抓到条大鱼。”莫博德光着屁股艰难坐起,茫然点点头,愣了一会,李同惊奇地听他竟用流利的汉话唱起了诗经《小雅》: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目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榖,我独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谷?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鱣匪鲔,潜逃于渊!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
莫博德的语调凄凉,把《小雅》反反复复的翻唱,愣是把这支小调却唱出了大漠的萧瑟,也唱出了几分无奈。
李同感同身受,他抱着鱼篓呆呆的站在水中,泣不成声。
第九天。中午,李同添了胡杨枝趴在地上吹旺火,把鱼放在火上烤,肉香渐起,情绪激动地说道:“老莫啊!你他娘的把我吓死了。昨晚我都以为你过不去了,能活过来就是老天爷对你好,咱们以后要为自己好好活着。别一睁眼就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死那么多人老天爷会不高兴的。”
青烟袅袅,李同把串着胡杨枝新烤的大鱼从火里取出,递给莫博德,莫博德这次也掰掉鱼头扔了,啃着鲜嫩鱼肚,沉思半晌,睁着堆满眼屎的眼望向火光,也激动地说,“家主,我刚才说的想法是真的,西域这么大,凭着我们俩的本事,收拢一些野人,也可以打下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将来有一天陇西李家会后悔的,会亲自派人来请你重回宗族。”
“老莫,我就从来没打算回陇西李氏。我就是我,李家是李家,我跟他们不想有任何牵连。喂,什么时候你开始改口叫我家主,以家臣自居了?我可没有同意哦。我和你是兄弟,生死与共的兄弟。”李同边说边捡起鱼头,斜眼看着莫博德,吹掉上面的沙子把鱼头吃了。
“呵呵,理所当然的事。名分早已定了。在我的心中,你就是我莫博德的家主,作为家臣,让西域的李氏壮大起来是我们的使命。没有了目标,我撑不下去的!”
莫博德又吃了几口鱼,终于体力不支缓缓躺倒,李同摸了摸他的额头,叹息一声,莫博德烧得唇焦舌燥,脸色赤红。
李同很奇怪,这家伙不知道发了什么疯,这次清醒以后,就开始以家臣自居,替李同谋划未来。他要用自己的一生帮助李同开创一个西域李氏家族出来。莫博德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奇怪,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大汉还是匈奴,其实都已经出现了门阀世家的苗头,只不过表现出来的形式不一样罢了。
第十天。莫博德再一次陷入昏迷,越烧越厉害,开始用匈奴语说胡话,李同一句也听不懂。下午李同喂他吃了一条鱼,喝了点水。如此又过了三日,莫博德腿上的伤口在香茅草和太阳的曝晒下渐渐拔干。他不再说胡话,只是沉睡。
李同每天早上不厌其烦的把伤口清干净,挤出带着柠檬香的香茅草汁,淋在莫博德尚未结痂的伤口上。到了第十三天,莫博德开始退烧,一直水肿的腿开始消肿,腿上的黑紫也开始褪去。早上李同给莫博德换药时发现伤口有些地方开始结痂了。他戳了戳腿上结的痂,惊喜的发现,下面是硬肉不是软脓。这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狗日的!总算是把这家伙救回来了。此时此刻,他感慨万分:自己收一个小弟咋就这么难呢?
李同每日捕鱼,割香茅草捣碎给莫博德换药,闲来无事就跳进湖里畅游一番。天地悠悠,瀚海风吟,长河落日,苍浑静谧。
光屁股莫博德的腿上渐渐结出块巴掌大的痂,身体虽然虚弱,但脸色好了很多。到了自己能动时,他穿上了里衣,嫌麻烦没再穿上那臭烘烘的老羊皮。李同的战马不再怕人,熟悉了环境后,自由溜达在这片小小绿洲里。
李同认为这段时间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最幸福的时光。为此,他非常享受现在的安逸,甚至他会突发奇想,想要留在这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里并不具备长期生存的条件。要不是这个原因,他真有些舍不得这个地方。
两个人回望渐渐远去的耙子湖,竟然都依依不舍。不过现在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因为他们已经断粮了,只能够继续心情。
————
李同和莫博德这两个小人物的失踪,并没有影响到汉匈之间的战争。在两道不高的山坡之间,是一片微微下陷的很大的一片开阔地。在开阔地的四周,是起伏的大大小小的丘陵,上面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草和灌木。
站在任何一道丘陵上,都可以把整个开阔地收入眼帘。开阔地上,没有树,只有草。只是草已经让牛和羊都吃光了,没有了草,也就没有了牛和羊。开阔地上也有庄稼地,同样庄稼也早就收割了,看不到一个种地的人,充满了有些荒凉的宁静。整个开阔地,像是被打扫平整过了一样,把它变成了一个大舞台,正在等待这一出大戏的上演。的确,是有一出大戏要上演,这个大戏的名字,就叫汉匈大战。这个大戏已经排练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开幕的这一刻了。
在开阔地东面的丘陵上和西边的丘陵上,所有的演员和编导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东边的丘陵上,是来自东汉的士兵和将军。西边的丘陵上,站着的是匈奴的士兵和将军。汉军身披盔甲,整齐列队,由盾牌、弓箭、大刀、长矛还有战车和骑兵组成了不同的方阵。每一个方阵,看上去都像是一头凶猛的巨兽。
匈奴的军队,看上去没有那么整齐。但汉军有的兵器,除了战车以外,他们一样也不缺少。人数看出似乎要比汉军多出一倍以上,同样,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可怕的杀气。两边最高的那个丘陵上,站立着双方的将军。
东边将军的头顶上,飘着一面黑色的绣着红色汉字的大旗。西边的将军的头顶上,飘着一面蓝色的绣着一只野狼的大旗。他们是这出大戏的导演,并决定着情节的发展。但这出大戏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样?却不能完全由他们说了算。每一个参加演出的军官和士兵,他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将这些每个人的行为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可以说,整个这部大戏的结局,将由他们来决定。都明白这个道理,没有经过商量,两边职位最高的将军在这个时候,喊出的话,却是那么的一致。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你们要勇敢向前。
将军的话音还未完全落下,士兵们的回应,就像惊雷一样响起,让脚下的大地开始颤动。东边的大鼓擂响,西边的牛角号吹起。几乎就在同时,至少有上万支利箭飞上了天空,像是黑色的鸟群。
天上骄横的太阳,似乎都被这场大戏的开场吓住了,转身跑进了厚厚的云彩里,不肯再把脸露出来。天色,顿时昏暗下来。一场东汉和匈奴之战的大戏,终于已经上演了。
汉军的方阵经过了无数次的排练,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已经被预料到,刻苦训练得到了回报。前进的速度虽然有些缓慢,但是坚定有力、不可阻拦的。一开始,汉军确实占了上风,可匈奴人从来都不是这么容易战胜的。他们也许缺少战略战术和精确的配合,可骑马打猎的日常生活,早已经把他们每一个男人都锻炼成了骁勇善战的士兵。当匈奴人的马蹄踏破了汉军的方阵时,他们就像一群狼闯进了羊群。开阔地上干燥的沙土,变得湿润了。不断喷溅的鲜血,很快汇成了一条条小溪,流进了湖水里,湖水开始变红。
耿恭所辖部队没有出现在汉军的第一方阵里,甚至在第二梯队里也没有他的身影。在开阔地靠着天山一边的丘陵上,在一片稀疏的丛林里,他正和他的三百名骑兵静静地站立着。
耿恭的身体一动不动,不等于心也没动。透过一棵树的缝隙,他看到的是整个厮杀的场景。实际上,匈奴人砍向汉军士卒的每一刀,都像是砍在了他的身上,他的皮肉会疼痛,他的心会流血。汉军的方阵在顺利推进时,他为他们喝彩,同时也不想让他们马上取得胜利,因为他和他的士兵们还没有上阵。
昨天下午,耿恭走进了这次战役的总指挥奉车都尉窦固将军的军帐后,耿恭坦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是埋伏在战场侧面,在匈奴大军向前推进发生混战时,冲出来向敌阵的腰间发起攻击。匈奴人必然阵脚大乱,就算想逃跑,也会在这种前后夹击中死伤惨重。窦固将军想了想,同意了耿恭的建议,但要求耿恭必须在看到他的令旗挥下时,才可以发起攻击。
此刻,耿恭把目光投向了飘扬着汉军大旗的丘陵,盼着将军举起那面不大却威严的令旗。但他知道,这会儿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将军会在自己一方处于上风时,马上使出决定性的一招。
从黑风暴里侥幸生还的范羌站在他身边说:“耿司马,看来,用不着我们了。”
耿恭不耐烦地说:“少废话!范羌,你现在给我盯着窦将军手中的那个令旗。”嘴上这样说,可是握着刀柄的手急出了汗。
过了一会,耿恭又对范羌说,“传我的命令,等会儿冲锋时,都要紧跟着我,只要我背上的军旗还在飘扬,不管是谁,只要活着,就不许后退。”耿恭的装备与别人一样,身上有刀剑有弓箭,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在耿恭的后背上,还插了一面不大的汉军军旗。
与此同时,站在汉军大旗下的窦固将军,不会在意耿恭的着急。看到汉军的方阵在顺利地向前碾压,不断挫败匈奴骑兵的进攻,他的脸上出现了掩饰不住的高兴。这场战争的胜负,对大汉帝国来说,当然是重要的;可对他来说,更是与政治前途、荣华富贵密切相关。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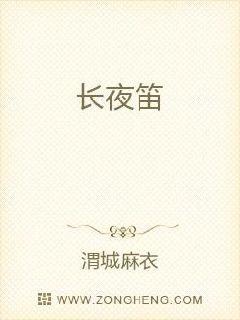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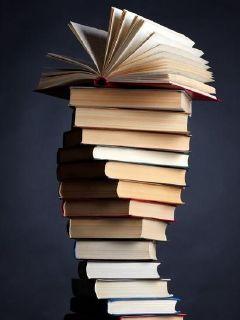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