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
姬昌恢复神智,已是来年春天。清醒后他颁下的第一道政令是即日起,周侯治下各类典礼,禁绝人牲,也不许人殉。在需要人牲、人殉的场合,一律用人偶代替,木偶、泥偶、布偶、兽皮缝制的偶……均可。唯独不可以用活人殉葬和献祭。
由于这道禁令,岐周境内逐渐兴起一个崭新的行业——陶俑业,大大小小性别各异的陶俑被成批量制作出来,以满足社会各界对人牲的需求。原本用不起人殉和人牲的小户人家,居然也排场起来,动辄弄几个人偶,买先人高兴,给考妣陪葬。原先就用得起人牲的那些豪门、军曹之类,改用人偶之后也都相应地扩大了规模,该用三个的用五个,该用十个的用百个,一个比一个阔气。与此同时,供人偶乘用的仿车、仿马、仿兵械,也一一造了出来,跟人偶摆到一起,几可以假乱真。到了后来,顶级人家殉葬,人偶成群结队,仿佛阴曹地府里的正规师旅(秦兵马俑的源头)。
他颁布的第二道政令,是即日起逐年减少人牲进贡,五年后彻底断贡,改贡其他美人珍宝。届时所有的俘虏将按军功大小分配到参战将士个人,给各家各户做劳逸,而不再由官家掌握,作朝贺贡品。
由于这道政令,岐周的田间、作坊,一下子多出来一大批有生力量,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兵丁们在战场上,更愿意卖命了。
第三道禁令:六种牺牲——马牛羊猪狗鸡,从鸡开始,分等级节制使用。在必须用“三牲”的场合,只许牛羊豕各一头,不许滥用。最高等级的祭祀,才允许用马,且只许一匹。
第四道禁令,是颁给姬姓宗亲的:本族女眷,无论何族何姓,自嫁入本族起,不许抛头露面,不许擅自外出;宗族内部,夫妻之外男女授受不亲;非祷非祭,男女之间不得传递物品(非要传递的,先放到地上,对方再取起);为人妻为人母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本族子女,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井、不共食;走在路上,男子靠右,女子靠左;女子出门,夜间无灯不出,白天须适当遮掩(“必拥蔽其面”)。
一望便知,前三道禁令都是有感而发,都是为了长子伯邑考的事。这第四道禁令似乎离得远了点,其实也还是为了同一件事,为了伯邑考的悲剧将来不再发生。那姬昌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假如早有这条规矩,他又怎会怀疑到自己长子的身份!又怎会在孩子的有生之年,带搭不理,给自己铸下那么多大错,留下那么多遗憾!因此,他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女人是祸水。不加以禁锢和约束,悲剧就层出不穷,天下就不得安宁!
第五道禁令,是颁给周侯子孙的:在严格执行第四道禁令的前提下,家族继承(无论财产还是爵位)实行立嫡立长制。特殊情况无法立嫡立长的,要在宗族内部说明缘由。
五令三申之后,姬昌带头实施。两件大事:一、设坛拜相,礼聘军师;二、立姬发为太子。两大盛典合二为一,占卜、献祭共用一套三牲,简明高效,震惊朝野。从此,岐周风貌大变。姬旦叹曰:俺大哥,死得值!
消息传到朝歌,朝堂之上激起轩然大波。
与外界传言相反,商王受徳看了周侯的禁令,非但没有恼怒,反倒暗自钦羡。里面除去第四条,他觉得对女人过于严苛、不足为训以外,其余部分他全部赞同。他更觉得,自己“向西学习”的国策,是做对了的。他之所以疏远昆仑、亲近岐周,不就是要推行立嫡立长吗?免除了多少内部倾轧、你争我夺!还有战俘入奴,他太赞成了!让他们做苦役,废物利用,远比把他们杀掉、埋掉,有益得多。继位以来,他已经力排众议,下令禁止了人殉。除非仆人自愿殉死,任何人不得用活人陪葬;他也禁止了豪门大户私用人牲;宫廷用羌,也大大限制了数量,目前顶级祭祀以百羌为限,回头还要继续施压,直至取消这一陋习。他觉得,西伯侯的率先改革,太是时候了。他要大力推广,借这个机会加速实现他自己的理想。
可是没料到,围绕这一议题,朝堂之上演绎出一场前所未有的对立。
拍手叫好的是飞廉、恶来、费仲这些平民将领,其中飞廉和恶来还是异邦逃奴。商王受徳在格斗场发现了他们,看这两人均有万夫不当之勇,因此分外怜惜,破格启用。现在飞廉是他的征东统领,恶来是他的七萃总兵,负责京畿戍卫(牧野之战,“武王亲射其口”的那位)。费仲盐商出身,与胶鬲同乡,子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他结识,相知甚深,如今是他的货财总管。他经营的巨桥粮仓(也叫囷仓,今河北邱县古城营附近),堪称天下第一仓,三年绝收也不至饿死人。
可偏偏这些能臣良将,在王叔比干、王叔箕子和王兄微子启、微子仲衍等人的眼里,还不如一只蚂蚁。有时候连旁观者都看得出来,他们不是反对对方的意见,只是不屑于与对方平等对话,甚至不屑于看对方一眼。在他们眼里,双方的身份差距,实在如天壤之别。和对方同处一室,对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侮辱。
这一回也不例外,飞廉他们拍手叫好,比干他们就坚决反对,而反对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我们不能愧对祖先!更难听的话在后面呢:咱大商什么时候成这样了,连祭献祖宗的区区几个人牲都出不起了?
其实他们真正想要说的是:要是连门面都撑不住了,你受德还不如早早让贤!
双方针锋相对,相持不下,商君就想听听中间势力的意见。父师疵、少师彊,是宫廷中有名的骑墙派,很多问题上都模棱两可。商君就问:你们是支持哪一方呢?二人答:“我们觉得,王叔他们说的在理,不能愧对祖先。”
商君闻言,暗暗有点吃惊。他觉得需要亮明自己的态度了,便转向王叔比干他们:“叔叔们说的都对,一直以来我们也都是这么干的。可是,那天在典礼现场,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我是说假如。假如那天被选中的不是伯邑考,而是你、我或我们的儿子,我们会怎么办?会不会跟姬昌老伯一样,悲痛欲绝,撕心裂肺?事过之后,会不会跟如今的周侯一样,誓言禁绝一切的人殉、人牲?我们还能够心安理得地用祖先做幌子来反对变革吗?”
比干他们面面相觑,朝堂上下鸦雀无声。
受德又补了一句:“我相信,拿我们的孩子做献祭,不是我们祖先的意愿!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爷爷,绝对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要以吃自己子孙为乐。”
“说得好!”飞廉、恶来等情不自禁喝起彩来。作为曾经的人牲,他们感同身受。
微子启出来说话了。他说:“王弟所言,不无道理。将来我老了、我死了,也绝对不会希望噬食自己的子孙。”箕子、比干等一干人就一齐望向他,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他可是他们的头儿啊,难道就这么轻易地屈服了?
他朝他们做了个不易察觉的手势,意思是少安毋躁。然后话锋一转:“可是,假如我知道,我的后代是被人皇选中,被天神选中,脱离苦海、一步登天,让他的魂灵去与他们做伴,不是一天半天,而是长长久久地做伴,永远做伴……我想我不会痛苦。高兴还来不及呢!”
箕子、比干等一大帮人,更加热烈地喝起彩来。比之改革派刚才的喝彩,音调高出了几倍,闹闹哄哄的,形同起哄。
顽固派成了绝对多数,朝议只好不了了之。大家不欢而散,商君叫住恶来,问他:“你怀疑那几个人与周侯勾结,今天的事又怎么说?他们把周侯的禁令骂了个狗血淋头。”
恶来叹口气,说:“大王啊,怕就怕他们朝堂上骂周,朝堂外通周。”
“有这种可能吗?”商君走过来,用手背试了试他的额头,笑道:“没发烧啊!”
“哎,对了,”商君又问:“我怎么看那太史辛甲有点反常啊?他以前可基本上是你们这边的。”
“谁说不是呢!父师、少师也是,都有点反常。莫非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
“哦,有这种可能。还有啊,那伯夷和叔齐,都说他哥俩能言善辩,今天却一言不发。你不觉得奇怪?”
“这倒没注意。让微臣打听打听吧!”
还没等他打听,那哥俩已经不辞而别,奔岐周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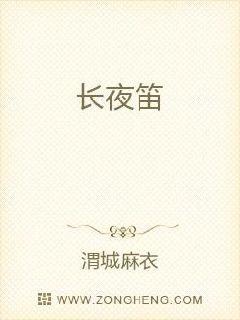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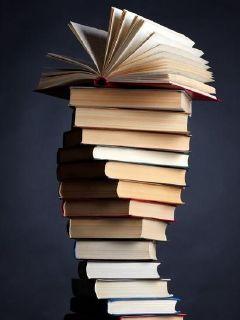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