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生产队那些事儿(下)
兰英情缘未了
大队的事,只要大队长拍板,就像是铁板上钉钉子。况且小白这事,也属大队长权限。大队长一锤定音,小白当生产队长,这事就定了,谁也扭转不了。
可是,偏有人不信邪。副大队长宣布任命,前脚刚离开,潘氏寡妇第一个站出来(老公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慢慢习惯就叫上寡妇了),公开反对。理由是小白在某天某夜,趁娃娃熟睡时进屋,更可气的是,表现不像个男人。从那以后,小白再不敢拿正眼看她,怕她躲她,就像老鼠见到饿猫一不留神就会被擒住生生地吃掉。
寡妇的男人,前些年被抓了壮丁。该杀的一走数年,再也没有回来过,留下两男三女五个孩子,大的刚过十三,小的两岁差点,外加一个瞎了双眼年过花甲的婆婆。岁月的风霜,过早地在潘氏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家庭的不幸和沉重的负担,全部压在她一人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本想一走了之,看看老的看看小的,狠不下心,再说当年挨刀的,与自己情意绵绵,心性相通,恩恩爱爱,招煞了多少傍人。有心改嫁,寻寻觅觅,难配适人,纵有动心的,过来相亲,挨枪子的连倒在缸子里甘甜爽口的井水也赖得喝一口。只有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长相像粗矮没有熟透的冬瓜的男人,想想可怜的双亲盼望儿子娶妻生子的眼神,停下匆忙的脚步,犹豫地慢慢地转过了头。可回过头,逃得比村子进了土匪还要快还要坚决,就像是兔子撞到了猎人的枪口惊得没命似的飞奔,眨眼间就闪过沙丘的背面不见了踪迹。
老娘真的很生气,想着要不是挨刀家的把老娘害得苦,就你这样的,哄,当年老娘未必会拿正眼瞧着你。老娘这样的脸蛋儿,三十几岁的年纪,稍稍保养,该当风韵犹存,二春花开也不是什么新奇怪事。恨只恨老娘命苦,早早没了男人痛,就像冬天里猎人丢失在树林里的猎物来不迟收网就被大风刮到旷野上,任凭它自生自灭。真真该享受幸福的青春,却已经是人比黄花瘦,人老珠黄不经看,灰黄头发,满脸皱纹,无人问津。这一天下来,老娘侍候老的,照顾小的,还要喂猪养狗,打柴挑水,哪一样都离不开她。只要她不在场,土屋里老的骂,禾坪上小的哭,鸡飞狗跳乱糟糟。
白天,潘氏与其他男人一样,外去劳动挣工分挣粮食,挑粪担谷,运土搬石,插秧车水,行行要会,样样照做。虽然辛苦,倒也充实。最难煎熬的,是漫长又看不到尽头的孤寂的黑夜,独自一人,以泪洗面,心里还牵挂着挨刀的,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到底还在不在人世。老娘不望财来不求贵,只图个平平安安,盼着一家人和和乐乐,比什么都好,都暖心窝。该杀的哪怕叫人捎一封信,一句话回来,都好过没音没息……
那挨千刀剐的在外面发达了,做了东家的乘龙快婿,当了陈思美,花花世界过惯了,大鱼大肉馋嘴了,不思想家乡,忘记了亲娘,不需要妻儿……
经常被这种恶梦惊吓,出了一身冷汗。掐掐脸蛋,有痛的感觉,恶梦醒了。为什么不做个美梦,哪怕一次,长梦不醒,该有多好。
其实,寡妇的男人,五年前偷偷地爬火车回来过一次。那是一个风雨交加雷鸣电闪的晚上,她和儿女们已早早在毛草土坯房睡下,似梦似醒,听得有个黑影在纸糊的窗户外面轻轻地叫唤:“英子,是我,我回来了”。听起来模模糊糊,像男人的声音。她不加思索,赶紧起身,下意识地从三两件衣服中扯出那件四个补丁舍不得常穿的红碎花棉布嫁衣,罩在上身,麻利紧了紧长年穿着的暗黑发白的破旧麻裤的裤带。快步走到门前,伸手去拉木门的木栓,又犹豫地把手缩了回来,稍稍停顿片刻,双手拍了拍白泛腊润的脸蛋,捋了捋黄黑齐腰的秀发,抻了抻棉布嫁衣的衣角。然后,用左手护住胸前,这才用右手拔出插销,横拉门栓,打开门板。门外站着一个身穿灰色雨衣,湿淋淋的男人,干瘦黄黑腊脸,满面络腮胡须,目光闪烁着惊喜,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多少个夜晚,多少次意境,魂牵梦萦,思念得心痛的男人,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出现在眼前。
她一时不知所措,曾经幻想过无数遍的喜悦情景,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中,原来竞不堪一击;她曾经重复过无数遍的温暖话语,当幸福真的来临时,却不知从何说起,甚至忘记要招呼男人进屋。男人没有犹豫,仿佛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样的珍贵,都是那样的吝啬。他以极快的速度闪进房内,把包袱丢到石凳上,转过身,盯着兰英,不由分说,抱起她窜到灶屋,不一会儿就滚到干燥的稻草堆里,没了影儿。整个过程,英子全身麻木,没得半点感觉,半点反应,甚至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她只能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男人,满意地起身,掌着昏暗的油灯,看了看亲娘,看了看小孩,眨巴着亮亮晶晶的眼睛,捂实着长满黄黑牙齿的嘴巴,夺门而逃。唯一留下的,是浓浓的旱烟味和难闻的汗臭腥,以及年后出生的满妹。
时空的转换,像坐在过山车上,没有来得迟感受,就已经一闪而过,等英子回过神来,追去门外,外面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天空的闪电一划而过,一切都无处可遁,明晃晃一道闪电,喀啦啦一声霹雳,灰色的豆大雨点冲砸下来。大黄狗一直蹲在黑暗的屋角,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像个懂事的孩子静静守护着主人,此时,昂起头在黑夜中“汪…汪…汪…”一通乱叫乱吼,像个明事里的孩子要为大人壮胆撑腰,宛如有人黑夜里撞到了鬼却又看不见鬼,为掩藏恐惧不得不做出壮壮胆子的姿态。随着一声由远而近沉闷雷呜的惊炸,兰英想起男人临走叮嘱:“我奉命调往一个很远很远的孤岛,恐怕很久很久不能回家,你要保重,等我回来。”英子奋力冲出门处,望着空空荡荡的黑夜,任凭雨水冲刷。她不再压抑情感,不再委屈自己,再也控制不住的泪水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一泄而出,干干脆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只有黑夜中明知发生的一切,却缩在墙角的地铺上默默装睡的婆婆,陪着她无声无息地悲伤地抽泣。
从那一夜始,兰英知道男人再指望不上了。今后还能依靠谁,她在心里筛过一遍又一遍,默念一番又一番。第一时间,白崽从她紧锁的心底冒了出来,那样的强烈,那样的迫切,那样的无需斟酌,那样的心甘情愿。
当年,白崽就是与男人一起长大,一起被抓走。白崽瘦骨伶仃,疯疯癫癫,部队嫌他糟蹋粮食,没过多久就被遣返回来。解放后,小白自然是同情怜悯的对象,加上红色的出身,光荣的履历,分配去喂耕牛、养水鸭、守仓库。这三种事情没有早晚,没得偷闲,工分还低,别人都不乐意做。白崽不嫌弃,照先前一样,傻乎乎乐呵呵,忙前忙后。可有两样,白崽不上心,懒得去管,一个是外表从不讲究,头发曲卷杂乱无章,衣裤下不遮体上不裹腹,剩两个黑珠子挂在白晰脸面上;二个是吃饭从不讲究,哪家有啥活,主动过去搭搭手,冷热不顾,稀硬不嫌,最后剩下的,他狼吞虎咽,将就些就妥了。如果有点辣椒,就喜欢得不得了,感觉像飞上了天。白村上下男女老少没有人不喜欢他,也没有人会尊敬他。老点的叫白崽,大点的了叫小白,小点的叫白椒叔,他倒无所谓,叫啥都答应。
小白,没有住的地,冬天,就着牛圈铺点干草合着牛粪味入眠;夏天,就着藤条织个网挂在枣树上听着蝉呜声昏睡。冬天,天寒地冻,不管冰霜风怒嚎,哪怕熟睡见阎王;夏天,闷热酷暑,蚊虫多,蛇出洞,嗑睡重。小白冬天易挺夏天难捱,蚊子就像轰炸机,一队接着一队,轮流进攻,赶也赶不走,打也打不散,比拼的是耐受力,就看哪一方坚持得住。大不了,起一身的血疱疱,长满身的红疙瘩。倒是蛇的危害要严重得多,一旦被咬,轻则受伤,重则丧命。小白,用臭草(鱼腥草)捣碎成渣,涂鸦在树上藤上驱赶毒蛇,点燃艾叶产生的烟雾熏离蚊虫。
小白,没有吃的地,东家瞧瞧,西家转转,半截黄瓜,半瓢稀粥,几口红署,一瓣南瓜,塞塞牙缝就成。小白也有心,队分东西,谷子,油菜籽,鱼呀,肉呀,他一概随手送送这家,丢给那家,一点不留。兰英对小白上心,也不是平白无故,主要是平日里,小白知她家人口多,工分少,粮食供需差距大,有意无意多给些。遇到接不开锅的时候,小白总是鬼使神差,就像及时雨宋江,看似无心无意,实则有备而来。手上不是鸭蛋,就是酒糟,不是谷糠,就是野菜。小白每次来得正当,恰到好处,纾难解困,怎能不让人动心,怎能不叫人猜想。
英子估摸小白的心意,也不是一天两天,自己也不是没有一点意思,只是碍于对男人还存留希望,抱着想念。可经那一夜,兰英对男人的半点思古也断了根,就像钢刀砍在莲藕上来回的拉锯,藕断丝也断。
白崽知道,兰英家要煮点啥吃,总少不了他那份,总是先让小崽送过牛圈来:“娘叮嘱,一定要看着白叔叔吃完,才能把竹碗拿回来。”这句话,比吃什么东西,都更让白娃受用,舒畅痛快。他不是没有想过,跟兰英家一块过,但是,怕辜负了她,更怕她男人回来。
当兰英会过男人,最后一点希望破灭,对其心死绝望的第二天夜晚,小白第一次去她家,她大胆主动的表白,确实吓了他一大跳。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的一张薄纸的距离,突然被对方捅破,小白毫无防备,只得落荒而逃。
从此,小白再也没有胆量迈进她那潮湿阴冷的小土屋,即使有时看她很可怜,他想像以前那样搭搭手帮帮忙,担心引来风言风语,更忧潘氏多情自误,只得就此打住,望洋兴叹。从此,小白只得躲着藏着,像六月天的狗被害了红眼病的花猫追着远远地逃开,不再象以前一样无拘无束,没肝没肺……
再后来,白崽就当上了生产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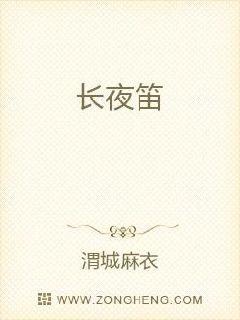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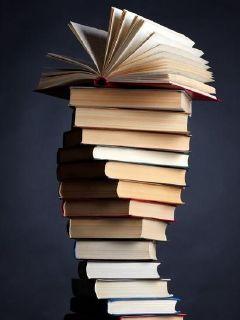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