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建丰巧破秘方,定远杀人诛心
(十七)建丰巧破秘方,定远杀人诛心
小年将近,寒风凛冽,像无形的剪刀,削剪着大地上的一切。路上被人踩化的积雪,和着稀泥反复融化又冻结,导致路面凹凸不平,又坚又滑,即使经验再丰富的赶车人,遇到这种路面,也是无计可施。张老爷的马车从张家庄到济元堂一路颠簸了二十多里,他只觉肠胃都快错了位,两个眼珠子上下蹦跶不停。
路过北大街时,张老爷习惯性地掀开了车帘,归一堂门口那位每天开门迎客的大掌柜,虽已多日未见,但他们生意还得做,门还得照常开。只是没有了伙计擦拭那块“敕造归一堂”的牌匾,看上去,已经蒙了一层灰。
相比于冷清的归一堂,济元堂如同菜市口一般热闹。许多人为了给家中的病人尽早排上队,夜里就守在门口了,等着济元堂开门后,依次登记,待医师到店按顺序接待。眼见着济元堂被病人挤破了门槛,张老爷只好在门口贴出告示:自本日起,本堂医师出诊仅限三里内;本堂张医师不再接诊,悉之。
不一会儿,张建丰骑着“溜烟”,带着自己的小弟张建川,从家中一路晃荡过来。他跳下马,蹲下,让弟弟骑在自己的肩头,把他扛到了楼上。
“你怎么把他带来了,瞧这小脸冻的!别吹着凉了!”张老爷抱下小儿子,将他的脸往自己的脖子上贴了贴,“哎哟,这冰的呀!”
张建川摆了摆双腿,从父亲的怀中挣脱,就去拨弄桌子上的台灯,开开关关不停。
“川儿,咱们在家说好的,过来要帮哥哥做事情,不要玩了。你要是说话不算数,以后都不带你来了。”
“那你快说要做什么啊?”张建川学着父亲的口气道,“我忙着呢!”
“他能做啥事?”张老爷一抬眼皮道。
“爹,您不是教他认全了家里所有的药和写法嘛!您把今年一整年每个月的进货单都拿来,让川儿一张一张念给我听,我要绘一张图表出来,然后把嫣红姐从魏家抄过来的单子也给我。”张建丰说着便在书架上取下一摞生宣,铺到地上,一张一张地用浆糊接起来,接了近二十米长。然后用尺子和钢笔在上面画了一千多条竖线,十二条长长的横线,将纸分成了一万多个格子。
张建川在一旁不停地追着问:“哥哥你在画什么?”
“画房子。”张建丰敷衍道,他伸了个懒腰,“累死我了!”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浪费我那么多纸。”张老爷习惯了大儿子捣腾新鲜事,也懒得管他,只顾自己写字。
“我在用科学的方法破您的秘方!”张建丰知道说出来父亲也不懂,“简而言之呢,就是学以致用,用数学教授教的统计归纳法来破您的秘方。”
“时候到了,我自然会传给你,你现在要了干什么?”
“我才不稀罕要,我就是做道代数题。”张建丰咬了咬笔杆道,“川儿,看你的了,你不是说比哥哥还聪明吗?把家里所有‘a’字开头的药都背给我听听,一个都不能丢哦。”
张建川高兴地绕着哥哥转起来:“阿魏,安息香,艾蒿,艾叶,奥尕……”
“再说一遍,哥哥没听清。”
“哥哥你真笨!”
张建丰将弟弟念的药名每隔一格,依次写在纸张的顶部,五百多味药,二十多米纸,正好全写完。然后在最右侧依次写下一到十二,表示十二个月份。他一手拿着印泥,一手拿着一个未刻字的石章,让弟弟从一月份开始念进货单。十斤以内便在相应的药下面的格子里,盖一个方方的红印,二十斤便盖两个……待到张建川将一整年的单子念完,纸上已被盖上了上万个密密麻麻的章。
张老爷搁下毛笔,走到儿子身边看得云里雾里,不知他究竟在做什么,但他一个堂堂大学生,是这个县里最有学问的人,这些奇异之术,又岂是常人能懂的。
“爹,您看出什么没有。”张建丰道。
“跟镇鬼符咒似的,我哪看得懂!”
“四月到九月,这四十三味药。红章盖得最多,都已经盖不下了。然后十月到三月,其中三十五味进货量大幅下跌。”张建丰指给父亲看,“这说明您的化疠丹配方,藏在这四十三味药里。为了掩人耳目,您配药粉经常要倒掉一些,所以要尽量倒最便宜的药。我猜测,这四十几味药里,价钱贵的前十种,定是配方,价钱最便宜的十种,全部排除。爹,您说我猜得对吗?”
张老爷听着儿子的分析,目瞪口呆,他说得千真万确!不由佩服起来。张老爷给儿子指了指道:“这十个是最便宜的,这十个是最贵的。”
“还剩下这二十三味药,您看,这八种药,什么甘草、党参、茯苓、当归、茵陈、枳实、元胡、黄连从一月到十二月,全年用量都很大,虽然我不懂药,但这数据说明这些是常用药,除了茯苓和黄连中间这几个月暴增外,其它药变化不算大,所以化疠丹含茯苓和黄连,不含其它六味。我猜对了吧?”张建丰得意道。
张老爷点点头道:“嗯,算你对了,还剩十五味,挑八味出来你怎么挑?”
“暂时还没有想到,您把嫣红姐抄来的进货单给我一下,我做个对比。”
张老爷遂将魏家的进货单交给儿子,只见他又在纸上密密麻麻地盖上黑色的方块。做完这些,张建丰顺着纸张来来回回走了几十遍,皱紧眉头,望了望父亲,又看了看地上。
“猜不出就别猜了,自己骑马回家去,川儿一会儿我带着。”
“爹,您心脏受得了吧?”
张老爷嗤笑道:“儿啊,你跟爹还卖什么关子!”
“爹,这个世界上的化疠丹,都有一半是咱们家的药对吧?”
张老爷点点头:“咱家和魏家一人一半。”
“那也就是说,归一堂的消耗跟咱们家是一样多。”
“只要是那十个方子的用药,消耗都是一样多的。但归一堂平日里生意要比咱们稍好一些,所以普通药材消耗肯定要多些。”
“爹,您先别写字了,过来看一下。”张建丰道:“四月到九月,您看这图上,这二十八味药,归一堂进货量比平时增加了十倍多,并且数量跟咱们相差不大,尽管每个月细看下来数字有出入,但六个月加起来的总数几乎一样多。其中有八味是咱们刚刚剔除掉的最便宜的药,做幌子用的。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张老爷听着儿子的话,看着地上天书一样的图表,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不敢相信地看了一眼儿子,摇了摇头:“不可能!决对不可能!”
“爹,百年前魏太医传方子给两个儿子时,就说了谎,两家的方子都是完整的配方。化疠丹的配方只有二十味,根本就不是四十味!魏太医把这个秘密带进了棺材里,是希望两个儿子和睦。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秘密一直没被揭开,也是因为大家都以为配方不一样,即使暗中查到了些蛛丝马迹,也不敢相信,还以为是自家的方子泄露了。”
张老爷还是不敢相信,摇了摇头。儿子信口开河胡说,根本不知道这个方子的秘密藏得有多深,更不清楚这一百多年里,为了争这个方子死了多少人,他的外公,外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这个方子而死。这个洪县最大的秘密,怎么可能是一个白痴都能猜到的秘密?
“爹,厉害的阴谋,都是看似没有阴谋,让别人猜破了脑袋,结果还猜不出来,这正是魏太医高明的地方。如果您不信,下次有人得瘟疫,试试就知道了。”张建丰见父亲还是不肯相信自己的话,笑道,“秘方我知道啦,您以后也不用搞得神神秘秘了,还说什么只能单传,我才不稀罕!”
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上天让嫣红用命换来了这些单据,就是为了让张家得到配方?张老爷看了看岳父的挂像,又伸手托起儿子的图表,摸了又摸:“丰儿,这事还说不准。现在就只有你我父子二人知晓,不能乱传。”
张建丰向弟弟呶呶嘴道:“川儿也知道了。”
“他那么小,知道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哥哥知道秘方了!”
“嘘——”张建丰抱起弟弟,“川儿真厉害!”
张老爷擦着火柴,点燃一根香,朝岳父的挂像拜了拜:“爹,师傅!如果丰儿说的是真的,明年清明,我可以去看您了吧?”
“爹,不用等清明,咱们家腊坟还没上,明天我们全家去山上呗。”
张老爷笑道:“丰儿,你做事不要总那么猴急。来,你也给外公点一根香,肯定是他在保佑你,暗中敲了一下你的脑袋,灵光乍现,解开了这个谜。”
张建丰道:“爹,什么外公保佑不保佑的,这是我代数寒假作业!教授让我们自己找数据,自己分析图表得结论,我也不知道找什么数据,就拿柜上的进货单试试了。”
张老爷道:“你大部分都猜对了,不过还有一味‘密陀僧’,用量极微,一年才进一次货,你这图上也看不出名堂。你光知道有什么药,具体每种药用多少量,你也算不出啊。”
“爹,这个您心里知道就行,但用量比例,归一堂跟咱家肯定是一样的。儿子无意窥视,您什么时候想告诉我就说,不想告诉我,您就传给川儿,我不可能将来还回济元堂当郎中的。”
张老爷拍了一下儿子的背:“你将来想干什么,爹不会拦着你,好男儿志在四方!快给你外公拜一拜,给你弟也点一支,一起拜。”
张建丰拉着弟弟一起跪下,念经般道:“外公,我没见过您,我娘说她生我的那一天您走了。谁让您不多等一会儿呢,那么着急干什么。您现在看看我呀,我长这样,我娘说长得像您年轻时候,可我看您的画像一点也不像啊!我十八岁啦!这是我弟弟张建川,也是您外孙,他六岁啦。来,川儿,快磕三个头,喊外公小年好!我还有一个妹妹,叫素翎,我爹跟您说过的吧?她十岁了,裹脚在家里不能动。我不让裹,爹和娘非要她裹,天天疼得哇哇叫。您在天之灵,给爹娘托梦,让他们不要再给妹妹裹脚了,现在已经是新社会,新时代了。”
张老爷揪起儿子的耳朵:“起来起来!磕个头都不正经!”
这时伙计上楼通报:“老爷,魏老爷来了。”
张老爷一惊,让两个儿子赶紧下楼回家,张建丰轻声道:“爹,他问什么你都当不知道,说都是从报纸上才看到的,和咱家无关。”张老爷点点头,赶紧将案台上供的孙嫣红的灵位收了起来。
魏老爷被请上楼后,二话不说,噗通一下直接就跪下了:“张老爷,表姑夫!求您大发慈悲,放过我儿吧!”
张定远赶紧去扶,无奈他就是硬跪着不起来。只见他头发糟乱,灰白相间,眉毛长得老长,耷拉在眼皮上,眼角溢出了白色的眼屎,好似几日都没洗过脸一般。肤色蜡黄,一身憔悴,喘着粗气,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响。
“令郎之事,我也深感痛心。如今判决已经下来了,已再无翻案可能,年前三天就要行刑了,我看你还是去南京找找人,去牢中探视探视,送他最后一程。快起来吧!”
魏老爷干裂的嘴唇颤抖了起来,眼睛像两口枯萎的老井,已渗不出水来。他忙磕头道:“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教好儿子,张老爷,您把我的命拿去好了,换他一命行不行?”
张定远见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起来,便也在他面前跪下了:“魏老爷,您这是何必呢,三太太的确是我岳父家的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但毕竟十几年前就嫁到了魏家,我们张家与她也仅止乎与礼。她的生死,与我们真没多大关系。”
魏老爷咳了几下,张定远忙起身倒了一杯水,加了两片糖姜,递给他道:“魏老爷,你我之间素无过节,归一堂在您接手后,与我们济元堂也再没生过嫌隙,大家相安无事地处了十几年,各赚各的钱。我不知道魏老爷您何出此言啊?再说家父也仅是个九品芝麻县官,南京可是天子脚下,他若要伸手,简直如蚍蜉撼树。”
“这么说,真的不是你在背后唆使?”魏老爷起身,被张定远搀扶到桌子边坐下。
“您看我,整日在铺子上看病,哪儿都走不开,要不是报纸上登出来了,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张定远无辜地说道,“令郎这事如果在洪县倒也好办,周局长多少要给家父点面子。我说令郎既要烧房子斩草除根,不应该疏忽大意,万不该留下活口,让那个家丁跑去了省里告状。省里直接下令抓人,我家老爷子也没办法啊!你说要是抓起来就关押在洪县,倒也好办。只是这事不知怎么地就让省里的记者知道了,还发了稿子去了南京。谁也没想到的事啊!本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怎么现在那些报纸就喜欢搬弄是非,瞎起哄,左右判决,还有没有王法啊!”
“我可怜的儿啊!”魏老爷呜咽了起来,“张老爷,我儿要是没了,归一堂后继无人啊!那秘方我留着何用啊?”
张定远一听,了然于胸,知道这老狐狸在试探他。如果自己表现出想买秘方,那想置魏展文于死地的人必然是自己。张定远颔首道:“事到如今,魏老爷,我就不隐瞒了,实话跟您说了吧。那方子,我前年就知道了,只是念于这是你们家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还是依照老规矩在您那儿拿药,我们不是过河拆桥的人。”
魏老爷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惊讶不已:“你如何得知?”
张定远道:“前年您大病,魏大掌柜开始主持家务,以为您撑不了多少时日,他又不愿跟两个弟弟分家产,就将那十副方子一并悄悄卖给了我,三十万大洋。三太太上个月不知怎地知道了这事,一直吵着要他吐出来,一家人均分,但他不愿意。这回三太太怀了野种,大掌柜的这个事就是她的保命符。三太太最后一次上我这儿来,跟我说了这些话!回去后没几天就听到消息说她失踪了,我猜测啊,她被关起来后,大掌柜怕她跟您告状,便连夜杀了她。不是报纸上写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觊觎母色。”
魏老爷听后战栗不止,张着嘴巴像被馒头噎住,他站了起来,死死地盯着张定远,抖着手指着他道:“你……你说的……是真话?”
“使君子五钱,苦参六钱,半夏五钱,柴胡四钱,槟榔八钱,密陀僧一分……”张定远背出了化疠丹自家的一半配方。
魏老爷绝望地一屁股坐下,好似魂魄都被妖邪吸了个干净。张定远一看他的神情,便知大儿子果然猜得分毫不差,化疠丹果然真的只有二十味中药,张魏两家的方子是一模一样的!这一招简直就是一箭双雕,一来撇清了和魏展文案件的关系,张家并不是为了夺取秘方而想置他于死地。二来让魏家明白,张家掌握了完整的配方,给你一口饭吃便给,不给,你的丸药就别想做出来,以后不管谁当家,就别再心怀不轨打张家主意了。
“魏展文,我不仅要你血债血偿,我还要杀人诛心!我要让你爹憎恨你,厌弃你!让你成为魏家的不肖子孙,叛徒,败类!让你爹觉得你死不足惜!死有余辜!让你死了后,也进不了魏家的祠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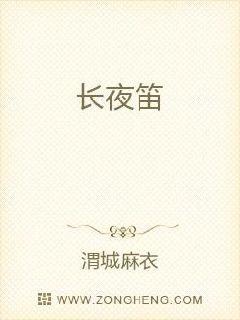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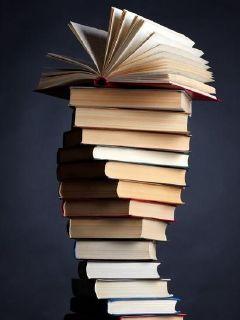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