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送信
六月二十一,夏至。
这座江边小镇难得太平了一段时日,江水退了不少,码头也恢复了涨水前的繁忙,不过宁秋去武馆给吕先生当差,小日子过得倒是愈发有滋味,平日里看那些个膏粱子弟练拳,有意无意还能学个一招半式。
单就最简单的扎马步而言,十二个新弟子中也就属沈长风能跟宁秋一较高下,宁秋这一身武神的筋骨无人调教也着实可惜,千里马还需伯乐一顾。
宁秋给吕先生当差之后手脚变得麻利了许多,就最简单的端茶倒水而言,宁秋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倒是能够同时兼顾快与稳,茶水一次也没有洒出。
宁秋快步走出武馆,手里拿着一封信,那是吕先生亲笔写的,他让宁秋送去县衙给县令,也就是沈长风他老爹。
县令沈肖已经是个过了半百的老头,作为镇子的父母官,沈肖办事也称得上亲力亲为,在全镇百姓的口中好评颇多,为人正直,办事讲求效率与质量兼并,镇子上几乎没有出现冤假错案。
县衙在整座镇子的中心位置,距离武馆还算近。
宁秋很快便来到了县衙门前,不过大门前面围了一大堆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少年不明所以,闷着头挤到人群的最前面,站到了县衙大门的门槛内。
此时县令沈肖在审理案件。
沈肖在上面端坐,公堂两旁分别站着数个持水火棍的衙役,皆怒目圆睁,中间跪着两人,地上躺着一具男尸,跪着的分别是一男一女,男尸用白布盖着,后脑处泛着血渍。
那男子面容清秀,眼神中透露着些许戾气,不时瞟向旁边的女子,那女子面容憔悴,眼白泛着血丝,像是大哭了一场,模样楚楚可怜。
沈肖开口厉声问道:“陈生!地上的死者跟你是什么关系,你为何要杀他?”
被唤作陈生的男子直言:“回大人,草民与死者并无牵扯,草民也并未杀他,请大人明查!”
陈生话音一落,那女子便立即反驳道:“你撒谎!是你将我相公唤去江边,最后一去不复返,不是你杀的还能是谁杀的!”
沈肖捋了捋胡须,思量了半分。
陈生瞪着那名女子,破口大骂,:“你个贱人!你不要血口喷人!”
沈肖见状立马将惊堂木一拍,公堂上随即鸦雀无声。
沈肖让右边的衙役前去查探尸体,尸体后脑部确实形成一个茶杯口般大的凹陷处,凹下去约一个手指头的深度。
尸体是今天早上在江边乱石推里发现的,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可以得知,死者是当天晚上亥时左右失去的生命体征。
衙役对沈肖耳语了一番,沈肖像是恍然大悟般,说道:“陈生,你是什么时候与死者去江边?又何时离开?”
“酉时去的,戌时离开。”
“可有证人?”
陈生连连点头,道:“有!卖饼的张安张大伯!”
“传张安!”
片刻之后,衙役将一个驼背的老头带到了公堂上,老头浑身散发着葱油饼的香味。
宁秋在外面看得越发有味,全然忘了自己是来送信的。
张安说道:“老夫确实是酉时看到他们二人一起走去江边,也确实是戌时回来。”
张安刚说完,一个衙役从门外来到公堂上,手里提着一袋瓷片,带着血。那女子看见碎渣,心头一震,手摩挲着裙摆,心绪不宁。
那衙役高声道:“禀大人,在死者家中发现瓷瓶碎片,碎片上血迹斑斑。”
沈肖挥一挥衣袖,示意他退下。
沈肖扬声道:“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那女子摇摇头,泪水从眼角滑落,道:“我无话可说。我认罪!”
“为何谋杀亲夫?”
“是他自找的!”
沈肖长叹一口浊气,道了句:“秋后问斩!”接着摆摆手,示意衙役将那女子带下去。
惊堂木拍下,一声退堂之后,沈肖便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
围观的群众也渐渐散去,宁秋对衙役说道:“我找沈大人有事,麻烦大哥去禀报一下,嘿嘿。”宁秋塞给那衙役三五个铜板。从小混迹街头巷尾的少年怎能不知那些个官差门道。
那衙役掂了掂手中的铜板,没好气地说道:“在这等着!”随后离开。
片刻之后,那衙役出来,将宁秋带到了沈肖面前。
沈肖显然认得这个从小就满大街跑的苦孩子,说道:“是你小子,找本官何事啊?”
宁秋掏出那封略微褶皱的信,呈给沈肖,道:“这是吕先生要小的交给您的。”
沈肖接过信件,拆开来,看了之后哼笑一声。
宁秋没有多问,鞠了个躬之后退出了县衙。
回到大街上,人潮拥挤,这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宁秋可不想这么早回去,开始闲逛起来。
宁秋回到了落红巷,想回去看看离开几个月,自己家的房子变成了什么鬼样。
推开门,一切如常,依旧寒酸简陋,若说变化,那最多就是落上了一层薄薄的灰。
宁秋并没有过多留恋,没多久便关好门出了小院。
巷口,宁秋遇到了陈泽鸣
陈泽鸣上前轻轻锤了宁秋一拳,带着质问的语气说道:“最近又去哪里发财了?”
宁秋回道:“哪有,倒是你,几个月不见,长高了不少嘛!”
“那你说,你到底去哪里了?”
宁秋挠挠头,说道:“说来惭愧,我现在在给武馆的馆主做事,待遇还蛮好的。嘿嘿!”
宁秋搂上陈泽鸣,豪气道:“走,大哥请你吃饭去!”
两人大踏步来到饭馆,点上了几个小菜和一壶酒。
席间,宁秋问道:“泽鸣,你说人们为什么习武呢?”
陈泽鸣摇摇头,道:“不知道啊,威风吧。”随后自顾吃着。
宁秋又问道:“那你想过习武嘛?”
陈泽鸣抬起,说道:“之前没想过,现在……可以考虑。”
“你听说了嘛?”陈泽鸣接着说:“最近镇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拳手,拳法甚是精悍,一边抓贼,一边找人比武,扬言这世间没人是他的对手。威风得很!”
宁秋将信将疑,出语:“有这种事?看来你大哥我孤陋寡闻了啊。”
两人畅谈一番之后各自离去。
——————
云泥寺内。
声响如雷震般外泄,究其原因,竟是一魁梧的莽汉与苦行和尚过招。正如陈泽鸣所言,莽汉正是那行走江湖的拳手,莽汉招招轻浮暴戾,苦行被迫应战,如若不然,这云泥寺就会被此人毁了去。
苦行也非等闲之辈,身为佛门中人,能行医济世不说,更是身怀高强武艺。苦行处处忍让,出招不下死手,他知道这个莽汉的目的并非是砸这个小寺庙,而是想要找人比武。这些日子莽汉的名声早已传扬千里。
那莽汉跃至三丈高空,挥起重拳砸向苦行,势如陨石坠地,凶悍如虎,苦行见势躲避,向后撤身,莽汉的重拳砸在寺院的地砖上,震起石屑三尺高。
苦行落地,心头一震,心想这么躲避不是办法,这寺院可没有这么多地砖供其练手。
苦行和尚褪去身上袈裟,眼神比先前要凌厉不少,脚步也沉稳了许多。莽汉招式爆烈是不错,却也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便是速度。相较于苦行而言,那莽汉无论是出拳速度还是移动速度都要慢上不少,这也是苦行镇定自若的原因。
当莽汉还沉浸在那撼地一拳的快感中时,苦行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早已来到了那莽汉的身后,使出一记佛家覆云手,扼住莽汉的前颈,同时往后撤步,只见那莽汉整个身体如山倒般砸向地面,苦行力度拿捏得十分到位,若再出一分力,这地砖又得裂开几块。
莽汉一个鲤鱼打挺,支起身子,面向苦行摆好架势,眼神迷乱了几分,晃晃脑袋之后继续向苦行出拳。
莽汉先前从未遇到像苦行和尚这般难缠的对手,打了半天双方都未伤其分毫,不用说流血,就是汗水也没有几滴。苦行出的都是软绵的擒敌招式,意不在杀敌取胜,而是降服对手,莽汉却截然相反,处处下死手,招招夺人命,莫说普通人,便是自幼习武之人遭了他一记重拳都会不省人事。
胜负还未分,院落墙头因二人打斗而损坏之处不下三十,三尺厚的院墙被莽汉的拳头凿开十几个窟窿,损坏的地砖不计其数。
苦行有意躲避,莽汉就连其衣角都够不着,其实胜负早已得知。
莽汉顿足,朝天大呼一声:“太他娘不痛快了!”
苦行见此,恭敬说道:“施主,你我二人各退一步,双方战平如何?若是同意,老衲给你指一条明路,保你战个痛快。”
“什么明路!?”
苦行掐了掐手指,脸上露出一抹微笑:“镇上有家武馆,那的馆主才真正是你要找的人,老衲遁入佛门,不便与你厮杀,所以,我们算战成平手,是双方受益之举。”
那莽汉厉声厉语:“行!平手便平手!只是待俺去打赢了什么狗屁馆主,俺再好好跟你打!”
苦行重新披上袈裟,环视周围的残破景象,道:“只是,施主您打烂的这些墙砖瓦砾,当如何?”
那莽汉豪气地甩给苦行一大袋沉甸甸的银子,道:“少不了你的!”
随后那莽汉离开了云泥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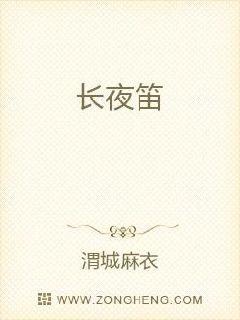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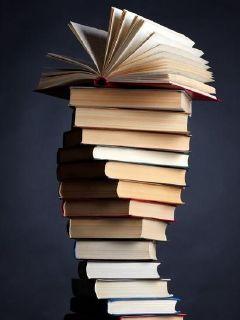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