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朝阳
走出楼门的卢夏没有想到,他就这么稍微显摆了一点,就被三个臭皮匠,不对,或许是三个诸葛亮把他们师徒给差不多研究明白了,还从中得出了更多的内容。想想也是,他一个二十不到的小青年,在老狐狸面前是无所遁形的。
重新回到那个军官面前排队报名,军官眼睛瞪得很大,看着廖仲恺的字条几乎不敢相信,给了一张表格让填完,告诉去另一边体检,卢夏拿回字条,小心的夹在毕业证书中,放入书包,就去体检,体检很简单,走两步,伸伸胳膊,蹬蹬腿,量量身高,测测体重,看看牙齿,视力听力,问问有没有隐疾之类的,完事大吉。表格上交,换了准考证,军官告诉27日小南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考试,不得有误。卢夏乐了,他就住在小南门附近的小旅馆,这下方便了。高高兴兴朝外走去,心里想着要不要回头给三位道个再见,没两步就打消念头,初次相识,没那个必要,来日方长。
走上江堤,准备原路返回,江边树下,俩人边聊边有一搭无一搭的打着水漂,没太注意,走了过去。熟悉的大嗓门背后响起“嘿!兄弟,报上名了吗?”回头一看,俩军装年青人,分不清是官还是兵。俩人都中等个头,大嗓门戴着一副小圆眼镜,热情洋溢的圆脸,笑脸,看着就透着喜庆,另一位浓眉大眼,一脸方正,略显拘谨,感觉还有点稚气。赶紧回走冲圆脸抱拳打招呼“报上了,还没谢过兄台,小弟还未请教”,圆脸透过镜片有点斜着看着他,转转看看,“书生?不像啊,别搞那文绉绉的,我叫陈赓,他叫宋希濂荫国,你叫他小宋就好,反正他最小。我们都是湖南人,你那?”,“我叫卢夏”“别报字号,麻烦!”卢夏心说本来我也没打算说呀。“直隶的,你们在这干嘛呢?”“等两个朋友,他们去的晚些”,陈赓上前轻轻锤了锤卢夏肩窝,感觉挺壮实,又问“你多大了”,“二十”,“比我小两岁,比他大两岁”。卢夏重新称呼“陈大哥”,看着宋希濂荫国,他也是活泼的年青人呀,嘴里逗着“小宋兄弟,嘿嘿”。宋希濂有点不高兴,估计是不愿意别人说他小。叫了一声”卢兄”,陈赓看着卢夏,“你就叫我名字,也别大哥了,你这叫法以后大哥满天飞,一指宋希濂,你也喊他卢夏,名字吗,本来就是给人叫的。不过我们叫你吗”,俩人异口同声“小宋”。
年青人凑在一起,大家都很高兴,卢夏也不着急回去,三人席地而坐开聊,“你俩穿着军装,莫不是已经当兵了?”还是陈赓搭话,宋希濂真是个好小弟,“我们在湘军广州随营军校,很没意思,就想来黄埔军校”,“你怎么来的?担保信也没有就闯来了?”“我家在直隶南皮,县城连报纸都没有,更没听说有国民党了,哪儿找人担保啊。先生告诉我这边黄埔军校的消息,我就来了,运气还不错。”“你跟着那教官进去一说你先生名字他们就同意了?”“哪儿是啊,我先生没啥名气的,那教官进去跟其他人商量一下,就同意我报名了,所以我说运气好吗”。卢夏不愿意说廖仲恺给自己开的条子,免得别人误会自己攀附,这种事还是少说为妙。陈赓狐疑地看了卢夏一眼“我听说这次招生很严格的,好多省份,尤其北方,不仅要担保信,还有初试,你两样都没有,直接来了就能考试,估计也没别人了。”卢夏还能说什么,嘿嘿傻乐,赶紧转移话题。“湘军很能打的啊,随营军校不好吗?”“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也学不到什么东西”。“陈大哥以前当过兵?”陈赓这次没在意称呼,站起来拍拍胸脯,“老子十四岁就当兵,跟枪一般高,四年老兵!”卢夏有些吃惊又有些佩服,还有点羡慕的看着陈赓,“打过仗吗?”“你应该问打过多少仗!”
“陈赓你又在吹牛啦!”,身后传来清朗的湘音,不疾不徐,三人回头,看到俩人,当前说话这人,看着只比卢夏略矮一点,不过气势很足,国字脸,大眼弯眉,眼睛很有神。后面一人又略矮些,圆脸,好看的双眼,剑眉直鼻,整体配合起来就显得有些严肃。陈赓道“这可不是吹牛,事实吗,共产党员不说假话”,陈赓伸手一拉,卢夏就势站起,宋希濂也站起来。“巫山,给你介绍个新朋友”,一指卢夏,“你们自我介绍”,卢夏先说“卢夏,直隶南皮”,这人说道“蒋先云,湖南新田”,卢夏有些纳闷,陈赓明明称呼的“巫山”,估计是这人的字号,他不是嫌麻烦不喜欢说字号吗。这事过了很长时间卢夏才偷偷问宋希濂,原来陈赓对蒋先云是又怕又敬。后头那人道“李之龙,湖北沔阳”。又序了年齿,蒋先云比陈赓还大一岁,李之龙最大,比蒋先云还大五岁,前清光绪二十三年生人。陈赓扒拉李之龙的手腕看时间,“快到饭点了,李之龙请客,巫山选地方”。卢夏有些不好意思,不想去,陈赓看出来了,直接拽着他的胳膊走“你从那么远的孤身地方来到广州投身革命,以后我们更会是同志、同学,袍泽,一起去。李之龙工资最高,我们吃他大户。哈哈”。卢夏不再扭捏,想想以后回请就是了,“我去,我去,你松开”。五人边走边聊,他们四人原先就认识,好像是无意识的,又很自然,聊天的时候蒋先云总能让卢夏感觉到自己没被冷落。
沿江一路是广州的繁华地带,蒋先云选了个看起来挺干净的饭馆,也没要隔间,五人大厅落座。“先来壶茶”,陈赓道。店小二奉茶,还送了一小碟瓜子。五人聊起广州的革命形势,其实都是他们四个在议论,卢夏本来就知道的很少,安安静静听着。广州现在是革命的中心,随着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实施,大量共产党人和有志青年来到广州,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革命力量日趋壮大。他们四个人都有些小兴奋,感觉孙中山自民国6年设大元帅府以来,虽几经起落,但自去年重返广州,年底又确立了三大政策,革命形势前所未有的好,孙中山一直念念不忘的北伐似乎也有了希望。
但以卢夏的见解来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北伐,光有革命热情是不够的。其实内中原因一戳即破,孙中山没有本钱,他的革命,腰上别的是别人的脑袋,两年前的陈炯明叛乱,就已经很能说明原因,表面上看是孙陈的北伐之争,理念之争,但其实内中情由很多,孙陈矛盾几年间已经积累到临界点,邓铿被刺(邓演达叔叔),双方表面上的温情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说到底,还是利益之争。孙要下赌场,用的却是陈的本钱,陈觉得赌本太小风险大,不干,孙就翻脸了,这能全赖陈炯明吗?或有人说,孙是大元帅,陈就应该听从孙的命令,那其实也是不对的,因为现在的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代表中华民国行使国家主权。孙陈不过是地方割据势力,过分一点说,就是俩叛贼。大贼头是绿林总瓢把子,声望卓著,但因各种原因,手头没兵;小贼头在大贼头手下若即若离,江湖多年也有了点实力。大贼头找小贼头商量打劫大户,说那大户的好多护院多多少少都跟我有点关系,咱俩联合,定能赚的盘满钵满。小贼头一听,你MD忽悠我那,即便能成,死的是老子的人,赢的是你的名,坚决不干,掰了。孙中山北伐,说到底,还是要有兵才行。听着四人的谈论,再加上卢夏自己的了解,你还别说,现在孙中山有兵,而且还不少!
现在的广东,是中国军队山头最多最乱的省份了,没有之一。除本土的粤军,还有滇军、桂军、湘军、福军,陈炯明叛军,邓本殷叛军,最离奇的是还有一支豫军。这其中滇军分为两支,湘军也两支,互不统属,福军应该算是一支私军。粤军、陈部内部也都不是铁板一块。粤、滇、桂、湘、豫、福都从属于孙中山麾下,五省联军外带一个福军,实力强劲。但在卢夏看来,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视角不同。革命者站在广州的立场上,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广东,分裂、军阀割据的北中国;卢夏刚从北方来没几天,他的屁股还没那么快坐到革命者一边,北京政府代表着中华民国,南望中国,那就是各省割据,叛贼处处,各省内部也是分割离析。南望的终点广东,也同样如此,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大旗之下聚合的各方势力也是各有其利益述求,尤其是各支客军,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广东,与本土粤军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分歧,甚至对立。因此,现在的广东,完全称不上是一个有战斗力的整体,不能说一盘散沙,但也不遑多让。当然,现在的卢夏对这些军队的了解还不是非常透彻,他甚至不知道那支豫军是非常忠于孙中山的,也不知道这支豫军是怎么来的,豫军也是其中人数最少的,但战力不弱,这支起于草莽的军队,为了追随孙中山,从河南一路杀到了广东,看起来总瓢把子和草莽英雄很登对,热血总是容易被感召,历史从来都如此。孙中山北伐,腰上别的还是这些脑袋,至于这些脑袋愿不愿意被别,卢夏就不知道了。
饭菜上来了,议论并未停止,饭桌上聊天谈事是中国人的天性,四个人的探讨依然很热烈。卢夏也并没有因看到广东的局面而沮丧,他来广州,本来就是奔着为消灭军阀割据,统一国家,进而维国权、护民生而尽自己一份气力来的。而这四个人与他的想法是一样的,使他颇有一种广州同道如此之多的欣喜。其实他不知道,如果他对广州再深入了解一下,此刻在广州的青年,尤其知识青年,绝大多数都和他有着同样的梦想或者叫理想,何况这些投奔黄埔军校来的青年,几乎没有例外。卢夏更不会知道,他已经融入一个伟大历史的开端,这些青年的热血,将会从浇灌广东开始,在这片祖先留下的土地上用鲜血浇筑出自己的印记。
卢夏渐渐融入话题,他就是问,绝不评论,尤其是涉及到军队,他问的更多,也问的很细。话题不知怎么就到了国民党右派上面,李之龙显得有些激愤“这些右派必须打倒,否则三大政策就不会很好贯彻执行”。蒋先云说道“在田说的有道理,三大政策如果被破坏,没有了苏联和我党的支持,以及工农的辅助,北伐成功的难度极大”。“那就坚决打倒他们!”这是宋小弟。蒋先云看了一眼话很少的卢夏,对视中两人似乎心里都在叹息“哪是那么好打倒的啊”。卢夏早发现了蒋先云的话总是很到位,没有咄咄逼人却又带着令人折服的气息。蒋先云也发现卢夏总能问到点子上,比如他问这些军队与大元帅府的关系,这些军队的粮饷从何而来等等,一句都没问有多少人枪!这是两人订交的开始。李之龙问“复华,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宋小弟认为卢夏知道自己的表字,他也有权知道卢夏的表字,嗯,大家就都知道复华了)“都不是”,“哦,你对我们共产党有了解吗?”卢夏苦着脸说道“在田兄,我除了认识共产党三个字,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四人有些诧异,很快又释然了,想到卢夏刚到广州,而党在北方除了北京,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存在感,也就不以为意了。其实他对共产党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点的,他知道苏俄,他的先生给他讲过现在苏俄的来龙去脉,先生对苏俄就一个字“呸!”他也知道孙越会谈,孙越宣言,当时先生还出题考他,他把脑海中先生的教诲,西洋、东洋、国内,杂七杂八,浆糊一般搅合了两天,交卷,四个字“远交近攻”。先生有些欣慰,又让他再想想,这一想就是一年多了。先生那个时候已经很少去帮他下结论了,更多是让他自己思考,或许先生那时就已经知道,雏鹰就要单飞了,能否穿风透雨,翱翔九天之上,自己要有一对坚强的翅膀。
蒋先云接着刚才没讲完的话继续“国共两党之所以是合作,而不是合并,这就说明两党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山先生以其个人威望促成三大政策的实施,国民党内部是有不同声音的,国民党不是我党那样坚强的战斗集体,其组织结构与我党差异甚大,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开始就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体,有共同的政治诉求,也有不同的利益区隔。两党合作是为了打倒军阀,恢复国权,为此我们要坚定执行三大政策,对于国民党右派,我们要坚决斗争。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党首先要扎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合作中发挥我党最大的作用”。卢夏心中感慨万千,不能小觑天下英雄啊,看着那几人佩服的眼神,也不知道他们听懂内中蕴含的意思没有,两党、合作,做好自己的工作,国民党不曾对共产党指手画脚,国民党分左中右,那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共产党凭什么打倒国民党的右派,要打倒,那也是孙中山的事情,但是态度必须有,那就是斗争。卢夏甚至觉得是不是“斗争”这个词都有些激烈了,他还没搞清楚蒋先云为什么不明说,以为蒋先云很会说话,顾及“打倒”派李之龙和宋小弟的面子。他现在对共产党一无所知,当然也就不能这上面出声了,他感觉,合作,很好吗,都是中国人,为了共同目标,当然要团结合作。
又说了会儿话,也吃饱了,卢夏也跟他们互相留了现在的住址,道别而去。走在回去的路上,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想着今天见到的三个国民党人和四个共产党人(宋希濂还不是,他不知道),都是初识,却没有疏离感,嗯,很好,很美妙的感觉。一路走着,左看看,右瞅瞅,买了几份报纸,回到旅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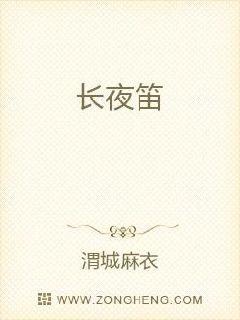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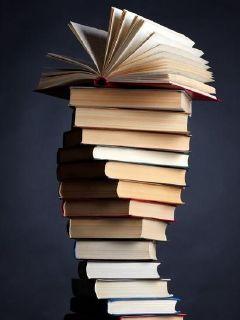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