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当奉献变成了取舍(九)
我习惯于用世间所有的美好去揣测我将要经历和面临的事情,不过在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才发现我始终是一个心存善念的未长大的少年,世间的丑恶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巨树,蚍蜉撼树根本无从谈起,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更是一场笑料。所以人们习惯了从微小的事情中获取满足和幸福感,幸福感变得越来越多时也就会抵消掉种种不顺心,转念回想起来,压迫在幸福上的不顺心其实会逐渐摧毁微不足道的萤火之光。
而在最后我选择了另外一个牌子的食用油,虽然没用过,但是上面有好几个欧盟认证的食品级标识,我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虽然不是大牌子,至少有国际的认证肯定不会差到哪去,再怎么说国际认证的东西也比自己浅薄的见识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在我去工地的第一年,也就是第一次去工地的时候。南北方地域的差异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当时我并不以为有多大的区别,毕竟走进社会看到不同的世界,首先是先要具备了解世界的能力,再次是你看到的世界是不是真正意义上不同的世界。说实话当时照样在乡土农村社群中度过的,唯一改变的是环境不同、地点不同,但经历的事情和人几乎是没变的,我当时面对的话语圈子也是不变的。可能老师变成了大工和领班、同学变成了小工和同样辍学来工地的甲乙丙丁。
后来我也去过一些地方无论是工作还是参加会议,都没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象。想来我还是刻板偏见存留在脑子里太深刻了,在面对新鲜事物时总会用在维系了二十多年情感的乡土信息套用,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不同的地方也是一成不变。直到我去了一趟四川,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冲击后才发现世界原来多姿多彩。当时能去四川也是由于一个女孩儿,而那个女孩儿与我之间的情感纠葛好几年,那位女孩现在是否在为自己而活我不敢苟同,只是她确实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在上初中时,我成为了一名寄宿生,现在想起来初中的时光留给我最深刻记忆的事情无非三件事,其一就是我在下晚自习的第一天晚上,看着黢黑 的操场对面穿透过的惨白的宿舍灯光,一点点一点点的映照在半个操场的头发上,黑亮的头发攒动,当教学楼上所有教室的灯全部关闭,我站在教学楼下面,心脏颤抖不停,当时我几乎都快哭出来。我没想到世界上居然会有这么多的人,当时我所面对的世界就是学校。至于我有没有跟我母亲说过此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在我上初二那年,我母亲有一次跟我、我小姑姑、我父亲聊天时说了一句:当初上学时回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学校里面那么多人,你害怕。你说你有什么可怕的啊?不就是人多点吗?哪没有人啊?我不知道当时别人是如何回答的,我只记得我低下头谁都不想看,在心里还埋怨母亲怎么一点不知道关心我的状态。后来我发现,我的小学同学很多也去了市里读初中,他们在与我为数不多的每次交谈中,都会兴致勃勃地讲起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不论是有趣还是无趣的,我不懂他们怎么就不害怕人多不多呢。当然讲的最多的依然是拉帮结派的事情,还有怎么样才能避免受到欺负。
其实在初一的某次地理课上,地理课本上讲到了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同时也是人均资源很匮乏的国家。我那个时候的脑子不太灵光,根本不懂什么叫人均匮乏,只知道人口最多的国家这让我很自豪,完全忘记了当初第一次下晚自习时我站在教学楼下面瑟瑟发抖的样子。
而让我害怕与人交往、害怕人多环境的状态有所改变的是,有一次我母亲来学校看我,那时正值午休吃饭期间。我们新生总是端着饭盆在学校的操场上随地找个位置就开吃,如果运气好还能坐在篮球架子上。我实在想不通那时的我们是单纯到令人发指么?就连吃饭都不敢弄到教室或者寝室一屋子饭味儿么?其实更多的是不想在教室或者寝室遇到班里的小流氓,他们总会抢夺饭盆里面的荤菜,即使那点肉少的可怜,我们舍不得一口吃完就成为了他们明目张胆且毫无廉耻的肆意妄为。那天我们围在一起蹲在操场上吃饭,我母亲对周围的几个同学说:大家都相互帮助帮助,都是同学要一起好好玩好好学。说完又给我打了一份菜,弄了满满一饭盆放在我面前。临走时跟我说:你看看你表哥,他在学校就是闯得猛,吃饭的时候总是跑在最前面用两只手掐满包子,你也多学学。我到现在都记得这句话,尤其是那个词闯得猛。我很清楚这个词对于年幼、害怕、萎缩的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我并无法理解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只知道每次中午打饭的时候我都使劲往前挤想要尽快打饭,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挣脱内心的枷锁,让我心里稍微放松愉悦一点儿。
在我母亲走后,我周围几个根本不太熟悉的同学也拿着自己的勺子在我盆里一勺勺舀菜吃,并且说大家需要相互照顾。我记不清楚当初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了,只知道用一两勺菜可以换取一份陌生的友情还挺好。直到前一两年的时间我才真正明白很多模棱两可的事情,尤其是友情这件事,拿所有东西换取来的根本不叫做友情。只有建立起你内心的堡垒,让堡垒浇筑成坚固的长城抵御侵袭时,友情才不会崩坍。
小时候我的邻居是搬过来的,那个时候我才4岁左右吧,他比我大一岁,所以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至今我们也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他家刚搬过来时跟胡同的街坊都不太熟悉,不过村里人基本上都相互认识,仅仅没有达到远亲不如近邻的程度而已。那时候他父亲做木匠活,所以家里有很多工具,他自己的东西每次用完都收拾的井井有条,小东西用盒子装起来,大东西放在干燥的地方。我当时并不太懂这些有什么用,也从来没有样学样的做过。后来有一次我发现他家用喝完的核桃露的易拉罐做了好几个油提子,大家估计都见过很早之前在农村小卖部、供销社打酱油、醋的大水缸,每个里面都有提子。他家做的是缩小版的,因为是用铁皮做的,看起来更有光泽、圆润和有骨感。我当时看了很惊讶跟他说:这是谁弄的啊?他告诉我是他父亲弄的,我当时对他说让他父亲给我家也做几个吧。后来这件事在某天晚上很多人在胡同口打牌歇凉时被他母亲说了出来。我母亲听完后说道:你爸爸也会做,回去让他给你做几个,你拿着玩。我很小,不明白大人之间的这种对话意味着什么,只是感觉我父亲并不会做这些东西。晚上回到家我母亲又特意嘱咐了一句:以后别在外面说这种话,想玩什么跟你父亲说让他给你做。我没吭声,我不能感觉父亲是否能做得出来。那时的我多一半回忆的是我没尝过的核桃露的味道吧。
等我再大点了,我们家买了一辆可以变速的自行车,在当时很稀少。我朋友也有了一辆女式的小的自行车,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玩,他正在用油擦拭自行车。我问他这有什么用,他告诉我可以把自行车保养好,不容易生锈。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意思,直到多年以后我那辆引以为豪的变速自行车经过无数次的风吹雨淋暴晒之后变成了一堆废铁扔在了垃圾堆了,才明白当时在我朋友的自行车上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我偶然听到父母聊天,聊所谓的发财命之类的话题,我父亲说当时我朋友他们家刚搬来是,他父亲就弄了一个磨面机和压面机来挣点零花钱,当时在我们北头村没人能想到用这种方式挣钱。而他父亲一直从木匠工人做到了我们村很大的室内装修队,一年到头都在忙着给别人装修房屋。我朋友从高中辍学后,学会了开车,买了一辆很大的冰柜车,开着车从南到北的给各个村小卖部送冰棍儿、冷饮、雪糕。
即使我们是邻居,每天几乎都见面玩在一块儿,受到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小学三四年纪的时候,那时我都10来岁了。从来没见过乒乓球、篮球、足球这些东西,有一次去我小姑姑的学校,她给我一块乒乓球板儿,给了我一个乒乓球,告诉我让我在墙上练习打,等打的很熟练了能接住球来来回回拍个几十个的时候,再给我一块好的拍子让我继续练。回家之后我玩了两次,全没接住球,后来那块板儿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估计是当劈柴烧了吧。
好像是同一年吧,我去小姑姑家遇到了从市里放假回来的表哥,我小姑姑让我跟他比赛拍篮球,我让他先拍,他说话不怎么利索,并不是口齿不清晰,而是脑子太活泛,导致表达能力跟不上思维的速度。他拍了两下对我说:我能一直拍下去,你根本就摸不到球。后来他毕业落户在北京,有一年他生日打电话叫我去,期间我们聊了很多,我有很多困惑。他说了很多我只记得一句:当年我考上清华,虽然成绩不错,但去了那才知道人人都是天才,我根本拼不过语言的表达能力,但是我能跟他们拼智商。有一次他贴出来一张跟SKY的合照,写着两大人皇的合影。
我小姑姑有一次跟我说,你表哥小时候不知道从哪本书上看到了胡萝卜对身体好,营养元素很多,吃肉过多不好。他就记住了,每次吃饭总是吃很多胡萝卜、蔬菜,吃很少的肉类。当然现在长大了,哪个好吃吃哪个。
我看到过他读的那些书,小学读的书加起来都得有两大箱子,比普通人一辈子读的书都要多。
我就见过一次我小侄子,那时候他还很小。现在4岁多点已经上幼儿园了,过年期间我乘坐我小姑姑的车回到市里,听到了她跟我小侄子的通话,说话利索,口语清晰,表达能力很强,我小姑姑说你小侄子比你哥哥小时候聪明多了。很多事情不用教就会。现在我小侄子接受着良好的学校教育,在家享受着一位北大硕士的父亲、一位人大本科的母亲的教育,再差能查不到哪里去?
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市里读初中的小学同学,只有一个算是出人头地了吧,在校期间年年得奖学金,毕业后在实习期间跟她男朋友一起攒够了西安的一套房的首付,现在生活富足而且大有前途。而她妹妹在她的影响下以专业课第一名毕业后顺利进入央财入职。
而她始终贯彻着一条生活准则,我一定要拥有自己一套房子,把我父母接过来住,让他们脱离农村。
在她读完大学读研期间,同为小学同学的另一位女生,算是她的表亲吧。那位女生的母亲跟她说: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回来跟我女儿一样在市里找个工作,一个月挣个1500,不一样过日子么?你应该早点工作让你父母别那么操劳。
她跟我说:她说着我就听着,也不反驳,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衔接的话题与思想,这样的对话在我的耳边上回想了无数次。也许那位同学的母亲可以从只言片语的被主流媒体黑化的新闻中了解到作为一个研究生毕业后面临着怎么样的就业压力,而同样她更无法了解到从农村走出去,走到大城市落脚成功并拥有广阔天地的女孩儿同她的女儿有着怎样的天差地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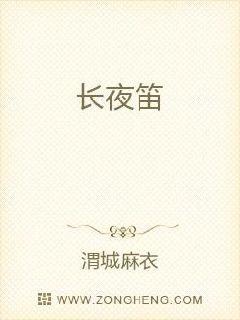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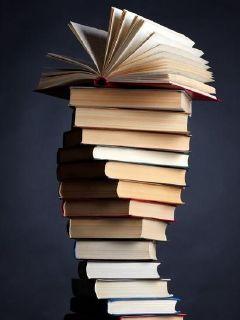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