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徒儿救师
那匆匆上楼之人,正是燕幽。
“殿下!林教头被捉了!”
赵元凌猛地回头,脑海中的念头电光火石般闪过:得罪了谁?人心险恶,如今也要落到自己头上了吗?
“哪个衙门捉的?”
“正是开封府!方才说大尹有案子,就是在审问林教头啊!”
赵元凌皱皱眉,向陈与轩欠了欠身,随即便告辞离开,赶往开封府衙署。
陈与轩将信来细看,却是一惊,自己是撞了何等大运,竟得堂堂皇子殿下的举荐啊。
………………………………………………………………………………………………
花开两头,各表一枝。且不论赵元凌怀着满腹的疑惑前往开封府,单说高太尉府中之事——
但见一个梳着螺髻的女孩儿哼着小曲儿,蹦跶着从角门进了院子。
随即便有个约摸三十出头的女子一把将她拉住,低声道:“我的小祖宗,你可算回来了。教习的嬷嬷可等了有一会儿了,你若再不回来,她恐怕就要去找娘子叫人寻你呀。”
这嬷嬷说话间便上下打量这女孩儿,摇着头道:“姐儿啊,你这又是上哪儿野去了?满身都是泥点子。”
“是唐家哥儿找我出去玩儿的,我能推却吗?”
那嬷嬷随即啐道:“好个唐家哥儿,诗书礼仪学不会,单学那市井三教九流的活计,还要带坏咱家鸢姐儿。”
那女孩儿却道:“插花做茶之类的繁杂礼仪,有什么好学的,真是不痛快。”
“姐儿啊,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你还是离那唐家哥儿远些才好,莫要嫌嬷嬷啰嗦,这都是为你好。他家家道中落,巴巴儿地与你做一处,谁知不是来攀附的?”
“哎呀呀,哪儿你想得这么严重嘛……”
说话间才留神,从衙内屋里断断续续传来哀嚎,女孩儿心里不定有多高兴,便问那嬷嬷:“好嬷嬷,我那哥哥这是又干了什么坏事儿被人收拾了?”
那嬷嬷摇着头,声音更低了:“他呀,自投你爹爹以来,仗着家里的势为非作歹,这回可是遭了报应了。”
“哦?却是何人如此大胆,真真是个豪杰!”
“先顾你自己吧,又要挨教习嬷嬷的板子喽。”
……………………………………………………………………………………………………………………
“阿嚏。”赵元凌也打个喷嚏,揉着鼻子道:“有人念叨我。”(自恋)
燕幽一路上将自己听到的都告与赵元凌道:“围观的百姓说:林教头带刀直入白虎堂,犯下了死罪,至于细节,杂七杂八的,小人一时间还未理清楚。”
“嗯……”说话间到了开封府衙前,赵元凌猛醒,对燕幽道:“林教头被开封府捕了不曾回家,林娘子定然焦急,你快去报与她,定说教头无事,叫她耐心等待。”说着又对元彻道:“七哥儿,你也陪我转悠了大半日,先自回府去吧。”赵元凌这回说得决绝,元彻察觉到了赵元凌的着急,他而今多说一句话都嫌多,于是便不再恳求,只是拿出自己随身的银两道:“哥哥要做事,定然用得着。何况哥哥还未曾用膳,不回王府,也不可饿着自己,胡乱吃些个。弟弟这就回去。”
赵元凌自己倒是慷慨,把随身的银两全给了个素不相识的士子,而今自己遇事,也只好借弟弟的银两。元彻一向善解人意,他俩虽非一母所生,但却比同父同母还要亲近,也不必推辞。
却在此时,几个军汉从里面出来,赵元凌见了心下更急。入内瞧时,众人都散了,府尹也已退堂歇息。
赵元凌只恨自己晚来,放眼瞧见一个洒扫的老军汉,上前问道:“请问老军,不知今日当案孔目是哪位?”
“是一位姓叶的孔目。”
赵元凌遂掏出一两银子来到:“不知老军可能为我引见?”
这老军拿眼瞧着赵元凌,望他衣着不凡,出手也阔绰,便欣然应了下来。
“哦,麻烦老军将他引到王婆婆茶馆。”
那老君自应下了。
赵元凌便仍上那茶馆,陈与轩已然离开了。
不多时,叶孔目便上楼来与赵元凌坐一处,赵元凌道:“叶孔目可曾看过今日林教头故入白虎堂一案的案卷了?”
那叶孔目心疑道:“不知足下何人?”
赵元凌却不作回答,接着问道:“若孔目看过了案卷,应当知道林冲是被冤枉的,此案尚有诸多疑点。”
那孔目随即感叹一声道:“这我又如何不知呢?莫说是我,府尹大人也清楚林冲的冤屈,可押送林冲的军汉是要了回文回去的,林冲有罪,已无转圜的余地了。”
赵元凌敬上一杯茶道:“那是否真要判处死刑?”
那叶孔目呷一口香茗,点点头。
赵元凌沉思片刻,恳请道:“叶孔目可否说得那府尹大人将林冲减罪?”说着便将银两全部拿出。
那叶孔目倒也不推辞,只道:“愿尽力一试。”
赵元凌点点头,胡乱吃了些,便取了马匹,直奔大内。他本该去殿帅府将那两个承局抓来做人证,只可惜他虽是个亲王,却无半点儿职权,根本不得与两府官吏有任何往来。纵使如他亲王之身,危难时却也只能任人摆布,毫无还手之力。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爹爹身上了。
“阿嚏!”赵佶也在用膳,今日陪宴的正是朱琏的爹爹。
他昨日闻听高衙内调戏自家闺女,气得面色发紫,却也没柰何,正要暗自咽下苦果,也因她的女儿的好名声,却不知如何早传到官家耳里,官家这些时日里正为太子和几个出阁亲王的婚事担忧,正想起朱琏来,便召来其父。皇家与将门结亲,原是祖宗遗风,正是一件大好的事。
谈的已然有了眉目,好好的心情,却被个喷嚏搅了。
“想是连夜来着了风寒(官家你是唯一一个承认着了风寒的),撤了吧。”
服侍御膳的太监于是便熟络地将蝶儿碗儿都收了。
却听官家接着对朱伯材道:“那你我两家可就那么说好了,咱们这就先把婚给定了?”
“权凭官家定夺。”
“我恐怕你们家姐儿还看不上我们家大哥儿呐。”
朱伯材忙谦道:“殿下乃是国之储君,孝悌恭俭,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岂是寻常人家能比呀。”
官家随即也到:“你们家姐儿才叫真真羡煞旁人,我可恨不得直接过继她为国朝公主啊。”
两人正商业互吹间,却见高俅冒冒失失地进来,一见了朱伯材,面上立马有些不自然,朱伯材就更不自在了。好在官家算放过他了,他便如蒙大赦,径直出宫去了。
“卿有何事?奏来。”
高俅便将一叠奏劄奉上道:“黎洞王韬降而复叛,已下数寨,请陛下圣裁。”
“嗯……黎民因愚蒙而复叛,颁下旨去,叫地方州府恩威并施,剿抚并举。”
高俅应下,又道:“枢密童贯上疏称西北边储尽失,请陛下拨下国帑,以修边备。”
官家于是又应了下来。却见高俅愣在那儿,只是不动,便道:“卿还有何事,一并奏来。”
高俅进宫时便瞧见肃王也在外头候着,猜想他是为着林冲那厮来圣上面前求情,只自己已然恶了林冲,绝无再放归的道理,加之他恃宠而骄,也想在皇子们面前树立个威信,便故作姿态道:“陛下,臣险些儿见不着你啊。”
“出了何事?卿速道来。”
“陛下,今日臣去枢密院点军,不料想禁军中一个姓林的教头突然杀出,且备有宝刀在手,便要暗害于臣啊,亏的是堂外有人,将那教头绑了送往开封府,否则臣便没命来见陛下了。”
“竟有此等事?”
“禀陛下,那教头前些日因点将来迟,臣下令笞四十,他便怀恨在心,要害臣丢掉性命啊,也不顾自家的下场,实乃亡命之徒啊!”
“着开封府仔细审理,务必还卿一个公道。”
“谢陛下垂爱。”
官家刚发下话要给高俅伸冤,赵元凌便也闯进来声称自己有冤。
官家闻听自己的儿子也有冤要诉,不觉好笑道:“哦?今日这是怎么了,寡人的重臣和皇子都被人给欺负了?(官家你不知道,他们是互相欺负),五哥儿有什么冤屈,也一并奏来。”
高俅知道陛下乃至皇子们的偏好,自然也是知道赵元凌暗中尊一个禁军教头为师之事,只是他从未过于关注过赵元凌,因此并不知晓赵元凌究竟拜何人为师。然而赵元凌是个刚出阁的皇子,怎会知晓这其中许多曲折?怎会料到一个臣子做出监视皇子的事情?此刻便也不知高俅要害林冲还含着欺侮皇子的意图。
“爹爹,儿子的恩人,爹爹要不要救?”
官家当即便奇怪了:“何人竞对我儿有恩?”
“是一个禁军教头……儿子先行请罪。”赵元凌知道私自拜师的罪过,便主动先服软。
“这……有何罪呀?”官家倒是被赵元凌的两句话给弄晕了。
“儿子私自拜他为师了(还以为对你有恩就要以身相许了呢,皮一下)。”
“你可好大胆啊!”官家的脸立马阴下来了。
赵元凌作可怜状道:“爹爹且请听完儿子的话嘛。爹爹也是知道的,大哥、三哥、九哥都是诗书大家,儿子比他们差上一大截儿呢,可也想做爹爹的好儿子,为爹爹争气。儿子虽愚鲁,可也颇知些道德的,那禁军教头虽为微末之人,但爹爹也教我等不可以天潢贵胄自居,且儿子颇好武学,因此未顾忌到法度,望爹爹恕罪。而今我那恩人被冤屈下狱了,还望爹爹明察他的冤枉,还他一个清白。”
高俅正欲反驳,却发现官家还没开口,于是硬生生憋了回去。
“那教头姓甚名谁,如何被冤枉的,你且说来。”
“爹爹,他姓林,是……”官家听到那教头姓林,摆手问高俅道:“哦?太尉,那个要害你的教头姓什么来着?”
“也姓林。”高俅回答道。
官家更稀奇了:“你俩莫不是为着同一件事而来?”
赵元凌忙道:“正是。爹爹请听儿尽诉冤屈!林教头的……”
高俅又怎会让他唱独角戏呢,忙道:“陛下,那林教头想来也的确是冤屈,只因一次迟到便被臣笞打四十,想来定心中不平,因此才会带刀私入白虎堂,也是臣治下太过严苛,才会酿成今日之祸。臣愿自罚。”
赵元凌急了:“爹爹,事实并非如此!乃是高俅之子……”
高俅又道:“但陛下不可罔顾法度,私闯白虎堂终究有罪。”
赵元凌道:“太尉可否容我将冤屈说完再做辩解啊。你我为着同一件事争吵起来,面上都不好看。林冲是否冤屈,待我将事实禀明,官家自有圣裁,太尉何必着急堵我的嘴呢?”
因林冲一事,赵元凌完全是正义的一方,要救林冲,最忌讳隐瞒自己的心思,因此赵元凌把自己的心思都摆在明面上,也把高俅的心思扯到明面上,让他也欺瞒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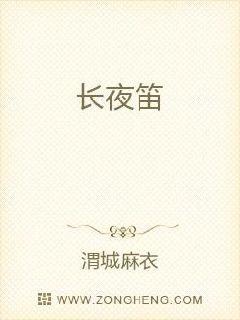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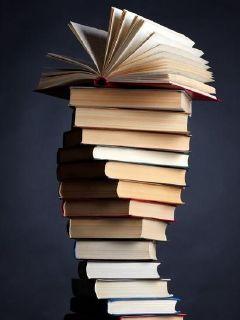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