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叫大卫,出生再大约三十年前的康涅狄格州,父亲是一个富有的矿主。在我十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我要在两年内专心致志经营我将要继承的事业,并获得大部分股权之后就可以继承他的财产了。
我竭尽全力的完成我父母最后的遗愿,不是以为他们的遗产而是因为我爱我的父亲,尊敬我的父亲。就这样,我在矿上和会计室里面馒头苦干了六个月,渐渐开始熟悉了这个行业的哥哥细节,工作也开始顺手了。
这里时候,佩里的一个发明引起了我的兴趣。佩里是一个老伙计,他把自己大大半生都献给了一个完美的地下探矿机器。在空闲的时候,还自学了古生物学。我仔细研究了他的计划,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检查了他所有的工作模型,那个时候我深信,我只要提供必要的资金就可以简称一个完成的、使用的勘探机器。
我并不想在这里详细讲述那个机器的构造——他就在离这里两英里以外的沙漠,如果你想看的话,明天可以过去看看。概括的说,外表上看起他就是一个长约一百英尺的大钢瓶,上面谅解一些让它可以在地下可以自由转动和扭转的一些装置,一段是一个巨大的旋转钻机,由一台发动机提供动力。佩里说,这台发动机能够产生的动力比起其他的任何一台发动机能够提供的动力都大。他还声称,就光是这项发明就能够让我们变得十分富有,我打算在这一次秘密实验成功之后就将这项成果公诸于世,——但是佩里却没有从那次的实验之旅中回来,而我的回来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是实验的前一天晚上,就是那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就要测试这个奇妙发明的使用性的重要时刻。快到午夜十分,我们在那个佩里建造他那个习惯称之为“铁鼹鼠”的机器的高塔,重新检查以一遍机器。它那巨大的鼻子静止的停在光秃秃的地面上。我们穿过舱门进入保护着个机器核心的外壳,把它们又重新一一固定了一下,然后进入了舱室,里面这个机器的控制系统,包括各种线管等,打开了里面的电灯。
佩里看着他的发电机,舱室里面的一个大水箱,里面装满了化学药品,那些能用来制造新鲜空气,用来代替我们呼吸时所消耗的空气;还有一些仪器记录这个机器的速度、温度、距离,还有一些能记录我们通过的地方周围的材料。
佩里测试了转向装置,转动了那些巨大的齿轮,俯瞰着那些可以把巨大力量传递给这个“铁鼹鼠”鼻子部位钻子的巨大齿轮,还有那些他也完全陌生的精巧的机械。
我们的座位是经过特别处理的,不仅能够保证我们想地下进发的时候,还是我们在地下各个方向行进,或者垂直向上回到地面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持平衡和稳定,还能保持我们始终都是头部向上的。
当一切就绪的时候,我们坐在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带上头盔。佩里低下头开始祈祷。我们过了好大一会,他终于祈祷完了,送了一口气,用手抓住了起动杆,随后我们身后就想起了一阵可怕的轰鸣声——铁鼹鼠巨大的身躯开始颤抖,震动——当松软的泥土开始穿过内层和外层夹板之间的空隙,在我们身后堆积起来的时候,发出一阵急促的声音。
我们开始了!
机器的喧嚣声震耳欲聋,让人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压力,似乎心脏都要跳出来了,整整过了好几分钟,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只能无能为力的抓住自己座位的扶手。慌乱之间佩里瞥了一眼仪表盘。
“我的天啊!”他大声叫道,“不可能,你快看看里程表上显示的是什么?”
他说的里程表和测速仪都在我这边的船舱里,当我转身去读测速仪上的数字时,我看到佩里在哪里喃喃自语。
“需要上升十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我看到他在哪里疯狂的拽着方向盘。
当我终于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找到那根小针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佩里疯狂的原因,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定了定神,压下心头的恐惧,尽量用平静的口气向佩里说:“佩里,等到你把它变成水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深度大概就有700英尺了。”
“那你还不过来帮我一把,我的孩子,”他冲我叫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推不动它,愿上帝赐予我们共同的力量能够成功,否则我们就完了。”
我慢慢的走到佩里的身边,我相信,那家巨大的车轮毫无疑问会立刻屈服于我年轻而有力的力量下。我的自信并不仅仅是来自于自己的自恋,而是我有着比常人强大的体格,在平时,我的体格总是让我的同伴们感到极度和绝望。正是这个原因,我的身体变得比他们想象中得更强大,因为我天生对自己强大得力量感到自豪,这使我在会尽自己所能得,用各种方法照顾和锻炼自己的身体和肌肉,而且,我从小就练习拳击,足球和棒球。
我怀着强大的自信抓住了那个巨大的铁环,但是尽管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还是和佩里一样徒劳无功,无法移动那个东西分毫。那个东西就像嘲笑我们的渺小,它没有移动分毫,它会把我们拖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笔直的向前狂奔,它是冷酷的、麻木的、可怕的!
最后我放弃的徒劳的挣扎,一句话也没有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喘着粗气。
这个时候是不需要语言的,至少我想不出要说什么。除了佩里的祈祷,我像它肯定会的,它可以在一个三明治时候祈祷,他早上起床后就祈祷,饭前祈祷,吃完饭前祈祷,晚上睡觉前又祈祷。在这期间,他常常找借口来祈祷,即使这样的祈祷在我这样世俗的人的眼睛里似乎是多余的,但既然它快要死了,我相信我一定会看到一场完美的祈祷,如果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暗示如此**的行为的话。
我转头看向佩里,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佩里这个时候竟然没有在祈祷,他变成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从他嘴里流出来的竟然不是祈祷,而是清一色的污言秽语,而那些咒骂全都指向这些丝毫不受控制的机械装置。
“我认为,佩里,”我责备到,“像你这样自称虔诚的人,宁愿听到你祷告,也不愿听到你这个时候咒骂。”。
“死亡!”佩里大声叫道,“是死亡让你害怕了吗,这与这个世界将要承受的损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什么,大卫要在这个铁通立面,我已经证明了科学不能光有幻想,已经用新的思路来证明这个设想的可能行。我们用一万人的力量来推动一块钢前进。两个人的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即使我们得坟墓是在很深得地下,这个世界得核心,我这个发明是成功得,我创造的这个机器是完全成功的,它带着我们向着地球的中心驶去。”
我必须坦率的承认,相对与世界损失了什么,我更在乎自己会将要面对什么,将要失去什么。这个世界微不足道的损失,对于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我们还能做什么?”我问,将我深深的不安压下掩藏在我低沉的声音里。
“我们可以停在这里,当我们的空气储备用完的时候,我们会死在这里,死于窒息。”佩里回答道,“或者我们可以抱着一丝希望,希望我们能够将勘探者从垂直的方向放偏转出去,沿着另一个方向最终能将我们送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内部温度达到更高之前成功做到这一点,我们甚至还可能生存下来。在我看来,即使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都要尝试,不然我们会死的更快,没有什么回避坐着等待缓慢的死亡的到来更折磨人的事情了。
我看了一眼温度计,现在的温度已经是华氏110度了。就在刚才我们说话的那一会儿,这个强壮的铁鼹鼠已经在地壳中向前行进一英里了。
“那么我们就继续吧,”我说道,“以这种速度,在不快点,也许我们很快就会迎来死亡了。你以前也没有说过这个东西有这么快啊,佩里,你以前不知道吗?”
“不,”他说道,“我无法精确计算出它的速度,因为我没有测量发动机功率的仪器,不过我想我们的速度应该是每小时五百码左右。”
“我们的时速是每小时7英里,”我坐在那里,眼睛里盯着里程表,我现在有点后悔,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佩里的计算能力差强人意呢,要是早知道,就应该在多做些准备了。
“地壳有多厚?”我又问了一句。
“对于这个问题,有数不清的猜测,多的就像地质学家一样多。”他回答,“有一个说法,大概是30英里,因为地球内部的温度,深度每增加60到70英尺,温度会升高1度,到了那个深度,地表上任何难以熔化的物质都会熔化。另一种说法是根据地球自转还有地球摆动的幅度的要求,地球如果不是一个固体的话,至少必须有一个不低于八百到一千英里厚的外壳。就这些,你觉得那个靠谱点,就选择那个。”
“如果证明这些结论是真的呢?”尽管心里十分恐惧,我还是又问了一句。
“不管是哪一种,对于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相同的,大卫。”佩里回道,“另外,我们的燃料最多只能够我们用三四天了,还有舱里的空气只能够我们支撑三天了,因此,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支撑哦我们穿越超过八千英里长的岩石到达地球的另一端。”
“如果地壳足够厚,我们将要在地表一下六百英里到七百英里的地方就会停止,但是我们距离旅程终点差不多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我们就变成尸体了,对吗?”我问。
“完全正确,大卫,你害怕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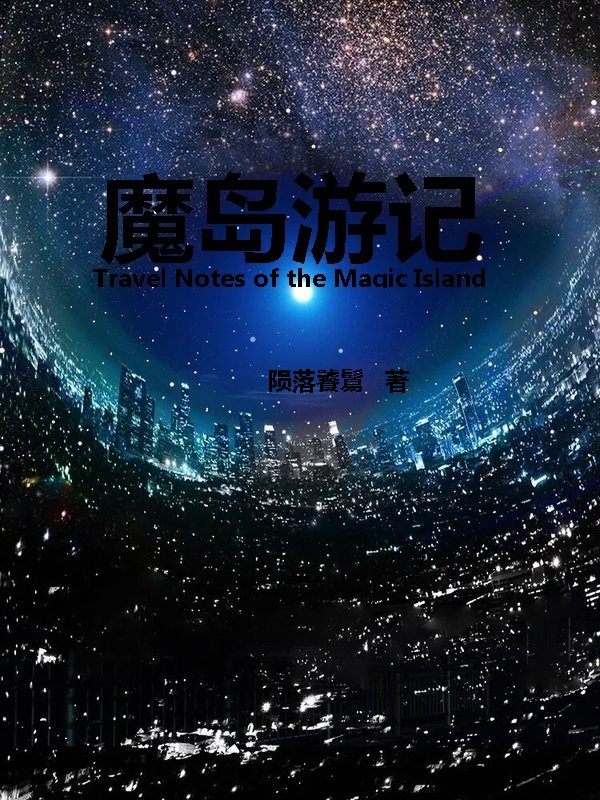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